报道:600元和国家计生政策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金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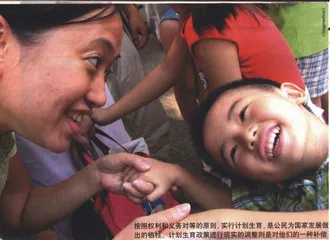
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为国家发展做出的牺牲,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现实的调整则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黄树民博士在他关于1949年后中国农村变革的书《林村的故事》中提及计划生育,他引用村支书叶书记的话说:“1977年的时候,政府开始紧缩每户农家可以生育的婴儿数目。新规定是一户只能生两个。”
这一项政策很快就转变为后来成为基本国策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有资料显示,我国生育率的转变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强有力干预下,出生率从70年代初的30‰。以上降低到1998年的16.03‰;总和生育率在70年代以前为6左右,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90年代中后期进一步降低到1.9以下。尽管在我国一些地区存在着出生人口漏报的现象,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在90年代末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保守地计算,我们在25年间减少出生2.6~3.3亿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健雄因此说:“在世界上人口如此快的减少还没有一个先例。”
回顾这一政策选择,葛健雄说,这个强制措施是在“坏跟更坏之间的选择”。这样一个选择附带的后果是,在解决了人口爆炸危机的同时带来诸多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说,人口控制本身有其合理性,但却靠单一政策的强制力管理方式,靠红头文件的机械做法,层层下达指标。相关问题专家王建国指出,这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带有强迫性,五花八门。
杨建顺说自己就来自农村,“那里不超生的几乎没有”。这样上面的土政策和下面的土对策相对应,杨建顺说产生的后果是一个恶性循环:“在表面上,它的成本是高额公共资金的支付,更深层的成本则是执法人员与当地人产生敌对情绪,群众对政府失去信心,超生黑户口使下一代的生存条件直接受到威胁,埋下怨恨的种子。”
王建国谈到这一点撰文指出,这种硬政策很难基于人们自愿的基础上,而且实行起来成本奇高,许多想生二胎三胎的,想生儿子的,想尽办法与政府周旋。政府大约有20万人专门从事计划生育工作,政府每年要花巨大的资金推行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的政策导向备受质疑的一点是,将关注点过分集中在生育数量上,将生育问题与其他问题相割裂,尤其是将生育问题与养老问题相割裂。
根本性的转变是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人评论说这是在控制人口与树立国际形象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找到的平衡点,中国计划生育开始从行政强制为主导向以群众满意程度为第一标准的新阶段的转变。
转变的驱动力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葛健雄说:“从1993年开始,上海已经连续11年保持人口负增长,浙江也有这个趋势。其实发达国家控制工业化人口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是靠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在中国,发达地区也在逐步过渡到这一阶段。”而从更大的背景上来看,有学者说,我们已经从降低生育水平阶段过渡到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
江苏省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李晓明说,独生子女政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政策,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农民生育愿望强烈,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还有更现实的问题。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需要大的环境和气候,《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是一个前提条件。
李晓明说,南京市在国内第一个制定政策法规,为农村独生女家庭发养老金,“江苏省的生育政策一直比较偏激,周围的省份对于独女户有生二胎的政策,但我们没有。我们在近一年的时间在南京各郊县调查,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即使局部地区解决了,也不是针对计划生育政策而言的。我们发现在南京农村一对老夫妇每个月有几十元、一百元的现金就可以生活,于是我们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对只生育一个女孩儿的年满60岁的农村居民,每人每月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25%领取养老金。”
而4月初,面对全国更大范围的奖励政策推出。华建敏强调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资金”主要针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进行试点,着重解决不发达地区的问题。“落实中央专项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确保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资金足额到
位。”李晓明解释说,现在新生儿人口增长较快的是西部等贫困地区,因此,切实解决这一地区的人口及相关问题意义重大。
李晓明说:“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为国家发展做出的牺牲,过去针对公民的权利部分,政府做得不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现实的调整则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
有学者指出,夫妇在生育控制上承担成本,可以说是为公众利益做出的牺牲,因此,有关鼓励人们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本质上也应该是一种补偿政策。但在我国特别的农村地区,在国家执行严格人口控制的同时,对生育控制个人成本的补偿政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虽然在一些地区开展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少生快富工程”等,但这类项目或活动不是国家制度性的政策。
国家计生委有关官员在谈到这一点时也表示,这次试点还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由此看来,从强制政策到奖励政策,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支持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已经有了开端。
普遍生二胎不仅有条件,也有必要性
——访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大文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计划生育的奖励政策是一种赎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大文:我们在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生育权,这两者都不能偏离。本来一定人口和人口的再生产就是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做贡献,所以有一点很重要:生育是对社会的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国家对生育的限定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
杨大文:我不承认我们搞过“一胎化”,从80年代初我就参加相关的专家咨询工作,我们当时是提倡“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但这是一个授权性的规定,各个地方要按自己的情况安排相关政策。
三联生活周刊:各个省分在具体操作上有多大的灵活性?
杨大文:我记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地抓计划生育,80年代后期各省都有了地方性的法规,那时就有关于二胎的规定,地方上叫做“开二胎的口子”,这个口子就有的大有的小,而政策是有连续性的。
三联生活周刊: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二十多年,现在是否到了一个转变的关口?
杨大文:计划生育政策现在仍然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控制人口的必要策略,我们的目标是2050年人口不超15亿。过去我们是不得己,现在我们国家的生育率并不高,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人口生产是惰性运动,过去的因素还在起作用,因此政府现在需要在社会保障上做文章。其实不是生一个就比生二个好,我认为普遍生二胎不仅有条件而且有必要性,这一目标相信也不会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