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光荣与梦想》
作者:苗炜(文 / 苗炜 史航 尚进)

1972年的尼克松
1969年离开越南的美军士兵
一个美国人说:“我认为,一本书应该读三遍,第一遍是年轻时读,第二遍是成熟之后读,第三遍是年老以后再读,这样就等于读了三本不同的书,无知懵懂的年轻人会逐渐积累人生的经验,从一本书中读到不同的东西。”这番话是针对威廉·曼彻斯特《总统之死》一书说的,去年11月是肯尼迪总统遇刺40周年纪念,许多人重新阅读了《总统之死》。这本书的精装本曾经卖出过130万本。
现在,曼彻斯特的另一本书在中国被重新阅读,那就是他的《光荣与梦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发行过这本书,后因版权问题迟迟未能再版。2004年2月,海南出版社以4500美元的价格购得中文简体字版权重新刊印。
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曾经影响过一代文字工作者,特别是怀有远大理想的媒体从业者。在我进入新闻行当时,有过一次培训,老师给我们讲《光荣与梦想》,这本书注意细节——麦克阿瑟是个自大的家伙,他总说“麦克阿瑟要如何如何”而不是说“我”,一般这样说话的人都是自恋的;宏观视角——作者讲述大萧条最厉害那一年的场景,同时交代那时候尼克松在干什么,肯尼迪多大了,就像平行蒙太奇;材料丰富,叙述生动,幽默感等等,这本书的优秀品质实在太多了。用一个词来总结,《光荣与梦想》表现出了一种“新闻的美感”。
那个培训班发的教材并不是《光荣与梦想》,而是解放军出版社的《外国优秀新闻作品选》,从快讯到特写,各种体裁都有。那本“作品选”里有两篇文章我记忆深刻,一个是有关三峡的几百字的文章,里面融入20多个数字,却一点也不显枯燥。另一篇是对一起枪杀案的特写,作者以扎实的采访重现现场,写得简直像是好莱坞的分镜头剧本。老师们大概害怕一个记者老憋着写《光荣与梦想》,却连个简单的采访都完成不了,所以一再嘱咐我们仔细学习那里头的范文。
我还记得老师对现场感的强调,他讲述自己对唐山地震所做的细致访问,讲他的作品《唐山大地震》,他还讲了一个笑话——有一年,一个地方举办鹦鹉比赛,各路的鹦鹉都充分施展自己的本领,有的背诵罗斯福的演讲“四大自由”,有的背诵毛主席的《别了司徒雷登》,台下挤着数万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欢声雷动。但最终拿了冠军的那个鹦鹉表演的时间最短,他上台就说了一句:“我操,这么多人!”——钱钢老师说,为什么这个鹦鹉拿了冠军,就是因为他有现场感。
那时我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没多久,根深蒂固地认为优秀的文字都来自虚构,伟大的故事都来自虚构,但经过这一番培训,我开始相信好的记者也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光荣与梦想》也可以算是新闻里的“战争与和平”。
后来,光荣与梦想成为一个固定词组,与之出现频率相当的另一个词组是“美丽与哀愁”。在我拿到新版的《光荣与梦想》之后,迫不及待地重读了一遍,在这本书的结尾之处,我终于发现它在十几年前为什么打动我,作者在最后一段提到了弗罗斯特的诗和托马斯·沃尔夫,他还用菲茨杰拉德的句子来结尾:“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它打动我的是文学青年叙述历史的卤莽。1932年,作者的历史篇章开始之时,他才10岁,但这不耽误人家通过材料与档案追述,文学青年在纪实性的写作中可以获得一种操纵历史的快感,或者说“记者的牛逼感”,这种感觉催生了我们这里许多虚妄的报告文学。重新阅读,《光荣与梦想》带给我的感受是嘈杂与混乱,调侃一下,这分明是一部美国版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对韩战的分析轻描淡写,对“二战”的记录毫无价值,对60年代文化的讨论也显肤浅,只有一种宏大叙事的情怀试图笼罩住1932到1972年的那40年光阴。
至于“新闻的美感”,我倒更愿意提一提《巴黎烧了吗》,译林出版社2002年7月发行了这本书的中文版,但它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光荣与梦想》那样的推崇,作者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分别是《新闻周刊》和《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他们用三年时间采访了800多当事人,采用其中536人的亲身经历重现了盟军解放巴黎的故事。
1993年8月的一个早上,一个撰写肯尼迪遇刺故事的作者给威廉·曼彻斯特打了一个电话,他希望曼彻斯特先生,一,能公开当年就肯尼迪遇刺进行采访的笔记;二,披露一下《总统之死》一书中有关总统安全工作的信息来源。曼彻斯特先生的回答是:“我没有借鉴你的作品,我的采访笔记不会公开,我的消息来源都已经死了,一般人们是写信给我,而不是直接打电话给我。”
这场在美国的笔墨官司并不重要,曼彻斯特毕竟是钦定的肯尼迪遇刺故事的撰写者。他写的书实在太多了,而且有许多本长得吓人,包括几本小说,他写过《克虏伯军火》、《美国恺撒——麦克阿瑟》、《告别黑暗》等18部作品,曼彻斯特就像是“历史著作中的阿西莫夫”。
2001年8月,《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说,这个对历史事件有着超强记忆力、脑子就是资料库的曼彻斯特终于承认他不能完成三部曲《丘吉尔传》的第三本,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983年,第二卷出版于1988年,两本书加起来共1729页,售出40万本。曼彻斯特说:“过去写作对我来说像呼吸一样容易,但现在我给朋友写封信都要一天的时间。我没法组织材料,没法联结上下文,我过去写作夜以继日,现在身体不行了。”他对未完成的书有一股了不起的自信,“我对丘吉尔的研究已经完成,别人不可能有我的风格,不能像我那样将我的理解贯穿在文字中,我是惟一一个能写这书的人。”全世界有600多本丘吉尔的传记,《时代周刊》评价曼彻斯特的第一卷是“80年代最了不起的非虚构作品之一”,而《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则认为该书毫无价值。
我从网上搜罗来这样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曼彻斯特和《光荣与梦想》只是二流作家和二流作品,只是出于好奇,想把自己第二次阅读感到的失落找到一些原因。曼彻斯特是位有责任感的历史作家,他说过,学校里的历史教育是片面的,日本人的历史教育就是典型,人民需要了解历史,在学校里学的那些还远远不够。对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在那个信息贫乏的时候,能有那样通俗热闹的读物是不寻常的。这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渗透着情感,他对一代美国人曾经这样评价“孤僻的、谨慎的、缺乏想象力的、琐碎的、没有冒险精神的、沉默的”,1951年11月5日一期《时代周刊》以“沉默的一代”来描绘1925年到1942年出生的美国人。
与曼彻斯特的形容词相对应,“开放的、卤莽的、充满想象力、大气的、敢于冒险的、爽朗的”也许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拥有的气氛(或者是拥有一部分)。在那样的时候,我们这些文学青年被《光荣与梦想》等书籍激发出一种历史感,总踮起脚攥着拳头想改变点什么,但在庸常的中年生活开始之后,我已经不习惯于从高处想问题—一比如说伟大的小说与伟大的新闻何者更伟大,而是从低处瞎琢磨一那么多烂新闻那么多烂小说何者更无聊。一本书的再版不能将昔日的光荣与梦想灌注到如今这纷乱、琐碎、轻浮的年代中,但我也不打算“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原来的那个年代也并不一定更美好。

几个改变历史的日子
1948年5月14日
“我想让整个世界对犹太人来说都是安全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说。1947年11月,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议案,11月29日,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其中10个是伊斯兰国家)、10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即联合国第181号决议。
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前,身高1.6米的“以色列建国之父”本·古里安宣读《以色列国独立宣言》。全文共979个单词,最后两句话是:“以色列国成立。会议结束。”
1948年5月15日凌晨,英国宣布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天,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阿拉伯联盟发表声明,宣布对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这种冲突延续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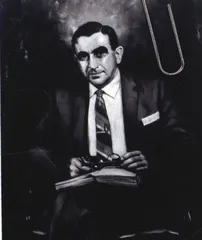
1952年10月31日
这一天的夜里,埃卢盖拉布岛消失,沉没于海底。氢弹爆炸成功。9个月后,莫斯科宣布“美国人不再垄断氢弹”,英国人也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装置。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的噩梦变成了现实,世界陷入“核恐怖”之中。
苏联人在1949年成功爆炸原子弹,使得爱德华·特勒认为有必要研制破坏力更大的炸弹,尽管许多科学家对此表示反对,但特勒却称“氢弹”为“我的宝贝”,他获得了“氢弹之父”的称呼。
特勒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在德国完成了大学课程,1935年,特勒举家迁往美国。在参与原子弹、氢弹的研究之后,他积极倡导《战略防御计划》(即后来为里根政府所采纳的“星球大战”计划),对美国的防御及能源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2003年9月9日,爱德华·特勒在加利福尼亚去世,享年95岁。在他去世一个半月之前,这位饱受争议的科学家被布什总统授予美国公民的最高奖章——总统自由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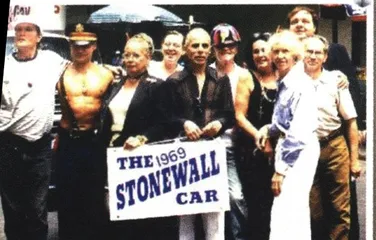
1969年6月28日
凌晨1点20分,8个警察进入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这家酒馆没有卖酒执照,顾客以同性恋者为主,有许多人在磕药。当警察要将酒吧老板押入囚车时,顾客与警察的冲突开始了,他们用酒瓶、垃圾和石块攻击警察。骚乱延续了两天。
这起事件被认为是同性恋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开始,每年6月都会有同性恋游行以兹纪念。
克里斯多福街51号的石墙酒吧原址已经变成服饰店,旁边的53号则仿原貌重建石墙酒吧,门牌上有一段话——“Site of the Stonewall Riots,June 27-29 1969, Birth of the Mod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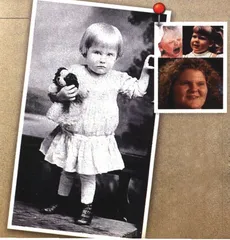
1978年7月25日
英国兰开夏郡奥尔德姆市总医院,路易斯·布朗在午夜时分降生,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期盼她早日来临的人们称之为“奇迹宝贝”,但也有评论认为,这是“弗兰肯斯坦之子”,许多报纸以“超级宝贝”称呼路易斯·布朗,但他们保留着重印当天报纸的权利——如果这孩子不能活过一个礼拜,那人们会购买他出生那天的报纸做纪念。
在她出生之前,宗教界和政治界指责医生“扮演上帝”、“制造怪物”,但路易丝没有一丝缺陷,她从显微镜下培养液里漂动着的一些微小的细胞团一一人类早期胚胎,经过母亲的孕育,变成了一个2.1公斤重的小丫头。
当年,路易斯·布朗的医生爱德华兹说:“我希望在很短的几年之内,试管婴儿变成寻常事。”但后来,路易斯要不断向同学们解释,她不是从试管里出来的。
去年,路易斯·布朗度过她25岁的生日(从照片上看,她好像有些胖),而这世界上已经有超过100万的试管婴儿。围绕她而引发的争论如今又有了翻版——克隆人问题。

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
历史就是这样经过我们
史航
奥地利人茨威格一生致力于记录那些人类群星闪耀的瞬间,然而我们毕竟不能终生仰望星空。那些一夜写出的马赛曲,一朝攻陷的君士坦丁堡,虽然穿越百年千年,影响着我们今日的生活,但是,与我们的生命有关的,到底是直抵天涯的他乡道路,还是低头可见的自家掌纹呢?失传沉埋而终于得以问世的隐史秘籍,或是搬家时偶然摸索出的中学日记,你更急着打开哪一本呢?
上大学的时候,我最迷恋的书是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六卷本,深蓝色的封面,讲述一个卷头发坏脾气的少年郎,一生怎么结识着友人历经着动乱选择着立场承担着命运。那里面诗哲情圣的名字比比皆是,可你真正感念的,倒是作者悄悄告诉你的事情。就像电车经过马雅可夫斯基大街的时候,作者会想起自己记忆中那个沉郁焦躁的年轻人,想着他与这条大街是何等的了不相干;作者谈起20年代在巴黎街头,见到流亡中的巴尔蒙特,对方只是冷傲地问一句“青年们还读我的诗吗?”作者没有告诉他真相,作者说他的诗还在流传,巴尔蒙特短促地笑了一声,大步流星走去,他是一个何等容易受欺的遁世者啊……
年轻时读到这样的书真是幸运,让你感知无常,永远不会轻诋友情,哪怕是终遭背叛的友情,因为命运太有办法让我们彼此失散。《我和我同时代人的故事》、《我承认我曾历经沧桑》……这样的书名都是何等的神奇啊,它们讲的都不单单是历史,而是命运。它们让我铭记的细节,让我的平淡人生,略染感慨喟叹。
戴安娜·拉维奇主编的《美国读本》上册,收入了《西雅图大酋长的演说》,这位印第安老人的告白,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天鹅之歌”。
“在我的人民看来,这儿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每一个山坡,每一条山谷,每一块平原和树林都由于一些在那早已消逝的岁月里的悲伤或愉快的事件,而变成了圣地。岩石貌似麻木,毫无生气,但却在那阳光普照的静悄悄的海岸边淌着汗水,颤栗着回想起那些与我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动人往事……
“当你们的城市和乡村的街道寂静无声,你们以为这些街道已经被人舍弃,其实他们却熙熙攘攘挤满了那些还乡的主人。你们白人永远不会孤单的。”
是的,时代已逝,因缘已失,我们只有在细节中还乡,我们只能凝神谛听那些普通人的喃喃自语。斯·特克尔首创的“口述实录文学”,在国内已经出版了三部——《美国梦寻》、《劫后人语》、《大分裂》——《工作》似也有零散译出。我们见证了那样一些的美国人,歌曲中听不到电影上见不到的美国人,他们历经萧条,战争,富足,他们诚实而迷惘。对照国内,我们倒也有过这样的口述实录,那就是当初张辛欣、桑晔访撰出的温厚篇章——《北京人》。如今呢,如今还有安顿们奔走传销迎风摇曳的绝对隐私。
其实,我不反感安顿们,因为A女士和B先生的情来情去患得患失,未必不是组成时代大历史的细密元素,俟以多年沉淀,一样会显得沉郁感伤。我们弄情索爱却又时时贪吝,这本是真切人性,不足羞,羞的是矫情的文笔,就像有害于人体的墙壁涂料,把那份贪吝修饰成为了品位,最终诱人学步,戕害无辜。

广岛,1945年8月6日
所以,真的迷恋马尔科姆·考利的文笔和用心,这位海明威的友人福克纳的研究者,他以私人感受为参照,就像手按《圣经》起誓的证人一样,记录了“迷惘的一代”,他们的幻灭与再生,书名叫做《流放者的归来》。结尾那段是何等神情内敛,回想自己历经的迷惘时代,他说那就像一个有太多音乐太多客人太多烟雾的派对,你终于走出来,发现外面已是黎明,一个老妇人正驼着背,在积雪的街道上走着,找寻一点有用的东西。
在街道上能找寻到什么呢?近来因为重版发行而又被提及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实录》,就是一本来自街道的书。作者威廉·曼彻斯特是一个记者,他记录下这个广袤国度里40年的兴衰光阴。这套书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意义重大。对我来说,则是它的开篇,意义最为重大,写的是在胡佛总统的暧昧授权下,在首都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正规军队,朝着请愿示威乞求退休金的退伍军人们动武的情景。作者写到了那次悲剧事件发生时的首都天气,写到好心人为请愿者们募捐食物,上等人则是掩鼻而过,写到报纸上催促政府动手的俏皮叫嚣,最后轻轻点一句——其实一切不过是在证明,这个国家里的有钱人,他们的心是越来越狠了。
这句话我可真忘不了,感谢译者译得如此直白坦诚。
此后漫漫的历史细节,不断这样刺痛着有心的读者,也可能是一次种族歧视的小小流露,也可能是一个反战老人的落魄晚景,总是这样智者缄口,总是这样良知远行,让我联想到教父之父马里奥普佐在《西西里人》中的慨叹——西西里啊,你是如此饥不择食地吞噬着你的儿子,你的精英,你可曾想过何时罢休?我确实也想知道,那些在《美国梦寻》里忏悔流泪的美国人,那些在《美国读本》中悲悯长叹的美国人,他们哪里去了?
我能在电视上看到联合国讲坛上的外交官,我能在报纸上看到记者麦克风前的政客,我能看到朝摄影机友好招手的美国大兵,可我想我还是错过了一些身影,那些在街头寒风中护卫反战标语牌的人们,那些在夜色中公开祈祷的人们,他们在报纸杂志上萎缩为一个数字,可我该多看一看他们的面孔。
历史就是这样经过我们,漫过我们,我们以为自己是岸,可以永远乐观地眺望,最终我们却成为河床,与善良的愿望一起沉埋永世。

登月,1969年7月20日
没见过光荣 只保留梦想
尚进
京文唱片在去年11月发行了一张名为《呐喊》的双张CD,乍一看就如同大多数摇滚拼盘一样,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收录了崔健创立的七合板乐队在1985年用绚丽的和声来翻唱《卡斯保罗集市》,辛弃疾的《烽火扬州路》是如何被轮回乐队金属摇滚化的,也很难发现唐朝乐队《太阳》的前身《粉雾》是如何走上当年那著名的“90现代音乐会”的。实际上乐评人们并没有如获至宝的感觉,颜峻慢条斯理地说那些是摇滚老爷子们了,王晓峰则干脆要把CD送人。而对于80年代还在听小虎队的大多数人孩子来说,那就是历史。这种感觉与今日读再版的《光荣与梦想》是那样的相似。
鳄鱼邓迪的扮演者保罗·霍根是《光荣与梦想》的推崇者之一,他评价道:“所有这一代的读者能再次回味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生活。”但谁是跟鳄鱼邓迪同时代的人呢,至少80年代商务印书馆发行的4册版本翻阅过的人并不多,我也仅仅是对1968年产生浓烈兴趣的时候才去图书馆翻阅过,远非许志远那样故意缴纳10倍丢失补偿金来收集老版本的《光荣与梦想》来的疯狂。就如同阿瑟·A·伯格在写《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时说的那样,“没有经历真相不要紧,可以通过分析和回忆来重温现场感,但是那种新鲜扑面的犯罪感,只有第一次接触才有”。实际上重印版本确实难以调起阅读80年代第一版时那种启蒙感,更多追捧重印版的人嘴上会大谈从《光荣与梦想》的作者威廉·曼彻斯特那里得到新闻感,同时获取了一位美国内部人士用文字方法对历史的记录。但是对于重印版本的大多数购买者而言,他们所需要的实际上并不是《光荣与梦想》本身,而是一种对于80年代文字记录时代的眷恋。这时你会发现,《阿甘正传》在故事性上比《光荣与梦想》更有想象力。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光荣与梦想》这本书。纽约市卫生局当年统计的在1932年每天只吃一顿饭,90%营养不良的儿童们,现在已经陆续作古了,不知道这与童年的营养匮乏有无关系。1938年10月30日,坐在大瀑布式落地收音机前听威尔斯“直播”火星人入侵地球广播的人,不知道还有几位看到了最近火星探索者的登陆。而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山谷与姑母驾驶教练机,第一个发现日本机群的小乔纳森,此后不知是否成为了合格的飞行员。当麦克·阿瑟的儿子跟随父亲在1951年4月20日纽约经历280万人的欢迎时,他可曾想过他眼前的一幕将是老兵时代最后的辉煌。所有人都关心艾伦·韦尔什·杜勒斯从1953年到1961年担任中央情报主任的时候,那些冷战故事的真相到底如何。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引发种族隔离制度坍塌的那几位黑人大学生,毕业之后到底做了点什么呢。1968年被派往越南的肯·肖恩是不是也同大多数退伍兵一样此后陷入人生危机。尽管这些仅仅是威廉·曼彻斯特对于细节记录的一部分,但是这只代表《光荣与梦想》所达到的文字高峰。
雷蒙·威廉斯在他的《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中写道:“自从1958年开始美国国家档案馆就收录电视片来记录档案了,文字工作者们被他们的传播语态抛弃了。”尽管雷蒙·威廉斯在说此话之前,《光荣与梦想》还没有出版,但是面对纪录片和CNN模式,电视毫不留情地压制了文字写作。就像孙玉胜所写的那本《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目睹了一次次的‘技术事件’造成了新的电视理念,从而深刻影响着媒体记录发展的进程”。90年代的互联网前沿分子,网景公司创始人吉姆·克拉克(Jim Clark)也对《光荣与梦想》颇有感慨,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威廉·曼彻斯特,因为网景给所有人带来了浏览器,在互联网上书写《光荣与梦想》,要比去图书馆查资料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