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交十记》到2004的外交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覃里雯)
2003年中国外交并不轻松,但中国政府在处理日渐庞杂的问题时,越来越成熟得体。图为中国总理温家宝2003年12月访问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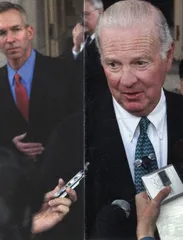
美国特使贝克在2003年12月的亚洲特别行程也如愿以偿
“在研究新中国外交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几个核心词:存亡、兴衰、荣辱。”一位四十来岁的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说,“我们很多人忽视了‘荣辱’这个不可缺少的领域。”他的这句话没有获得什么回应。这是2003年12月的北京干面胡同,钱其琛《外交十记》的新书发布会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召开,外交部官员、驻外大使、党史研究专家济济一堂,回顾各自眼中的十年外交。
外交官们的发言更为实际。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回顾了1989年之后中国如何“利用矛盾、利用不同点来解决制裁困境。”这些矛盾和不同点较之冷战时期更为复杂。他感叹“我们还在争取平等地位”,但是,外交官们从经验中学到了规律,“在国际重大事件之间都存在内在联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深为感触的是,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中国如何为自己赢得信任,创造更好的安全环境:在中国开展对苏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并参与维持柬埔寨民主选举之后,它与东盟的关系骤然升温。
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回顾了钱其琛主导外交工作期间的六大变化:从意识形态到实事求是;从着重强调政治到着重强调国家利益;从被动到主动;从政治领域到全面领域;从重点重视第三世界到全面外交,尤其是与大国的关系;从重视双边关系到发展多边外交(包括加大在联合国的影响)。
外交官们清晰地意识到最后残留的冷战时代符号都已经在改变涵义,这不再是一个由界限分明的阵营和意识形态主宰的世界。2003年末,卡扎菲承认利比亚对洛克比空难负责,并同意赔偿损失。2004年春季,包括波兰和捷克等东欧国家在内的十个欧洲国家即将扩大欧盟的阵营,这意味着它们将减少对一个再度强大的俄罗斯的忧惧……
2003年12月美国特使贝克的亚洲特别行程,向日本、韩国和中国政府寻求支持,以减免伊拉克的外债——他如愿以偿。美国同样理智地寻求了中国的帮助,解决朝鲜的核武问题。在不到一年的讨价还价、僵局和秘密的斡旋之后,2004年1月6日,朝鲜表示愿意有条件地停止试验和生产核武器。曾经态度强硬的伊朗也于2003年12月18日签署了防止核扩散公约,并同意接受核查。
2003年似乎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年份。你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民族国家之间迫切的大问题似乎都已经得到解决,或者部分解决。所有政府都主动或被动地归拢到既有国际体系之中,按照通行规则行事。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中热情地宣称:“世界似乎安全了、稳定了。重要的是人类有了希望。”“9·11”事件一度使这个印象受到剧烈动摇,但是现在它似乎又站稳了脚跟。
最大的疑惧存在于恐怖主义,这个伴随人类社会已久的肿瘤始终还是一个谜。但是正如梅兆荣大使所看到的那样,“‘9·11’事件并不只有负面效应,它逼迫政府间迅速消减猜忌,同舟共济”。
对恐怖主义的关注还引导各国,尤其是大国发展经济、重视公平,中国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贸易可以让世界更安全、更公平。”英国贸工大臣帕特里夏·休伊特说。
另一方面,反全球化人士和环保主义者对坎昆会议陷入僵局的欢呼可能过于天真。“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每天有数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5000万左右的妇女死于分娩。然而,我们还知道,通过减免关税,发展中国家至少每年可以获得1500亿美元,在2015年前将贫困人口减少1.5亿。”休伊特说。作为今日社会非零游戏的主要部分,贸易谈判需要足够的耐心,欧盟和美国之间就钢铁关税的问题进行了两年谈判,最终美国取消了进口钢铁的关税。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学会联合起来说不,更需要学会联合起来运用砝码,为自己创造机会。这正是中国发展和建立各个区域组织关系的重要性。
2003年的中国外交并不轻松,正好相反,它需要处理的问题日渐庞杂。但是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越来越成熟和得体。贸易争端仍然在继续,中国已经学会孤立地解决每个个案,而不是“对某些国家”作出笼统而过激的反应。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仅应当在经济和军事上是强大的,它同时也应当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传播到整个世界。
“扩大自由”将在美国的支持下被扩大到其他国家
2004年1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2004年的工作》(What We Will Do in 2004)的社论。在这篇短文中,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代表美国政府表示了广泛的决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扩大自由”,“自由”还将在美国的支持下被扩大到其他中东国家、拉美、欧亚和非洲;继续打击国际人口贩运活动;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救援计划将“使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免受这一恶魔的摧残”。“帮助较贫困国家通过实行良好的国家管理,选择合理的经济、贸易和环境政策,以及对本国人民的明智投资来实现其自身发展。”“与大国合作对付恐怖主义,与中俄日合作解决朝鲜核武问题。”‘我们也决心为结束在苏丹、利比里亚、北爱尔兰及其他地区的长期冲突而分担责任。实现这些目标将推动美国外交在全世界的成功。”
在2003年与2004年交界处,我们看到,全球60亿人中只有两个人能在作出以上宣言时不会被认为是疯子:美国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自冷战结束开始,学者们一直在预言多极世界的成形,但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就像电影《勇敢者游戏》中的蔓藤,粗大的枝蔓已经覆盖到了世界之屋的每个角落。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植物能够取代它的位置,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领袖能够同样宣称,自己的国家将为每个大洲上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发展负责。

朝核6方会谈在北京举行
“在未来20年里,中国的主要焦点将集中于国内,集中于无数的国内问题。”在2003年11/12月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一篇广受关注的题为《中国新外交》的文章这样说。作者Evan S.Medeiros和M.Taylor Fravel重点分析了中国外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生的变化:受害者心态的减少、加快融入现有国际体系、政策制定民主化、主动承担国际责任,这是一个逐步强盛的国家体现出的健康倾向。“中国融入了各大国际组织的星系,遵守其规则规范,以此倡导本国利益。它甚至在有限范围内寻求塑造这个体系的演变过程。”
被称为“中国外交大事之年”的2003年有足够的事件可供罗列: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中印首次开通直航,多次派遣中东特使关注巴以和谈,促成朝核六方会谈,中日韩合作宣言,中国防扩散白皮书,作为对话国第一次参与G8会议,各国领导人频繁互访……这些动作受到真诚的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活跃的角色出现。在近几年中,中国开始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采取少对抗、更成熟、更自信和(有些时候)更有建设性的方式。”《外交政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