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茶马古道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于)
藏族人丁大妈推开教堂的门,她说每天来这里让她觉得心里平静。当她推开门的那一瞬,令人一下想起林茨写的那本《福音谷》。看片结束后,我写了一个小纸条给田壮壮导演,向他推荐了这本描述傈僳族人和基督教的书。导演说他已经看过了林茨的另一本书《百褶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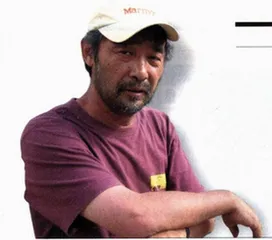
田壮壮
如果看过了《福音谷》,会觉得《德拉姆》(“平安女神”的意思)不够过瘾,它不够深入。《德拉姆》中也有30岁的傈僳族人牧师余建辉教大家颂读《圣经》的镜头,但远不如《福音谷》那样:林茨用诗化的语言,把虚构和现实编织在一起,写了这样一些“神贫”的人,宗教信仰改变了这些人的面貌,“所有的脸庞都被一种神奇的光亮辉映得灿烂而透明”,而日常生活中,他们不得不在巴掌大的地方种植农作物养家糊口。《德拉姆》还记录了生活在怒江流域其他民族和他们的信仰,但都只是不深地涉及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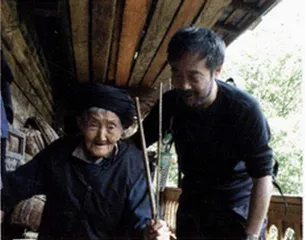
田壮壮与104岁老人在一起
总觉得田壮壮不会就这么完成了对一个地方的记录。他的第一部电影《红象》就是在云南拍摄的,而且4年前就开始策划了。在看片后的采访中,田壮壮回答了这个疑问:《德拉姆》只是《茶马古道》的一部分,它就是一部“印象式”的片子,计划中,这个题材要拍20个小时,在其他部分中,他会就某一个部分深入拍下去。宣传材料中也提到了另两部更具体的片子:《朝拜拉萨》和《马帮·古道》。即使是这么一个印象式的东西,也有些东西很打动人,104岁的怒族老人卓玛用才一生的经验之一就是“一定要拿得起就放得下”。一句人人都会说的话,从100多岁的老人口里说出来效果自然不同。

《马帮·古道》
初看《德拉姆》,第一感觉是画面极其清楚,这部片子是用高清数字摄像机拍摄的。但国内几乎无数字电影院,如果要进入发行,势必要走一道转胶片的手续。在记者们询问影片发行时,估计他们的心里几乎都有了自己的结论:这样的电影挣钱很难。田壮壮说他不排斥商业电影,但也说自己这方面做得不好。
看来田壮壮并没有把发行放在第一位,他淡淡地说拍这样一部电影对他来说不是个了不得的负担—这部片子的成本估计在200万人民币以上,拉来的投资。田壮壮在拍摄手记里说:“我们想将这个地区今天的生存状态进行拍摄记录”,记录下“这块土地上,为今天的文明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是文化。林茨在《福音谷》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20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对“文明”和“文化”作过有趣的区分,例如“相对而言,城市代表文明,乡村代表文化;集中代表文明,分散和多元化代表文化”等等。《茶马古道》将在这个地方被文明同化之前,用影像把现状记录下来,这是影片的第一目的。我们可以在((德拉姆》里看到最本色的马帮,女人和小孩会为自己家死了一头骡子而哭泣。这些远不是游客在丽江的四方街上跟穿着一身白的马帮合影时所能了解的。
以前因为《小城之春》曾经采访过田壮壮,问他10年没有拍电影怎么生活,他说帮朋友做点事情呗。这期间众所周知的是,他曾帮助过路学长等年轻导演。我想那10年他在很杂地修炼。看完《德拉姆》,在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他是否有上北京电影学院带研究生的意愿,他承认确实有这件事,同时淡然地说:“我怕误人子弟。”他是一个自负又自信的人。
也许是因为上述印象,包括他拍摄围棋大师吴清源的计划,我总觉得田壮壮在《茶马古道》里还有一些个人探寻的意思,探寻的是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我想他拍摄《茶马古道》决不单是为了记录什么,而是为了他提到的“和谐”—“你生活得快乐还是忧伤时挥之不去的情结”,而“自信祥和,愉悦,是那里原住民族的灵魂”(田壮壮《笔者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