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的交通阻挠我所有的梦
作者:朱文轶(文 / 朱文轶 庄山)
路是否少了?
“道路资源不足是中国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所所长钱少华提供的数据证明,到目前为止,我国城市道路用地在城市面积中占的比例处于较低水平,平均只有不足10%,北京也仅达到10.4%。而美国平均占到32.8%,其中纽约占35%,华盛顿占43%,洛杉矶更是占到50%。欧洲平均水平在21%左右,其中伦敦23%,柏林26%,巴黎25%,亚洲相对水平比较低,但日本东京占15. 2%,大阪占17.2%。

(李钺/象牙黑工作室)
然而,同样存在的一个现实是,我们机动车的拥有率也处于低下水平,如果按照这样可比性并不强的数字推算出一个结论似乎有失公允,相比之下,“分析道路布局是否合理可能更有价值”。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所总工、首都交通规划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马林说
缺少“单行”的城市
作为皇城的北京,先天性的城市布局锁住了城市规划者的建设思路,而形成的“路网稀疏”的道路格局给交通管理设置的最大难题就是不便组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员学术顾问、首都交通规划委员会专家李康对记者分析说:“北京的路网处在一种非稳定结构,主干道多于次干道,次干道又多于支道,正好是一个倒置的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主干道一堵,车根本就迂回不出去了。”“另外,路网密度大,如果次干道多于主干道,你就有大量可以组织支配的道路资源。”

在私车、公交、自行车三分天下的情况下,有限空间相互侵占,交通更无序(陶子摄)
清华大学交通工程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化普考察过曼哈顿与墨西哥,他说,“它们的交通井然有序都得益于路网稠密,道路分布均匀合理。在曼哈顿的长形岛上,纵向为路,比较宽,宽的地方有11条,不到300米就一条路。横向为街,比较窄,大多是单行道,每步行一分钟左右就一条,从南到北大多依号排列,总共约有300多条。城市的街道构成标准的几何网状图形,由于这些简单而科学设计的街道纵横交错,便于组织单向交通。墨西哥城也一样,主干道的间距是300米,路网密度高,大量组织了单向交通,你在墨西哥城看不到非常高大的立体交叉。”
“单行模式下节点多,却易通行,而我们的节点却往往是大并且路况复杂、交叉严重,不利通行。”陆化普说,“单行的优势意味着大大减少冲突点。用我们的专业术语,两车交叉,两车分开分流和两车合流,这都属于冲突点,单向通行这种组织形式会大大减少交通冲突点,从而不但能提高车速,还可以减少交通事故潜在发生的可能性。一般来说,单行线比双行线提高车辆通过量50%至70%。”
北京路网的格局设置等于放弃了这种优势而有效的交通组织方式,北方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杨浩对记者说:“路网密度小组织单向交通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路宽,它的绕行距离过长。我前方到了目标,看着它就是走不到。你要过一口到下一口犹豫,口与口之间距离很大,走了很多无效的车公里,无效绕行距离增加了,就很失败,而且行车的安全性也难以保证。”
取而代之的方案之一就是用庞大的立交桥来解决大路口出现的堵塞,杨浩说很少有城市像北京一样在市内修如此多的立交桥。为什么要一个接一个的修下去?张敬淦形容为“立交桥强迫症”,“因为修了一处,必定要接着修下一处。70年代西单和东单堵塞得厉害,便有人建议在这两个地方也修立交,我坚决反对。因为西单修了,车流一下子就到了六部口;东单修了,车流就到了王府井南口,等于把一个地方的压力传递到了另一个地方。”“西单路口的问题最终通过一个小细节解决了,就是在路口显示‘禁止左转弯、右转弯’,并通过交通标志指出往前一点右转有一个胡同,在那里可以右行和左行。”

无奈的等待(photocome)
北京城最早的设计者之一、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说他在参与1992年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制定时曾有过一个想法,就是在二环路以内,打通死胡同,不能走车的胡同应稍加拓宽,使胡同成为纵横交错的单行道,在二环路以外地区,一定要在大约二三百米见方的街区都设有双向车道,要推倒单位、机关大院的院墙,使楼房与楼房之间都有可行车道,这样对加密路网起到补救作用,“我在调查中发现,二环到西单,很多车走胡同,我们的胡同大约有6米左右,而国外很多城市7米宽的街就可以开双向公共交通线路,胡同为什么不能利用呢?”“城市要以楼为单位管理,使所有道路成为公共资源,不能圈地为牢,使大片的街区阻隔交通。”
人车混流的现实
今年初,北京市城调队对城八区2000户居民家庭调查,被调查者对交通工具的选择,“29%的人乘坐公交车和地铁;31%的人骑自行车;22%的人开私车;10%的人乘出租车;8%的人步行”。人车混流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交通现实。马林对此的解释是:“在中国特色的交通结构中,价格因素其实非常关键,交通出行成本在出行工具的选择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举例说,上海今年取消公交车的月票,发给个人公交补贴,这一政策公布当天,上海乘坐公交车的人次从1000万锐减一半。…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居民每天的出行距离大约在6~8公里,在这个距离内骑自行车需要20~30分钟左右的时间,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则要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所以很大一部分人仍然选择自行车。”
而几年中,北京市机动车道越修越宽的同时,行人和自行车行道被越挤越窄。“过去北京的街道机动车道、自行车道和行人道都有较合理的分配,而且行人道比较宽畅,行人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张敬淦说,“现在的交通政策一直是在考虑机动车,包括长期以来的‘畅通工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牺牲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利益来实现机动车辆的畅通。在道路建设和管理者眼里,交通问题是机动车带来的。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在私车、公交、自行车三分天下的情况下,人为地剥夺一种交通工具的空间,反而会带来它们对有限空间的互相侵占,让交通更无序。”
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副局长、总工程师段里仁分析说,北京宽大的路面更吸引了人流与车流的混杂,“每个节点尤为明显”,“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30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就有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的后果。”
环路好不好?
在城市结构限制的被动前提下,俄罗斯学者发明了“单中心+环线”的城市交通解决方案,然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城市都尝到了无可奈何的滋味,北京“摊开的大饼”甚至被李康比喻成了“引狼入室”。他感觉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于:“交通规划在被动追赶城市规划的进程中疲于奔命,本意在分散市中心人流的住宅小区一个个变成了出不来进不去的“卧城”
上了环路的套
在“以‘单向交通’为城市主要交通经脉”的可能性被否定后,北京选择了“环路包围城市”的道路格局。张敬淦说,决策者的用意在于“打通两厢、缓解中央”,“减轻城区压力”。修建环路的动力异常清晰,按计划,到今年六环通过,北京环路的总长将达到431.3公里。段里仁说:“这是无人能比的,国外很多城市像东京规划的环路是三条,一共是318公里,但目前只是规划,即使到2011年,三条环路依然不能全部通车。巴黎现在通车的环路只有一条,他们也规划了三条环路,但迟迟不能全部通车。伦敦也只有一条快速环路,将近200公里。”

节日出行,有限的几个进出城路口此时几乎都成了隘口(程铁良摄)
而环路唱主角和环路加上城区密集路网的效果却截然不同。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所总工、首都交通规划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马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环城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过于集中地修建环城路,因为如果在环线建设中不注意的话,很可能就会使城市的放射性出口大量减少,“北京的二环、三环和四环路修好后,城市中心向外就被限制在有限的出口上,理论上原来是可以有无数个出口,现在只能集中在这几个固定的点上。这使得每一条环路几乎都成了一道围墙,进出城的路口大大减少,每个方向有限的几个进出城路口也几乎都成了隘口。”
“多层环路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妨碍人流内外有效流动。北京现在的交通堵塞点主要是在二环、三环、四环路的桥下。因为,在环路上封闭路面,消灭红绿灯,提高了车速,但十字路口应有的拐弯、调头功能却都让桥下路面承担了。所以,桥下总是堵得一塌糊涂。”马林认为,造成北京这一问题更为突出的原因在于环线与辅路是并行的,这样使环线与辅路间的干扰非常大,环线的车出不来,辅路的车也进不去。他说:“广州的环线修好后对广州的交通改善非常大,原因是它的环线是高架的,没有损失原来地面的道路和出入口,因此增加了整个道路的通行能力。”
杨浩的一个课题是研究环路的实际效率,他说,封闭性环城路从表面上提高了某一方向路面的车速,但从整体效率上看却是在浪费资源和时间。环线建成后是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大容量通道,与其他的道路相比,它的行车条件大大改善,但与此同时,它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愿意走环线,哪怕是绕一点也愿意。另外,由于直接进出城不畅,也迫使很多车走环路。走环路必然造成车辆无效占有路面的时间增加,带来行车里程和时间的极大浪费,这样使交通运输效率大大下降。“据测算,走一个圆的半径比走圆的直径要多出1.6倍的路程,而走方形的边就要多出两倍以上。原来从A地到B地,可能只需要走直线就行了,但现在从环线上绕一下,就可能使原来的3公里路程增加到现在的5公里,从而产生两公里的无效运行。交通效率的低下使得尽管交通量很大,但有效的交通量却并不大。”
“按照当初的设计思路,环路应起到跨区交通的作用,即以10公里以上行驶距离者为服务对象。但实际上我们调查的结果是,目前环路上两公里以下的交通却占到24%左右,短程交通的大量存在,造成了车辆在环路上频繁进出。”杨浩说,这与北京交通路网东西向和南北向干道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东西方向有长安街、平安大街等干线,而南北方向却缺少主要干道,因此,东二环和东三环、西二环和西三环事实上承担着南北主干道的作用。记者从交管局交通指挥中心获得的信息显示.高峰期间南北贯穿市区的交通流70%集中这几条环路,流量最高时达1.6万辆/小时,是设计饱和流量的1.8倍,导致二环、三环路在没有任何交通意外的情况下依然经常发生拥堵。“因为流量过于饱和,在与东西向干道交汇的路口车流汇集,成为长安街、平安大街的出口瓶颈。”马林说。
“卧城”的交通尴尬
张敬淦说,针对城区的饱和开发,1 992年他起草北京规划方案上报国务院时提出了两个战略转移,“一个是城市建设重点从市区转移到远郊区,另一个是市区建设重点从外沿拓展转移到调整改造”。
然而这个转变并没有真正落实,首都交通规划专家委员会马林说:“所有的功能区还都在依托市区建设,而因为级差地价,居住区则开始远离市区。”“其实这并非是在分散城市功能,而是单纯分散居住人口,你把人分散出去而城市功能没有分散,可以想见,形成了几十万人从望京从亦庄还是要往市内跑,这样就出现了潮汐式交通,早晨向心交通,晚上离心交通,而且十分踊跃,交通压力很大。”
这种依附城区的功能区往往带来了新的节点拥挤。马林说:“比如金融街,金融街的拆迁迁出了40万左右的居民,而建成后金融街的工作人数将近100万,流动办事人员在150万左右,这会是一个多大的交通量?按照规划,这些人的车位必须保障,每一万平方米建筑,车库面积必须达到可以容纳60辆汽车的标准。但另一方面,周边路网设施跟进却很难顾及。类似金融街这样的商务集中地现在分布得到处都是。”
“如何真正实现大城市的多中心化,还是一个更大的工程。”马林说。
道路崇拜及局限
在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210万辆的北京,11月1日最醒目的新闻无疑是全长98.58公里的五环路全线通车。无论交通部门的管理者还是超过200万的私车主们对它都寄予重望,尽管一个月前北京市交管局曾并不乐观地将北京市交通状况定性为“过饱和状态”。在多数人看来,这条目前世界上最长的环线至少能在相当程度上疏导骤增的交通流量,一扫近日来城市拥堵的阴霾。在当天的通车现场,一名参与剪彩的首发公司负责人信心十足地向记者描述这条环路给予北京交通的未来,“它连通了北京的7条放射性高速路:京开、京石、京津塘、京沈、机场、京承和八达岭以及1条京通快速路,不仅实现高速路间的‘高速对接’,而且也实现了除京沈和正建的京承高速外的各高速路到三环路的快速连通,许多节点将变得更为通畅和快速。”“北京道路‘环路加放射路’的规划正在逐渐成型。”

宽阔的道路是否能解车辆增多所带来的一切麻烦?(photocome)
相似的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十年前。北京也是国内第一条全封闭、全立交、没有交通信号灯的城市快速路—二环路竣工通车。“在经历了北京城80年代后期一段痛苦的拥堵后,当时有决策者称‘十年内不会发生大的堵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副局长、总工程师段里仁回忆。的确,很少有人相信这样精心规划的宽阔道路会发生拥堵。但堵车很快成为现实,并且紧随而上规模更大的三环、四环同样在劫难逃。但是,人们对道路一如既往的崇拜让他们笃信,宽阔的道路能解决车辆增多所带来的一切麻烦。北京交委会向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80年至今,北京市道路长度和道路面积的平均递增长率仅为1.6%和4.76%,而同期北京机动车数量以平均年递增15.9%的速度增长,北京的人均道路面积已明显少于其他大城市。“2002年,北京的人均道路面积为4.7平方米,少于上海的6平方米、东京的13.5平方米,伦敦的24.5平方米。”段里仁说。
这样的数字很容易推导出道路建设滞后于车辆增长的结论。接下来,最直接的政策选择莫过于“修路”和“限车”,然而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在北京城最早的设计者之一、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记忆中,无论道路与车的比例发生过怎样的变化,北京“堵车”由来已久,“80年代以前,北京就是早上出城难、晚上进城难。90年代以后的情况是高峰期进城堵出城也堵;这两年又变成早上进城堵晚上出城堵。…以前我每天中午从单位回家吃饭,一天一共要坐4次公交,行程50公里,经常堵的路段是新街口豁口,记得最长堵过两小时。二环封闭后的大半年这个地方好多了,但现在还是堵。”“长安街先后拓展过4次,成了举世无双的8车道120米宽路,结果到现在平均车速只有14公里左右。”“1956年,打通‘汉花园’,结果经过沙滩的人流车流骤增,又花大力气改造北海大桥,将坡度改小路面展宽,最后还是堵。”“70年代在交通压力下,打通前三门大街,打通朝阜大街,结果发现越拓宽越堵,因为它把流量都吸引过来,而前方总有节点与瓶颈。而主干线拓宽又损害了原来的许多可通行小路。”
看上去,这个巨大城市的“周期性”堵车症正验证着交通学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当斯定律”(Downs Law)—这个外国术语的意思可以被精简地表述为,“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其诱发原因,北京城建设计研究院高工刘迁解释为“三头齐发原则”,“如果在高峰时间特别拥挤的地段一旦大有改善,就会导致三种情况,而使改善全被抵消。或者汽车驾驶者原来走别的路,现在都集中在这里;或者汽车驾驶者本来在其他时间行车,现在同时集中在一起。另一种可能是汽车驾驶者本来乘坐公共交通,现在驾车通过这一改善地区。”刘迁说,既然供给永远无法满足需求,那么就要在有限的供给下对交通需求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不是通过单纯的‘建’和‘限’来解决,而是一种综合的系统性工程。”他认为,汽车总保有量不能限制,而道路机动车总量必须得到限制,“只用于上下班的私车和一天24小时在路上行驶的出租车对资源的占有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外有数倍于我们的车,但却没有我们如此严重交通问题的原因之一。有关部门曾做过统计,北京小轿车年行程公里数为4.7万,美国是1.9万,英国为1.25万。”“车辆的拥有和使用要分而视之。”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咨询专家李康接受采访时称:“现在的问题在于,道路的需求、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双重失衡,道路处在一种非稳定结构。而公共交通、轨道交通严重滞后,覆盖不到所有的人口,很多人在步行距离内无法很快到达轨道交通站点,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交通的自调节和自适应能力就很弱。”“拥堵,因为人们的选择性已经太小了。”
世界各大城市解决拥堵的各自之道
纽约:从郊区到达市中心都是直达的放射性线路,阻塞状况并不明显。私车一律停在郊外。到纽约曼哈顿的上班族,是从家里开车到市郊地铁站或火车站,再换乘进入市区,然后在市内乘公共汽车、地铁或出租车去上班、办事。曼哈顿的许多街道,只有持特殊牌照的车辆才能停车上下货和上下客,其他车辆不得停放,否则即遭罚款。

华盛顿:公交车送官员上下班。不仅工商人士不能驾驶私车进入华盛顿的办公楼,美国联邦政府官员也不得驾车出入华盛顿。官员们大多不住在华盛顿市内,而是住在与华盛顿特区相邻的三个州的小镇上。如果他们每天开几十公里车到华盛顿上班,通向华盛顿的几十条公路都会堵车。为此,联邦政府拟定用公交工具接送代替个人开车的计划,使部分人放弃自己开车,改由公交车接送。

巴黎:公交优先,轿车分单双号入城。由于私家车急剧发展,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巴黎的城市交通几近瘫痪。于是,法国政府开始下大力气重点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如今,巴黎设置了480多条全天或部分时间禁止其他车辆使用的公共汽车专用道。对于小汽车,巴黎市政府规定,采用分单双号车牌形式来限制轿车进城。市中心的就业功能被疏散到郊区的卫星城镇中,缓解就业与居住之间的不平衡。

东京:地铁至上。东京人的家用汽车平日放在车库里,上下班乘地铁。一则是因为乘地铁才能准时上下班,二则是公司里只有总经理和董事长才有车位。截至1999年,东京圈40公里范围内有高速铁路13条,地铁10条,高速公路9条,短距离轻轨2条,每日负担2804.5万人次的客运量,其中高速铁路占61.4%,地铁占26.3%,公共汽车占6.7%,其他占5.6%。交通路况电子信息牌实时显示路况信息,以供交通人员疏散拥挤路段和人们选择行车路线。

伦敦:停车费抑制轿车。当地政府发出交通白皮书公告市民,为了限制轿车数量,减少堵车和空气污染,从2000年起提高停车费用,同时城市内原有的各大公司、公共场所的免费停车场一律改为收费停车场。从今年7月份起,伦敦又规定,进入拥挤市区必须额外收费。

香港:得益于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香港人口700万,截至2000年12月行车道路的总长度只有1904公里,许多不到20米宽的车道上,跑着各式机动车辆,但仍能做到运行顺畅。香港的道路大量实行单向行驶,驾私车的人从此地到彼地也许直线距离很近,但要兜很大的圈子才能到达。所以香港的交通很大程度上依赖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其公共交通服务种类繁多,市民可按快捷、舒适及方便程度,选择各自心仪的出行交通工具迅捷到达。每天,地铁、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出租车和渡轮等交通工具秩序井然,载客超过1000万人次。



多伦多:行人地下通道网非常发达,即使在暴风雪的恶劣天气,人们也能通过地铁、城铁和公交车安全舒适地抵达目的地。
维也纳:鼓励人们弃私车坐公车。政府为公共交通支付高昂的津贴,再用高昂的燃油税、停车费和严格的停车规定,来限制私车出行量。

新加坡: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全国约80万辆汽车(其中约50万辆为小汽车)在城市有序分流。新加坡之所以交通顺畅,主 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陆路交通立体网络;服务规范,管理严格;独创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及拥车证制度,有效控制市区车流量及车辆总体数量。
私车是否多了?
“限制私车”,“提高停车费”,一系列针对性很强的政策意向让北京人在更高的层面上感到了道路拥堵的紧张。那些令外地人一见就莫名敬畏的宽阔马路究竟能容下多少辆机动车?不同的专家给出了从1 00万到700万落差悬殊的数字。而交通规划专家的意见是:“数量并不是参照的标准,重要的考虑在于不同出行方式对城市空间消耗的差别。”如此计算,与承担公共交通任务的公车和轨道交通相比,私人汽车注定成了罪魁祸首。然而,不同个体都有选择快速、舒适出行的权利,“限制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手段,现实是我们还没有能够提供更好的选择。”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中心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刘治彦认为,“我们应该给不同层次的出行者都提供更好的出行享受”
谁占了城市的路
“凭什么限制私家车?哪条堵车的路上不是大公共后面排着长长的车龙?大公共占用道路要比小汽车大得多,要限制也应该先限制大公共的数量。”对于私家车主的普遍质疑。而研究者的解释是:“交通管理者要考虑的首先是人均道路的占用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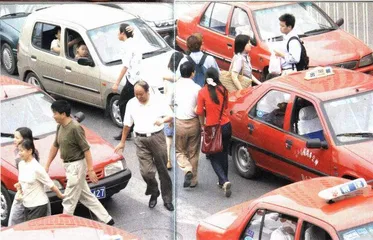
人车混流是中国特色的交通现实(photocome)
根据北京市交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02年底,北京道路总长18759公里,其中城市道路4400公里,比1997年增加了近800公里。而同时,机动车数量也以每年将近20%的数量增长,小客车出行所占比例由1986年的6%上升到了23.2%。自1994年到2000年的6年时间里,公交运营车总数由7819辆增加到15445辆,增长97.53%。这样下来,“北京的道路有90%左右处于饱和和超饱和状态”。
谁占用了更多的空间?刘治彦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标准公共汽车长10.5米,宽2.5米计算,在静态时它占用的道路面积是26.25平方米,在平均速度1 8公里每小时左右时,车头间距22.52米,那么占用的道路面积是78.82平方米。小汽车长度5米,宽1.8米,在静态时占用道路面积是9平方米,以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车间距25.97米,占用道路面积是90.9平方米。但是,当加入公共车80人,小汽车4人的载客量数据后,无论动态还是静态,公共汽车所占的道路资源都相对比较少。其中,动态状况下占用的道路面积比为:公交车:小汽车:自行车为78.8:90.9:6.76。这就意味着运送相同数量的乘客,小汽车占用的道路资源是公共汽车的23.19倍。
“小汽车也应该区别看待。”李康说,“占用多少道路资源,日行车公里数才是最关键的指标。一量出租车每天跑将近300公里,而一辆私家车无论如何是无法比较的。”
公交系统的薄弱让人们不得不选择其他的替代物,在私车之外,出租车在北京广受欢迎,但过量的出租车却成为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节点。段里仁指出,与世界上一些大城市相比,北京市的出租车数量太多,目前已经达到6.7万辆。美国纽约有出租车约1.6万辆,香港地区人口是北京一半,出租车约1.8万辆,“北京出租车占路面交通量的30%至40%,平时白天空驶率约为37%,晚上空驶率为40%至50%,这样便无效占用了道路的面积,如果出租车空驶率能减少20%的话,整个交通量就能减少8%。”
公共、私车与出租之间的选择
没有人会质疑公共交通的好处。一辆公共汽车的承载率可以是一辆小汽车的几十倍,一列轻轨可以完成1000辆小汽车的工作。对于某些特定的行程,公共交通可能是最快的出行方式。但公交的吸引力却在北京的现实中明显下降。北京市城调队汪斌告诉记者:“今年的调查中,公交和地铁的交通分担只有41%;而不到十年前,公交的分担率曾达到80%。从现在私车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更合理的结构应该是有60%的人出行选择公共交通,20%的人选择小汽车,20%的人骑自行车出行。”
公共交通被很多人放弃,在北京交通大学专家毛保华看来,并非全是私车侵占所致,“人车混流的道路状况使公交系统很难做到整点,公交线路虽然被专门划分,但绝大部分路段,公交要和私车、出租车抢线,道路受到干扰把握时效上就有难度。”“如果以准点率和舒适度来选择交通工具,现在状况下的公交作为一种交通方式的确不具备吸引力。”
“另外,公交车的端点还远没有考虑到居民生活的便利性。”段里仁说,在规划西直门立交桥的时候,没有把行人考虑进去,在西直门附近有20多个公共交通线路,没有进行有效整合,相隔很远,“一次我到西直门地铁下车,找了半个小时也没找到我要去的公交车站,这种情况下,当然谁也不愿意去坐公交车了”。
公共交通线路规划的不合理是另一个问题,段里仁向记者举了个例子,“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市区的西北角、北京火车站在东南角,连接两点的公交车103路已有数十年,其路线是斜穿城市,经过数个双向通行交叉路口和多次左转弯。这样的安排,说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其实,该线路是由多个短距离的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折合而成的斜穿城市路线,并没有真正实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由于该路线要经过数个双向道路的交叉路口和多次左转弯,即造成和经过许多堵塞点,结果,它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斜穿布局路线能减少时间的预想实际上是落空了,等一辆103往往要用上15分钟时间。”还有问题就是公共交通之间站点连接给倒车带来的不便,地铁、轻轨、普通公交之间的连接都十分困难,以致彼此倒换非常不便,要走很多路浪费很多时间,尤其在冬夏季节,给倒车者带来不便。如果是倒车带来长距离走路而且不便,人们也就不会选择公共交通。另外,也有人提出,对私车拥有者而言,进城改乘公交,也没有相应的可转换考虑。
毛保华认为,在北京目前情况下,地面发展公交虽然能有所缓解拥堵,但收效甚微,“因为我们供需差距实在太大,地面网络的先天缺陷,难以改变的人车混流现实,单靠地面交通解决一定行不通。东京的地下交通承担着全市80%的流量,整个城市拥有400公里的地铁网络,假设地面交通全面瘫痪,轨道交通完全可以解决问题。而我们对道路交通系统的依赖性过强。”
北京道路历史及现实选择
北京规划局高级顾问张敬淦1949年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作为参与北京城市规划的第一批专家,他初次打量这个城市的时候,发觉相对其他城市来说,北京的道路规划会是一件“难办的事”。“紫禁城居中,中轴设计当然是老北京城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却给交通带来了先天的不利。”10月31日晚,张敬淦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首先是内城九门之间相互不通,东直门、西直门不通,长安街也不通,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平时封闭,老百姓走路都得绕行。再从道路系统来看,干道少,胡同多,这种街道布局走人还能勉强对付,一旦有车,问题马上就来了。”

(象牙黑工作室)
张告诉记者,五六十年代交通最紧张的是西直门,“西直门通往颐和园、八大学院和香山,交通量最大,当时是人挤人,车挤人,几乎每天都发生交通事故”。对机动车交通来说,北京的先天不足是路窄,因此在规划者眼中,一个急待发展城市的当务之急便是开道辟路,“先是从城门开豁口,从东往西开了六个豁口,分散交通流量,最后才拆城门。”“接下来,就是西单往北、菜市口往东干道的拓展”,“拓宽道路几乎是北京交通规划的指导思想。”
让道路越来越宽的还有北京的小区和大院建设,张敬淦说:“1955年,苏联专家组帮助北京进行城市规划时,提出了以‘小区’为基层单位,以现有道路为界,建立30~60公顷的大型住宅小区。当时的考虑是基层单位大可以设施齐全方便居民,但带来的问题是面积大了,路口间的间距就拉大,形成了目前北京路口与路口之间少则五六百米,大到1.5公里的局面。”“当时没有想到它的交通弊端,并且认为这样的规划能减少节点,减少红绿灯,加快车流速度。于是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道路红线规划一直执行至今,按其要求,城市干道宽度为60至80米,次干道为50至60米,支路为30至40米,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700至800米一条,这给北京‘宽而稀’的路网定下了基调。”
而事实上,路远不是想象中的越宽越好。北京市规划设计院高级建筑师杨振华认为:“四车道的马路,如果中间车道的通行能力为1,那么内外两侧的车道的通畅能力只相当于中间的0.65,呈递减关系。它的通行能力远小于四条单车道通行能力之和。”
杨振华说,市区道路网容量,除了要有足够的道路长度和道路面积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千路和支路之间合理的比例关系,及其网络的连通性等条件。仅仅着眼于几条主干道,解决的只是点和线的问题,真正需要解决的则是“路网”—也就是面的问题,“目前北京市6米以上的道路密度为3.52公里/平方公里,道路面积与总面积的比例不足10%,国际标准为20%以上,而一条道路要保持畅通必须达到这个水准。”张敬淦说,“大路朝天”给北京带来了致命的交通顽疾,“本身用于道路上的土地已经很少,而这些道路又都主要集中在几条主要干道,整个城市的交通无疑会严重依赖这些主干道,这样陷入了交通量越集中,路越嫌窄,就越要拓宽的恶性状态。”
庞大规模的小区和大院又反过来加剧了这种交通紧张,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中心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刘治彦认为:“在北京,任何一个小区、单位,哪怕只有一座楼也必然会有围绕四周的围墙或路障,即使有门也只供本单位、小区车辆使用,在设计中,这些区域是无法纳入城市交通的,所有的出口都面对大街,上路的车辆都全部集中在城市干道。一个事实是,在高峰时一些小胡同往往比大道的通过性要好,这种地块分割无法产生一个更有效率的路网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