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防洪策略的新出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金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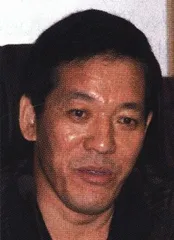
张志彤

7月1日晚,淮河防汛办公室紧急会商防汛形势
三联生活周刊:您搞防汛工作二十多年,“洪水”的概念有什么变化?
张志彤:我们对洪水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去考虑自然因素多了些,其实洪水本身是由自然因素造成的,但灾害大小则在于人为的管理。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一直在修筑堤防防止洪水泛滥,一方面增加了安全感,一方面为什么当有更大的洪水发生时会造成灾害?
张志彤:我们过去强调工程建设多,这是必要的。但反过来,每个工程都有一定的标准,洪水超过了这些标准怎么办?无论从经济意义还是从其他角度考虑,洪水都可能超过工程的防御标准,我们不能无限制地提高防洪工程的标准,其实在经济上不划算,更不可能,所以我们在思路上有一个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国家层面的决策变化?
张志彤:从大的意义上说是我们国家防洪思路的转变,简单地说,我们要从“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洪水管理包含了控制洪水的内容,但后者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说穿了,“管理”就是承认洪水的风险。过去我们是“战胜自然”的思路,事实上人在自然面前是不可能完全战胜的,改造自然也是有限度的。我们要承认这种有限性。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很熟悉的一句口号是“严防死守”。
张志彤:“严防死守”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洪水来了,我们的堤防就是这样,怎么办?需要一个进退有序的做法。过去我们对防洪有一些零星的想法,今年1月初水利部汪恕诚部长在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观点:洪水管理。今年的淮河防洪就是新思路的第一次运用,而且成功了。
三联生活周刊:确定淮河今年防洪“成功”的尺度是什么?
张志彤:淮河今年防洪的成功在于:政府有效的管理和防汛的科学调度。比如我们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这一次在淮河大水中就有体现,在安徽大堤上就竖着责任牌,张三、李四的名字都写在上面,这些都是应急机制的运用。再比如分洪撤离,在我们没下达命令前,省里就已下令让那些有可能用到的行蓄洪区的老百姓撤离,最后再清一下场,所以安徽转移了几十万人,没有死一个人。民政部门运帐篷,老百姓的生活、饮水、卫生防疫都在有序进行,不再显得很忙乱。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今后的防洪中,达到和谐相处需要的外部保障是什么?
张志彤:我们会实行一系列的制度,规范人类的社会活动让人适应自然。比如防洪评价制度,如果在防洪区建个厂子,首先要看厂子对防洪本身有什么影响?它的防洪风险度以及应该建什么相配套的防洪设施等等,所以我们说要管理规范化。规范化要靠法、靠制度。我们现在对全国凡有洪涝问题的地区搞洪水风险分析,制订洪水风险分析,不断完善包括江河防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防台风预案等各种防汛预案,增强风险意识。从整体上来讲,我们讲是“五化”:工程标准化、管理规范化、洪水资源化、技术现代化和保障社会化。
下游:根治洪泽湖:淮河洪水的未来出路
“现在为了保洪泽湖,几乎整个淮河沿线都变成了蓄洪区。不解决洪泽湖问题,任何治淮措施效果都大打折扣”
救命的工程

洪水在一些城市已成为生活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7月18日,站在淮河入湖口,江苏盱眙县水务局局长姚玉祥对记者说:“现在的出湖水量已经大于入湖水量,洪泽湖出湖总流量一直维持在12000多立方米/秒,而淮河上中游入洪泽湖的总流量最大时达到14500立方米/秒,超过1991年11000立方米/秒的入湖流量。”
淮河第一、二次洪峰下来的时候确实让姚玉祥紧张了一阵子,虽然早在7月4日23时48分,江苏省第一次正式开启6月底刚刚建成的入海水道,为即将来到的洪峰准备了库容。但汹涌而来的洪水还是令洪泽湖蒋坝水位7月6日超过13.5米警戒水位,在14日15时出现了14.37米的今年以来最高水位,比1991年的最高水位高出0.31米。
“没有入海通道,今年灾害损失肯定重得多。”姚玉祥一再强调自己的观点,盱眙地处淮河中游的尾段,淮河从这里分成三条支流进入洪泽湖,而盱眙县境内全长70公里的淮河干流水位落差达到3.5米。一方面,水位落差对淮河洪水的销能起到了极大作用,但同时,水量控制也直接关系到洪泽湖的安危。“现在看来,洪泽湖的排水还不能满足大的洪水,我们不能加大洪泽湖的压力。”为了确保洪泽湖大堤,盱眙境内的行洪区域开始使用,截至7月17日,盱眙县全县受灾人口达到53万余人,姚玉祥说:“感情上讲上中下游要互相理解,也必须有上下游的整体观念。”
入江入海的争论
洪泽湖排泄不畅一直是困扰治淮工作者的难题,而几百年来的事实表明,这正是淮河流域灾难的根本所在。说到这一切,每位研究者都把黄河当成了罪魁祸首。
洪泽湖在淮河中下游的交接处,横断淮河,集水面积占到淮河水系集水面积的83%,无论从蓄水功能还是排水能力上说,洪泽湖都称得上淮河流域的枢纽,“古老的淮河本来是安全、平静的”。王玉太介绍说,自从1194年黄河南堤决口夺河以后,打乱了淮河流域水系,使淮河失去了自然形成的独立入海通道。同时,由于黄河带来的泥沙淤积,至1855年黄河改道北流之时,给淮河流域留下了土地沙化、河道淤塞、出海无路、入江不畅等心腹之患。
淮河水在被挤兑后自己选择洪泽湖作为出路,然而,由于泥沙的淤积,洪泽湖的湖堤比上游蚌埠河堤高5到6米,河底比下游里下河地区地面高10~11米,上游洪水到这里需要“爬坡”,而对下游来说,它俨然又成为高悬的威胁。
历代专家都在为淮河水找寻出路,而摆在他们面前的主要的思路就是在入江、入海选择上的权衡。治淮先驱张謇于1919年提出了著名的“七分入江、三分入海”的方案,即按7000立方米/秒流量入江,3000立方米/秒流量入海,并将2500立方米/秒水量蓄留洪泽湖,从而妥当解决淮河当时最大水量12500立方米/秒的蓄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在入江、入海的问题上最终达成的妥协还是“入江为主,入海为辅”。原有的入江水道经过历次整修,到1992年投入1个多亿,使设计流量达到12000立方米/秒,姚玉祥介绍说:“今年入江水道最高走到8940立方米/秒,因为下游的高邮湖水位已经超历史,入江水道的堤防也不能承受更大的压力。”
王玉太向记者解释,虽然入江水道比较现成,但不可能开得太大,一方面,需要考虑江淮同时发水时将面临长江水顶托的自然状况,而更主要的是考虑入江水道经过扬州、江都等经济发达地区,除建造成本高外,影响也太大。而入海水道经过的主要是人口相对稀少,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相比较之下,这无疑成了治理淮河一条更佳的选择。但入海水道设计多大流量依然很难得出共识,1975年8月的大水后,一些人要按照可能遭受的巨大洪水的想象来设计“万年一遇”的规模,但显然,技术和经济上的合理性都被广泛质疑。而开通的800流量的苏北灌溉总渠,王玉太认为是受了当时水文资料不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设计能力显然是太小了”。
1958年,江苏省把分淮入沂建设成洪泽湖洪水分流的通道之一,虽然设计了3000流量,但这条通道受到天气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有可能滴水不能进。
一系列的工程之后,淮河洪水的出路好像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经历了多次教训和抉择后,入海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淮河水利委员会80年代做出的规划中,近期目标是与苏北灌溉总渠平行,紧靠其北侧建成2000流量的入海通道,这项耗资41亿元、历时4年、今年6月底正式开通的工程让每一个人都感到“万幸”,它在今年的泄洪中最大流量达到1800立方米/秒,“相当于洪泽湖每天涨7厘米左右”。
回归自然的河湖分家理想
淮河入海水道西起洪泽湖二河闸,东至滨海县扁担港注入黄海,全长163.5公里。已经完成并发挥作用的工程使洪泽湖防洪标准从5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远期(2005年前)工程设计排洪流量将由现在的2270立方米/秒增加到7000立方米/每秒,而洪泽湖防洪标准也可进一步提高到300年一遇。王玉太觉得这样淮河就基本可以让人稍微放心了。
其实,无论是入江还是入海,在洪泽湖的治理过程中始终是按照“蓄泻兼筹”的方案实施的,回顾过去的工程计划,似乎总是在不停的修订过程中,这期间是否造成浪费一时间还难以做出判断,但假如用一些专家的“河湖分家”的观点来审视的话,过去淮河上的许多工程似乎都成了无用的摆设。林一山强调说:“1950年以来,没有看到研究根治淮河的办法,仍是延续着历史的错误道路,即只考虑洪水怎样进洪泽湖,而不考虑河湖分家,如果等到治淮的工程完成后,再考虑治本工程,已经完成的工程就可能大部作废。”
原淮委规划设计院总工王先达说:“河湖分家,是一项根治淮河的战略性工程,应作为新一轮淮河规划的重点。”持这种看法的人虽然有不同的设想,但他们共同的意愿是放弃对洪泽湖的完全依赖,调淮河之水直接进入入江水道或入海水道,使洪泽湖独立成为淮河真正的调蓄洪区,然而,关乎到下游3000多万亩良田灌溉问题的大湖又怎么可能轻易被放弃呢?毕竟,淮河流域旱灾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洪灾,蔡敬荀分析说:“其实河湖分家的原则是不损害洪泽湖的综合效益,主要解决淮河中游洪水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