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4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任田 陈蓓 杨不过 锡拉)
倒霉的rrrr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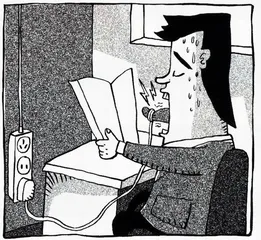
任田 图 谢峰
我是学西班牙语的,在大学里上第一节课就犯了难——因为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socorro”给大家练。这个词是“救命”的意思,应该相对比较popular吧!因此在老师示范之前,我自作聪明地寻思着大概和“撒苦啦”差不多,老师一示范才知道,天哪,原来学语言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上,是要挑人的。
难就难在这个“r”。这个字母在法语里叫小舌颤音,在西语里叫大舌颤音,总的效果基本相似于彭丽媛唱那句“得儿儿儿儿,呀得伊得儿喂”里的“儿”,对初学者难度颇大。在我们外院,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想认出学西班牙语的,就听他(她)说话像不像马打响鼻;区分学法语的,看他表达有没有伴随干呕的症状;寻找学德语的,则看他是否总倒抽冷气,“伊西伊西”个不停……
如果练不会这倒霉的“r”,哼哼,四个字伺候:劝其转系!就为这个该死的“r”,外院多少男生拍墙大吼,多少女生含泪苦喊。所以我说,虽然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但外语也是要挑人的,有些舌头死活颤不起来的家伙,即使遣送到第三世界的拉美,就算啥也不干,被狗追时喊声“救命”也要产生交流的障碍。
好不容易游刃有余掌握了一个“r”和两个“rr”的时候,才蓦然发现,会发“r”的人居然总被不会发“r”的人嘲笑,这是什么世道?在时髦肥皂剧《欲望城市》里,女主角卡瑞有个墨西哥的女朋友,她那不肯休止的夸张的“r”发音总被朋友们嘲笑,而她却毫不自知,依然“r”此不疲。
其实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像靠演《弗里达》大红特红的墨西哥女星塞尔玛·海耶克,人长得靓极了,前阵子和爱德华·诺顿闹情变,就被诺顿的前女友冷嘲热讽,说其实诺顿早想把她休了,就是因为听不惯她“r”个不停的墨西哥英文!还有莱昂纳多的前女友、巴西名模吉赛尔,常上男性杂志封面的主儿,性感得都没边儿了,据说和莱昂纳多分手的原因之一也是被人嫌弃有一口巴西音的“r”派英语……俗话说,傍上一个款爷并不难,傍上一个靓仔也不算难,难的是又款爷又靓仔都给她傍齐了,最后因为口音问题叫人家飞了,才叫得不偿失。
后来,我一位学法语的同学沾沾自喜地对我说:其实法语不用非颤个“r”出来不可,把“r”含到嗓子里就可以了,发出来反倒是巴黎郊区农民的标志,城里人都只做干呕的表情,而不发干呕的声音,遇到“r”,“喝”一下代过去就行了。后来我专门关注了美人苏菲·玛索的发音:“喝”的同时还伴有小舌微颤,她是农民?
去年在马里安巴
陈蓓
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文学系有一门课,叫拉片课,就是把大师的作品反反复复地看、学习和领悟。
当时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比较有优越感的地方,就是可以看到人们看不到的外国影片。拉片教室外有一个类似图书馆书目目录的影片索引箱,打开那些小抽屉,另外一个通往绚烂世界的天堂之门就被推开了。那时候我比较热衷于《E·T》之类的好莱坞影片,对伯格曼、安东尼奥尼什么的深刻老大叔没有兴趣,阿伦·雷乃也是这些大叔中的一个,《去年在马里安巴》就是他的作品。
据看过这部影片的同学讲,这部影片讲的是一对陌生的男女在偶然遇到后,女子一口咬定他们去年在马里安巴就已相识,并有过激情的假期,但男子却一头雾水、矢口否认。整个故事就是在探讨去年在马里安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到现在也不确定是哪位同学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更没法儿确定他的复述和大师原作之间到底有多远的距离,但可以确定的是,后来每当我们对一件过去的事情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又无法考证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去年在马里安巴”,这些事情包括谁谁失踪的那本书最后出现的时候是否放在上铺的枕头边,周三的专业课某人是否确实到场,还包括学期中的论文到底是我的同学没放在老师的桌子上,还是老师没收到……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大学的时候,有那么多“去年在马里安巴”的事件。
当然,这不表示我们对大师没有敬意,只不过表达敬意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同学为交论文,到我们宿舍来找“西区柯克”的参考书,进门就问:“这儿有西区柯克吗?”宿舍里遂有来串门的男生答:“丫拍广告呢,呼他吧。”而那正是全北京影视圈总动员拍广告挣银子的年代。
顺便说一句,在这个银子比电影更重要的时代,我还能想起阿大叔,是因为近日在街头小店里,惊见DVD版的《去年在马里安巴》,它悄然触动我心中对电影的激情和柔情,并心中暗惊:DVD盗版商的眼光真真是越来越专业,这么偏僻的片子也有市场,业余影迷水准直让专业人士汗颜,但后来转念一想,电影原来就是大众产品,那些认为电影是只属于少数人的艺术实在是某些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在做怪,武林里拳头大的说话,电影是买单的人说话,管他欧洲电影非洲电影,观众的口味才是至高无上。你何以确认现在被写进中小学生必读的唐诗经典,不是当年街头巷尾连包子铺的伙计也可随口而出的流行词句?但不知道为什么,事隔多年,我仍然没有买阿大叔的作品,仍然不打算知道去年在马里安巴究竟发生了什么。
恋人絮语
杨不过
我有个弱点:虽然不喜欢某些东西,一旦有人奋力地煽起情来总会被催出泪水。譬如倪萍阿姨和还珠格格。我总为这些眼泪羞愧,因为它们暴露了我低下的品位。
鉴于同样的原因,我这个对诗一窍不通的人,也曾熟读过一个外国人的诗。即使在应该反叛的年龄,我喜欢的也不是发狠的铁骨热血,而是发酸的情意绵绵。
“你不像任何人,因为我爱你。”
“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
“我会上山去给你采摘幸福的花,风铃草/黑榛子和满篮朴素的亲吻/我会善待你/如春天善待樱树。”
很琼瑶吧?我曾经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抄的就是类似的诗句,和它们做伴的还有三毛的话和许多优美句子。但他不是文学少女,他是巴勃罗·聂鲁达。
除去翻译的问题不说,以我浅薄的审美观来看,尽管自从高中后就羞于提起席慕蓉,但她的诗也不比他逊色,甚至颇有悲剧色彩和浩荡之气。
不过他那些流传开来的句子似乎都将他神圣化了,实际上还有很火爆的内容。
“你那委身于我的姿势就如同大地/我这粗野的农夫之体在挖掘着你/努力让儿子从大地深处欢声堕地。”
所幸最终落在儿子上,比起露水鸳鸯毕竟纯情多了。
听说他之所以出大名的诺贝尔奖,是因为除了写诗之外还是伟大的政治家。但我对他的政治生涯——被迫流亡海外、反法西斯、讴歌国际纵队——完全没兴趣,觉得这是游击队员而非诗人该做的事。我读过的仅仅是一点情诗。电影《邮差》里,他的力量被诗意地神话了,渔夫的儿子因为遇见他改变信仰,终其一生希望写出美妙的诗歌,但直到死前才做出最有诗意的事——给聂鲁达留下一卷录音。
“第一,海浪声;第二,海浪,大声的;第三,掠过悬崖的风声;第四,滑过灌木丛的风声;第五,忧愁的渔网声;第六,教堂的钟声,第七,岛上布满星星的天空;第八,我儿子的心跳声。”
王安忆有篇小说《小新娘》,讲一个从小没大志向只知憧憬出嫁的小女孩,小市民归小市民,但我就是这样一个没出息的人,跟那小新娘一样设想过无数煽情的场景,比如录下心声或者拍摄天空变幻的云给某人,但后来发现早已被人用滥了,只恨吾生也晚。不过曾有一次奏效,大学里一个大雨的无聊夜晚,校园里积水过膝,我录下一片蛙声,送给一个朋友,居然讨得欢心。
我相信每个人在恋爱之时都痛恨自己的古板与俗套,无法用独一无二的方式打动爱人。我相信真情和技巧同样重要,否则情场杀手哪有市场?
即使严肃渊博如柏拉图,也写过这样的情诗:“我把苹果抛给你/假如你真心爱我,就收下它/并献出你的贞洁。”提起柏拉图,跟情爱有关的似乎只有“Platonic Love”,除此之外就是学究嘴脸。而实际上,柏拉图相貌英俊,是少有的美男。
游泳卡

锡拉 图 谢峰
一直到现在,我的BALLY钱包里,还是留有三四张游泳卡,它们来自不同的城市,全部已经过期,虽然我每年都会换一两回钱包,但它们总是与银行卡、身份证呆在一起。有那么几年,我总是在好几个城市中间穿梭,那些大同小异的城市,如今给我留下的惟一印记,就是许多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游泳卡——游泳是一项不需要同伴,又不太枯燥的运动方式。那几年,我总是觉得很热,总是有用不完的劲,于是我对其他生活要素毫不在意,却不能不游泳。我对城市的记忆都是从游泳卡开始。
那时的我,时常从一个陌生城市的地图中,准确地找到游泳馆的位置,不顾一切地跳进带漂白粉味的水中,体力耗尽、精神满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动荡又有趣,而我对一个城市认识的开始总与游泳池的细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候我会觉得,南京是用一种奇怪的褐色马赛克做的,上海的确比杭州大,长沙是圆的,广州见不到底,沈阳到处是中学生(那家游泳馆,是一个少体校的训练基地),青岛基本上没有人走动(大概人都在海里游泳),如此等等。当年的那些游泳卡,大小不一,花色各异,但无一例外,都是一张小卡片封上塑料,有的是月卡,更多的是计次的,但会有一个期限,它们便宜时只有几十块钱,最贵的一张要600块,期限是两年。如果碰巧在一段时间里,我两次光顾一个城市,而游泳卡又没过期,我便会欣喜若狂地与这张卡再续前缘。
那几年,我还经常会在穿梭中认识一些女孩儿,她们身处不同的城市,有着游泳卡的所有特性,我对她们的记忆也像对她们身后的那些城市的记忆一样颇有心得,那就是凭借额头来分辨她们之间的不同——无论是在泳道里狭路相逢,还是在咖啡馆里面对面地坐着,你都永远只能看到她们的额头,那时的我还没学会从另一些部位开始认识女孩儿。
关于女孩与游泳卡的关联,是我上周在什刹海参加一个同学35岁生日小聚会时感悟到的。我那过生日的哥们儿拿过我的钱包,抽出几张游泳卡,异常真诚地对我太太说:“对,女孩儿是像游泳卡,你看,都打了孔了。”我那直奔四张仍然小巧玲珑的太太,丝毫不以为意,她的目光掠过那些过期的游泳卡,停在我仅有的两张健身俱乐部VIP卡上,那片刻的狐疑,让我感觉,一个男人的中年真的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