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以哈佛为榜样?
作者:朱文轶(文 / 朱文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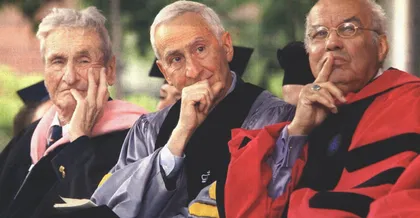
张维迎一再强调高等教育所遵循的普遍规律和全世界高等教育美国化的趋势是此次北大教改的前提。看样子,改革者们是想几年后拿出一个“中国哈佛”的样板来
Tenure对任何一个美国大学教员意味深长。自认为是美国最好大学的哈佛,将Tenure的档次提得很高
到“全球教授市场”去买教授
1992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他在北大方案中看到很多“哈佛”的影子,“我注意到,有些似乎是哈佛制度的特别性规章,稍加演变,引申到了‘中国的哈佛’,也就是北大身上”。
“比如说Tenure(终身教职)制度,这是现代大学教师人事制度最关键的环节,也是北大改革最核心部分。就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多数大学而言,更重要的是职务晋升而非Tenure这个环节,像一般大学对教师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从副教授升为教授,把关把得更严,但对于在副教授这一级上是否给Tenure,则相对不是很苛严。而在美国体制中,对是否给教师Tenure则把得特别严。因为教师一旦获得Tenure,除非严重失职或违法乱纪,大学就得把他‘供’到退休。这一关若把不严,大学冗员、占位现象就会很严重。”丁学良说,“美国25所最佳研究型大学中多数将Tenure定在了副教授这一级,也就是说,一个人拿到博士学位,工作六七年之后,晋升为副教授的同时也获得了Tenure。他再干个四年五年,如果学问做得好,就晋升为正教授。在重视研究的大学里,也有的人虽有Tenure,但一直到退休也升不到正教授。”“而哈佛的Tenure只给正教授。因为哈佛认为自己是美国最好的大学,必须把Tenure的档次提得很高。所以,北大的目标既然是中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在北大方案第一稿中同样把Tenure定在正教授这一级上。”
在Tenure体制导向市场选择下,美国的各个大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流动的“教授市场”。丁学良解释说,“因为不同学校的要求不一样,有些学校70%的教员可以拿到终身资格,有些学校连10%都不到。有些人在哈佛肯定拿不到,只是去镀镀金,在哈佛过一两年到其他二流学校,很快可以拿到终身教职。但结果是,一旦教授流动起来,不同教授的价值也就在市场中得以体现,名校教授的价码是相当惊人的。像美国的经济学家萨克斯,从哈佛大学跳到哥伦比亚大学,价位是30万美元外加大量科研经费。”“这样,越是顶级的大学就越容易聚集上顶级的大师。”
长期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学飞由此深感国内大学体制的沉疴,“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竞争性程度很高的机制,哈佛的校长才能说哈佛随便挑出一个教师都是世界一流的学者。这话,北大的领导恐怕没有底气说”。“中国高校长期以来的现实是,北大的教授就是北大的,复旦的就是复旦的,相互之间不流动,教师队伍永远没法更新,差的没法走,好的没法进,结果是死水一潭,毫无生气。”
按照这次北大的“教改方案”,“在讲师和副教授中实行择优和分流,目标是讲师流动在1/3以上,副教授流动在1/4以上”。照此,北大将在三到五年内换血将近1/2。“北大就可以像哈佛一样到‘全球教授市场’去引进教授。”陈学飞说,这是北大的梦想。
到底什么是一流大学?怎样来判断与保护一所伟大大学的个性、历史和它深入骨髓的精神?大学的精神能不能不进入市场?又怎样不进入市场?
像“哈佛”一样裁员?
“事实上,不光北大,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都正在美国化。”去年回国的教育学者别敦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香港地区的大学原来统统是‘欧洲体制’,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高等教育,在国立大学的教师之间,待遇基本上是全国拉平的,各院系之间也差别不大,带有浓厚的福利社会制度特色,市场因素很少。”“他们和‘美国体制’竞争了很多年之后发现不灵光了,因为很多一流的教授都往美国跑,许多大学便开始转向‘美国体制’。”“像英国,1988年颁布《教育改革法案》,规定大学教师临时工化,政府可以放手解聘大学教师。日本政府去年也推进了高等教育‘法人化’改革,决定在2004年将现有的国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法人’,国立大学在拥有人员组织方面的决定权的同时,大学的教职工将失去以往的国家公务员地位。”
丁学良说,无论以“美国模式”为榜样的方案细化到哪一个层面,纸上北大和哈佛如何相似,“减员增效”都是最急迫和现实的选择。而任何改革都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妥协,问题是这个“妥协点”划在哪里非常关键。如果太向过去一端靠,改革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如果太往未来一端靠,改革又很难推动。
照别敦荣的看法,同样的改革到了中国阻力必定会大许多,因为按“哈佛”那样的裁员率,若是搬到中国内地大学来,会有巨大负担。“北大同样如此。”他说,“那些社会里的大学在‘欧洲体制’下,冗员现象并不是十分严重,也就是说,虽然教师做研究的‘生产率’普遍不高,但基本上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教学和研究任务一般是不轻松的。西方的公立大学,虽由政府出钱,大学预算仍要经过议会里的好几轮辩论,不可能花大钱雇一堆人不干活,而且还有媒体监督以及学术团体的约束等。”“但在几十年的计划体制下,中国内地大学教职员中的冗员比例一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冗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易一下子甩掉的包袱。”对此,北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陈学飞说:“哈佛教授的工作量是很重的,基本上每人一个学年要同时上五门课,平均下来,每周得有7.5个学时,这还是在研究工作之外。而北大除了光华管理学院几个学院授课任务较重之外,大部分教师只有每周不到3个学时的课程。”“有10%的教师只承担了0.2%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如何处理这10%,学校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一名北大哲学系教师在网上留言说:“北大文史哲各系教授名额早已满员、超员,有的(比如哲学)在五六年内教授不会有空缺,如果大幅度换血,体制难以承受,但如果改革妥协,力度不足,在未来10年15年里,北大都找不到吐故纳新的机会。”
一个“大型国企”的体制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研究所赵婷婷博士对记者说,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法》上,中国国有大学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结构实际上是一样的,国有大学校长副校长就像国企的厂长经理。“美国2610个亿的教育经费绝大多数来自于民间和企业的投资,因此作为雇主裁掉雇员是没有争议的,但我们国家高校的教师其实仍然是准公务员身份,辞退的确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
教育学者杨东平说,教育主体性和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处于政治冲击和经济挤压的双重窘况之中的北大有一系列的“体制综合症”,“长期以来国家对大学实行供给制,由此导致了国有化的办学体制、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单一渠道的投资体制。这种官僚化作风在90年代后期高校院系合并改革之后,反而有愈演愈烈之风。”杨东平说。
杨东平承认,西方大学在本质上拥有几乎一致的价值观,即对学术自由与知识本身的信仰,那些不同的学制只是一种表面差异而已,“能不能在引入竞争的同时,仍然拥有大学的纯净和精神,这不止是一套方案的问题”。
美国的tenure制
在美国大部分学校的情况是这样的:申请工作者,首先获得一教职,获得一个任职资格(tenuretracked),只有进入这个过程才可能有资格转为终身教职(tenure)。如果没有获得任职资格,就只是一个临时工,不算学校的正式编制(faculty),不能享受他们的权利,如参与决策,参加选举与被选举系主任等行政职务。有了任职资格后,一般过6年有一个评审,当然中期也会有评审,但中期评审不会影响具体雇用。6年后的评审非常关键,如果通不过则要走人。如果通过,就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有了副教授就有了终身任职资格。
在评副教授时,本人提出申请,把所有的履历、研究成果与贡献的卷宗,必须要寄出去,全部要外校本专业的专家进行评审,一般要收到四到五个人的评审意见。收回后再从系里的学术委员会、系主任到院里的学术委员会和院长进行评审,这些都通过后,到学校里的人事委员会。学校里的人事委员会是根据一定程序选举出的,学校的人事委员会通过后,再由分管的副校长批,副校长通过后就可以了。再以后校长或校董会一般只是名义上盖个章。
评审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系里的意见。获得副教授后,就有终身资格,一般有六七年的时间再申请正教授,把同样的程序再来一遍。对正教授的学术贡献要求更高。
而对于新聘教师、一个教师晋升与否,给不给Tenure,最重要的评价不是来自本系、本学院或本大学,而是来自外部——来自全世界那个领域里相当受尊重的专家、教授的匿名评审,一般都是找7人,甚至9人,都是国际上的资深学者,但不告诉你他们是谁,同时选择外部评审人时有“六不准”:外部评审人不可以是你原来学位论文的指导教授们;不可以是与你共同发表过论文、论著的人;不可以是与你共同主持一个研究项目的人;不可以是你过去单位的同事;不可以是你现在单位的同事;当然更不可以是你的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