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8厂房的回音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任风)

3.刘展《砰!砰!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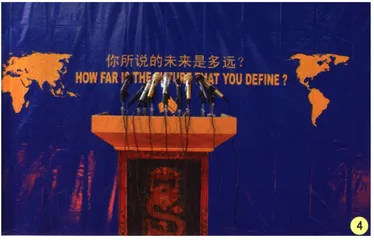
4.刘■《你说的未来有多远》
他们或许曾经身着父辈和兄辈的蓝色旧工装向小学同学夸耀,他们或许从大学文科毕业后便进入各自的行业,特殊的行业要求使他们成为这样一种人:与社会的相对距离成为他们与社会合作的必要条件。他们的工作内容属于社会转型中敏感的那一部分,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设计为最易于适应变化的模式。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热爱那种易于拆装和重组的IKEA家具,并小题大做地将这种热爱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他们的责任在于在我们这个无序和超现实的城市中寻找乌托邦的现实可能性,通过个体的努力将城市的暴力转化为活力。
4月13日,这样的一群人在北京城东北角打出了“大山子艺术区”的旗号。由徐勇和黄锐发起,邱志杰和张离策划的一个大型的艺术活动使这片工业厂区人满为患。活动包括特展和各机构与工作室开放两部分,特展《回音》在生态时空1200平方米的展厅中,邀请了十几位不住在大山子的当代艺术家(不做地域性的限制)组成。在特展的同时,厂区的艺术家工作室和机构作相应的配合,做艺术区开放展。如以策划《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艺术展示》而闻名国际艺坛的北京二万五千里文化中心举办了《王劲松水墨画展》。八亿时区出版工作室则举办了他们的书展,而“仁”俱乐部和“闹”酒吧也都有相应的演出推出。
“大山子艺术区”位于四环之外,机场路东南侧的大山子地区,是原798厂等大型国有企业,现七星集团的所在地。由于一大批艺术家、设计人和各种各样的文化机构进驻空置厂房,“大山子艺术区”已经由一个地理概念演化为一个文化概念,4月13日的大活动是他们在装修完成后向公众的一个集体亮相。圈内人说,其实这里早就成了北京文化旅游的必到景点了,相应地,房租也在飙升。
798厂等大型国有企业是建国初期由苏联援建、东德负责设计建造的项目,它曾经与位于石景山区的首钢齐名,共领新中国首都工业之风骚,几十年来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沧桑。当今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企业面临着再定义再发展的任务。随着北京都市化进程和城市面积的扩张,原来属于城郊的大山子地区正在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原有的工业外迁,原址上必然兴起更适合城市定位和发展趋势的、无污染、低能耗、高知识含量的新型的产业。大批艺术家和文化人的入驻,正是这一趋势的反映。
今天站在空旷的空置厂房里,你还能仿佛地看到当年社会主义生产的集体协作的忙碌身影,能听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广播声。你的怀旧甚至也无需借助于犹在壁上的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和语录。社会主义生产的痕迹似乎无处不在,不但建筑,整个50多年的社会主义生活的记忆早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和视觉文化的重要资源,这也是大山子艺术区的入驻者们无一例外地在改建和重装修厂房时保留了墙上的红色标语的重要的心理驱力。工业建筑己由工具理性的保留地演变成为感性的寄寓物。拟像渗透了仍然坚固的墙体,作为工业建筑的这些基本建筑,在今天却因为它的朴素性而成为极适合于意义附着的活跃的能指,你可以无穷无尽地阐释它,做得像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一样……
游荡在城市中却又怀疑城市的思想多动症患者们早就不可救药地陷入了对于厂房的爱情,他们在各个都市中寻找厂房,创造出loft文化。在纽约SOHO区,到Chelsea区;从柏林奥古斯特大街到西莫大街,再到伦敦的East-End,同样的历史一再重演,总是一批艺术家先发现这些宽敞萧瑟的旧厂房,以低廉的租金住入;接着是画廊入驻,然后财大气粗的设计师们来了,再然后是更财大气粗的时装店,把地价炒得比天高,挤走画廊和艺术家。这几乎成了loft国际现象的必然规律。这一规律注定了Loft文化在都市中的阶级属性:它是中心的创造者也是被中心逐出者,它不断地寻找边缘,又由边缘不由自主地身陷中心,出走再出走。这一位置及运动的方向,正好暗合了当今各国实验艺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也是各种各样由厂房、库房改造而成的艺术空间在各地的文化生活中越来越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之一。
90年代末,中国的房地产商开始把家庭办公作为有卖点的概念加以炒作。也是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改造和利用工业建筑为文化空间的现象。最典型的是两个同样以Loft为英文名字的艺术空间:北京的藏酷新媒体空间和昆明的创库。前者改造了北京机电研究院的厂房,后者则改造了昆明机模厂的厂房。“大山子艺术区”在规模和质量上显然是其发展,加上北京的地利,无疑将成为中国此类艺术空间的代表。
发生在“时态空间”中的特展取名为“回音”,策展人说:我们借助于回音,来测知我们自己的位置。这里的艺术家,从不同角度探索了相近的母题:如何借助于空间的规划和对于记忆的处理,在现实与意识之间建立起一种创造性的关系。
王卫的《移动的厂房》把这一意念具象化了。王卫拍摄了“时态空间”重装修前凌乱的旧厂房景象,将喷绘的巨幅图片覆盖在矩形的可移动框架上。展厅里忽然矗起一个巨大的立方体,图像空间与真实空间恍然相似,犹如镜面,大立方体一移动,你会发现那只是你的错觉。立方体的表面是过去,而这移动的立方体庞大的体积本身又不断地在改变着现实空间,迫使我们移动和避让,迫使我们不断地重新选择我们的位置。
张慧在《松鹤小区》则识破了这种古典的使用源自某种当代的欲望,“松鹤小区”的题名如同一个许诺着古典生活的澹泊宁静的房地产项目,它滚动着利益的计较。松风沓不可闻,鹤影定格成为玻璃钢雕塑,从金黄的民间纸钱的灰烬中站起,喷吐着世俗的烟火。
只有王书刚的雕塑《扫地》让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凝固,我们在纷乱的展厅中遭遇一群默默扫地的红色喇嘛。刘展的雕塑《砰!砰!砰!》是一群武装到牙齿的特种兵,他们的警戒与喇嘛们的舒缓形成对比。有节奏的扫地声会被爆响的枪声所淹没,但它执拗地存在,透出。这两组雕塑暗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策略:或者绷紧神经,准备用斗争来赢得安全,或者放弃武装,平静地赢得宿命。
李永玲的《金属家具设计》本身是可用的,被组成了家具的水管仍然是可用的。当水管互相沟通,水流可以在家具与家具之间连起一个自我循环的系统。坐在这样椅子上,你能感知到物与我的常与无常,水流意象化了时间,也在工业材料与使用它的生命体之前进行了机智的调解。
“飘一代”早已饱经世故,不再年轻。他们拥抱了都市也积极地解构了都市;他们规划和选择自己与都市的未来,因为他们深知规划和选择的不可能性;他们满腹乡愁,同时对这种乡愁满腹狐疑。他们贯通了阶级和方言,溶化了身份与信念,他们助长着城市的不靠谱之处,从而成功地延伸了城市的谱序。他们是回音,既是过去的回音,也是未来的回音。于是他们为自己选择一个根据地,以便昼伏夜出。这个地方叫loft或别的什么,这里是家和办公室的替代空间,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或办公室。他们将在这样的空间中坚决地安身立命,安其机动的身,立其灵动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