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的利益平衡点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老于 孟静)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拯救总是与旅游开发联系在一起
2月记者到洛阳采访时,正值当地开两会。对龙门石窟的再建设成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即要再花6000多万元建两座大桥,把车流彻底引出风景区,把龙门东山和西山作为一个统一封闭的风景区进行管理。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13公里处,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1公里长的崖壁上。龙门石窟200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对国内已经申报成功和打算申报的文化遗产来说,当地政府在申报前和申报成功后遇到的一些问题很具代表性。
奉先寺里卢舍那大佛右边那尊力士的脚脖子依然黝黑发亮。32岁的陈妍拿出一张照片给记者看,未满10岁的她坐在力士脚下小鬼的头上,努力伸着双手搂抱力士的脚脖子。“你知道”,她说,“当时下头有一堆人排着队等着抱佛脚呢。”说法是,如果谁的两只手能碰在一起,他就是个有福气的人了。在不少洛阳人家里,都有这样的照片。1960年就到龙门石窟工作的李文生的妻子就是龙门村的本地人,她回忆说她小时候,龙门石窟简直是“过路人的厕所”,虽然国家50年代就开始管理龙门石窟,但当地农民仍然赶着牛羊从卢舍那的眼皮子底下过。更甚者,此地乃是交通要道,去嵩县和伊川县等地的来往车辆众多。现在的游客只能远远地看着黑亮的脚脖子了,他们和脚脖子之间的距离是龙门石窟保护和开发的历史。
“文物区离百姓越远越好,像敦煌石窟和麦积山,根本不可能跟群众发生矛盾”,李文生说,“(像龙门这样)给点钱暂时解决了,过几年矛盾再起。”李文生说自己有双重身份,他是在龙门石窟里工作的人,同时又是龙门村的女婿,很多话也不太方便说。除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本身就对石窟有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利益冲突。
对农民来说,龙门石窟能给他们带来现实的利益,只要能在石窟门口摆一个小摊子就可以了。更有的人干黑导游的活儿。龙门石窟的门票60元,农民说他可以让游客只花30元,结果把游客拉到龙门石窟对岸,让他们隔着河看大佛。还有人把外地人领到山上绕小路,顺着树林荆棘丛钻,把游客的衣服挂烂了,让保安抓到还要罚款。一旦石窟的管理正规化严格化,等于是断了农民财路。除了个人,也有单位行为,龙门石窟附近的万寿山陵园是龙门村和民政局批准建成的,据说影响到了文物区和风景区的景观。
去年3月成立龙门石窟文物保护区和风景区管理局,加挂龙门石窟文物研究院,东西山合并起来管理。对这个问题,龙门石窟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李振刚更为坦率地说,一个知名景点周围,总是寄生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小团体。除了龙门石窟入口处有当地农民自发形成的小市场,上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旅游局在龙门石窟北门口建了一片仿唐建筑,离龙门大桥只有几十米。在南门外当地政府和农民通过集资,投资2000多万元建了一个巨大的“中华龙宫”,号称“中华第一龙”,附近还有一座万寿山陵园。各种各样的人造景点、当地民居、店铺及国有企业的厂房当时都成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问题。各级领导都希望能解决这些问题,但都没有彻底解决。
1999年市政府除了成立龙门石窟环境治理指挥部,使用行政手段解决外,更多是从经济角度,就是给当地居民足够的补偿。2000多万元的“中华龙宫”一声炮响就炸掉了,市政府作了赔付,而且炸后留下的空地也没有征用,而是采取租用,一年为这100多亩地支付40万元。2000年第二轮拆迁,最高峰出动了几百名公安和武警,当地居民不情愿,很多老人躺在屋子里不动,最终安抚下来的仍然是足够的经济补偿。
龙门村所属的地面也采取了租用形式,石窟每年给他们133万元。北门建了一条商业街进店,商贩必须进店经营。石窟管理局目前没有收管理费,商店也是让村子里盖,具体如何分配店铺则由村子里决定。
在石窟和当地居民及政府的关系中,前龙门文物局局长刘景龙的方法更生活化一些。他在龙门已经工作了快40年,村长见面还要叫他“叔”。如果有村民来闹,刘景龙就当面大骂他们,事后再叫过来安抚安抚,说说道理。刘景龙当领导时,过年给附近的村子1万元,“老人节”再给每个村子的老人1万元,给老人钱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他们制止年轻人闹腾。过年过节他们还经常跟当地人吃饭,他说:“这样下来,两边人成了一边人,怎么还好意思闹。”但这不意味着从此这里就没有利益的问题,政府机关跟万寿山陵园协调后,陵园地上的墓碑都被拆除,种上了树,但并没有阻止有人偷偷地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墓穴。
农民的行为除了用受教育不够来解释外,当地经济不发达是很重要的原因。洛阳市人均年收入在6000元左右,而龙门石窟2001年给洛阳市带来了2780万元直接收入,游客数为85万;2002年是3670万元,游客92.2万。洛阳市为了申报,前期花了1.1亿人民币,加上贷款利息,10年投资就可以收回来,由石窟带来的边际收入更多。
记者找到刘景龙时,他正在与南京博物院的人联系,要测试一种新型保护涂料的性能。据说这种新涂料喷涂在石像表面后,可以在40年内起到减缓风化的作用。作为一位文物保护专家,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护石窟展开研究工作。在他看来,80万的游客尚不足以影响石窟,龙门每年的容量150万,前提是分布均匀。刘景龙在如何从技术上保护石窟很有经验,有自己的方法解决同村民的关系,但也有些问题在他的能力之外,比如伊水上游的几家造纸厂至今还在排放污水,造成酸雨。不能解决的原因,仍然是地方势力。其结果是1982年看起来还很完整的一些碑刻,到现在已经字迹模糊了。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机会
记者 孟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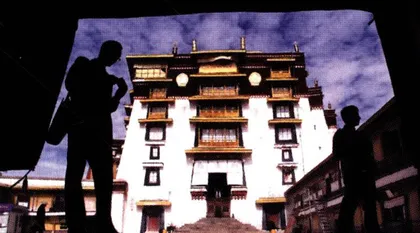
世界遗产之一的布达拉宫
中国艺术研究院外事处处长王路突然忙碌起来,忙碌始于去年,昆曲被确定为人类非物质与口头文化遗产之后。作为主管申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王路目前陷入了大量申报材料中,几乎包括每个有特色的地方戏种、表演形式、绘画形式。王路告诉记者,虽然没有明确数字,但他们在这一年间接到的申报项目不下几十个。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如未获通过该项目以后就再不能申报。这样,仅现有报名单位慢慢地排,可以排到22世纪。
更如火如荼的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申报,它们基本上都是风景区。据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推算,“申遗”热潮在三四年前就已经启动,但从去年起,有近百个项目报批到主管部门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和建设部,它们中有我们熟悉的卢沟桥、西安碑林和城墙、北海公园、殷墟、神农架、周庄,也有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独乐寺、丁村民宅、牛河梁遗址。
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今年6月29日至7月5日在苏州召开,苏州市专为会议设立了网站,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杨卫泽说,承办这次大会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苏州将把承办这次大会作为上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申遗”已经成为改变、重塑城市或地区形象的最好机会。
更大的推动力是,石家庄市旅游局有一份《正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报告。从该报告在市场分析后仔细列出的经济效益预测看,这个预计总投资1700多万美元(中方投入300万美元)的项目,在5年内可以收回投资,显然比房地产或其他开发项目见效快而且回报率高。
从1987年中国开始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项目之后,已经有28个项目被认定,它们极大地推动了旅游开发。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1994年申报成功后,本来已经是著名旅游点的它第二年游人就增加了1/10。小城平遥在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1998年门票收入是1997年的28倍。而仅30万人口的丽江申报成功后,去年的游客人数有320万人,年旅游收入接近20亿元。
谢凝高教授说:“申报本身是保护和拯救的过程,保护与拯救总是与旅游开发联系在一起。”因为联合国只能拨给世界遗产很少的经费,而国家每年给119处风景名胜区的拨款是1000万元,平均每处只分得8.4万元。对各地景点而言,申报遗产是走向世界,通过开发求保护的一个机会。
申报世界遗产至少要经历四项复杂程序:从上报省级建设厅或文物局,到国家建设部、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鉴定,最后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检验。1987年中国第一次申报时,曾一口气通过了6个项目,其后每一次申报都很顺利。但从2001年开始,联合国出台新规定,每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像意大利、西班牙、中国这样世界遗产在世界排名前三位的国家不鼓励申报,而要优先考虑那些缺少世界遗产的国家。
谢凝高教授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和广博的自然条件使很多项目都符合规定,申请遗产是把中华文明纳入世界关注的框架里争取全世界对这些遗产保护的支持,为什么要限制申报呢?而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专员木卡拉的看法,中国申报世界遗产中的问题是,“缺少专门的世界遗产管理机构来协调开发与管理”。事实上,目前的文化遗产管理,某些归文物局、某些归建设部、某些归旅游局甚至旅游公司,谢凝高因此建议,应该专门成立一个世界遗产管理局,加强协调管理。 文物意大利世界遗产洛阳龙门石窟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