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废灭曲》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金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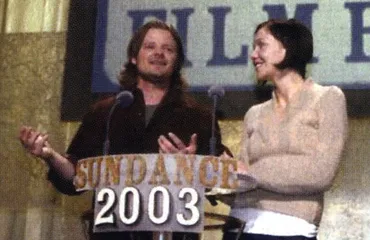
圣丹斯电影节颁奖现场

由“梦的碎片”汇集而成的《废灭曲》在圣丹斯电视节显得格外另类
在不足百年的纪录片史上,就“叙事”和“说理”这两条路线谁是纪录的正统,总有人争论不休。到了今天,突然发现争论的前提似乎不复存在——一些片子既不叙事也不说理,却煞是新奇好看。它们把自己归类于“故事片长度的非情节片”。
今年1月的圣丹斯(Sundance)电影节,纪录电影就要比故事片来得红火。奥利弗·斯通以纪录片参展,主题是关于卡斯特罗的,够酷。虽然没有得奖,却也证明了如今纪录片的兴旺。而5000参赛片中,要数《废灭曲》另类得紧。
片头使用了老资料镜头:一个传统着装的印度人在无声旋舞。当你试图确定这个镜头的意义时,却发现这个没休止的旋转其实没有意义:你不知道舞者是谁,发生在何时、何地。这旋转延续了近两分钟之后,是一个平滑的长镜头,这是整部电影中惟一清晰完整的影像:镜头从成排转动着的胶片盒的轴心,移动到足有几十米的洗印池。如果在看完全片后,还能回忆起这个画面的话,你将会心一笑:这就是无数电影巨作出生的产床。
都说电影如梦,但梦有多种。有些梦有线性的情节,醒来后会被回味、讲述,电影的心理机制即是基于这一类型的梦。而大多数梦是一些散乱的片段,发生后并不形成记忆,它们留下些许残痕,曾在无数个清晨烦扰我们的意识:梦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将这些无意义的形象残片忘记,但它们仍然藏匿于茫茫脑海的某一角落。电影和这类梦无关,否则观众会集体疯掉。但《废灭曲》走了极端,索性由梦的碎片汇集而成。片长60分钟,全是废损的黑白电影胶片。由于胶片的物理损伤,影像部分地丧失了。但残像带来了意料不到的视觉感受。
新奇的视觉效果总来自不同的介质。讨论胶片废损的原因,要回到它的化学构成。爱迪生和伊斯特曼发明的赛璐珞胶片,混合了硝酸、硫酸、酒精和樟脑精,爆炸性和诺贝尔的硝化甘油相近。后来爆炸性被驯服,但可燃性依旧。据计算,8000卷1000英尺长的胶片会在3分钟内燃烧干净。1937年,由于胶片爆炸和燃烧,福克斯公司的全部默片家当化为乌有。1977年,美国国家电影资料馆收藏的环球公司的所有新闻片被烧毁。人们试图通过电影把时间凝固,而变动不居的时间既然不允许人们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自然更不情愿让人们借助电影把某些瞬间一遍遍地重温。除上述化学不稳定性,赛璐珞胶片还有其他缺陷。从被制造之时开始,它本身就以加速度变形;时间长了,片基上银颗粒所构成的影像会逐渐变成棕色;感光乳剂会膨胀、形成粘稠的泡沫。最终,时间会把胶片变成一堆红色的粉末。如今,嘉宝的《神女》就已经成灰了。
受损变形的胶片为《废灭曲》提供了物自天成、非人力可为的创作介质。制作人、导演兼画面编辑比尔·莫里森以考古工作者的姿态,深入美国各重要的电影资料馆,在旧胶片堆里搜寻。选择素材的基本要求是:画面主体要可辨认,毁坏变形的程度要高,二者共同构成新的意味。片中图像具有含混的象征;意义指向类似的画面被剪接成板块,形成全片中不甚清晰、但隐约可察的结构:关于灾难、拯救、东方、孩子、一个穿插其间的妇女,没有明晰的意义和主题。看片时,你不能思考,也不能诉诸感情,只能下意识地随着片子的流程漂啊漂。你被教养出来的关于美的标准会失效。破损画面的频频闪动,会让你厌倦。这充满惊讶但没有愉悦的“审美”过程,如同被噩梦魇住。
片子的音乐本是为2001年欧洲音乐月创作,其中使用了不少东方响器,加上现代音乐常用的荒腔、走板,助长了电影的噩梦气氛,被评论称为《废灭曲》在音响学意义上的双胞胎。作曲家麦克尔·戈尔丹是纽约试验音乐阵营Bang on a Can的创始人之一。关于美,他的主张是:“我着迷于真漂亮、同时又是真丑的东西。当你听见了美,你也听见了丑。我要把美和丑混到一处。”导演莫里森暂时没有创作心得可说,他正在为发行商没着落愁苦。但他得到了一些珍贵的精神奖赏——美国纪录片巨匠麦克·默里森称赞《废灭曲》是“历史上造得最好的电影”;还有观众给导演发了一封电子信:“恭喜!你创造了第一部后-后现代电影。”
《废灭曲》说到底是概念片,表面上是对废灭的哀伤和追记,实际上,是人的创造精神的不屈服。在和时间的博弈中,人从来没赢过,人们的创造物也终将被时间彻底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