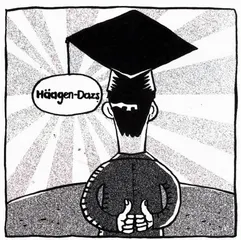生活圆桌(223)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黄莹 骆平 杨不过 林妹妹)
绝版阿嘉莎
黄莹 图 谢峰
“绝版阿嘉莎”当年瘦高清癯,是我的高中同学。这一称谓源自她对阿嘉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疯狂热爱。那时追随阿嘉莎的途径也少,除了几部拿腔拿调的译制片,就是图书馆里被翻得稀烂的几本旧小说。图书馆还没有翻修,阴冷的屋子里充溢着神秘的气味,她居然从中发掘出半架子阿嘉莎,然后一天一本,一个月看完,于是大家就都叫她绝版阿嘉莎了。
正版的阿嘉莎是个天马行空的人物,其出版物的数量仅次于《圣经》。连三毛这等特立独行的女子都为之倾倒,声称“我热爱克里斯蒂所有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不惜把“令人目眩神迷的奇书、华丽辉煌的迷藏”之类的猛词往她的作品身上砌,可见十分了得。“绝版”很早就发掘了“正版”为人及作品的特质,具体说来就是敏锐、孤僻、“奔腾”般强劲的思考,当然还少不了英国味的神经质。她还将这些特质结合实际发散到了日常生活中去,所以她总是保持步履匆匆、精神奕奕的形象,从不参与电视剧情的讨论和编派八卦消息,但是会偶尔驻足释放一个带有探究意味、耐人寻味的眼神,继而专注于研究牛顿定理和化学实验。考虑到她的家庭背景——她的父母和姐姐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她对阿嘉莎的热衷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举动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简直就是理所当然的。
正版阿嘉莎婚姻不幸,她笔下的神探们也统统独身。在这些神奇人物当中,绝版阿嘉莎更喜欢饶舌和爱管闲事的老处女马帕尔小姐,不感冒留着难看胡子混迹于全球著名旅游景点尽和漂亮女人搭腔的波洛,尽管后者的知名度要大得多。当时尚没有迹象表明她会守着自己独到的爱好做一个高贵的老小姐,然而她对姐姐在大学里面的恋爱颇不以为然,还给那个首次上门做客的可怜小伙子若干脸色,可见她认定情感是理智、尤其是亟需理智的侦探工作的大敌。她心高气傲如同《小妇人》中大大咧咧的乔小姐。
后来绝版阿嘉莎到了一座沿海的小城学会计。所有的人都觉得吃惊,大家都认为她会到京城深造侦探技能,至少也应该学习解剖、药学、化学之类与之沾边的学科。考虑到福尔摩斯的哥哥,那个在推理和破案上连他声名在外的弟弟都自愧不如的人物,曾是英国著名的会计,我对绝版阿嘉莎的精彩还是抱有期望的。后来我得知,绝版阿嘉莎在抵达那座柔媚小城的三个月后便陷落在几打玫瑰花下,从此以后心无旁骛,整日幸福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任海风吹拂长发飞扬。从此再无人和我谈起阿嘉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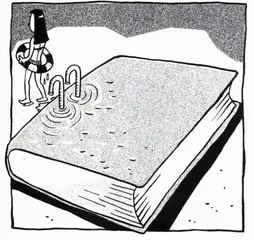
男人的芭蕾
骆平
芭蕾似乎有着女性专属的姿彩,而铮铮男性仿佛不太沾得上边,天鹅湖里面的王子,穿着中世纪盛装,惟一任务就是一次一次将轻盈、柔若无骨的天鹅公主托举掌心之上。忧伤的天鹅公主依旧媚眼如丝,而举重若轻的王子则面目模糊——光芒从来都是女人的。
真正注意到芭蕾舞中的男性,是在观看2000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时候,那个俊秀、英雄般身手矫健的男人,惊鸿一瞥地从镜头前风云闪逝。让我无比诧异的并不是他的舞姿,反倒是他的眼睛,他的眼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骄傲,好像在慎重其事地宣告,我是主角。刹那间,我迷上了他的矜持,男人的矜持。
他就是马拉霍夫,20世纪90年代中期红起来的俄罗斯芭蕾舞新生代巨星。因为他的缘故,欣赏芭蕾时,我渐渐开始留意男角的存在,也晓得了一些名噪一时的人物,像20世纪60、70年代的鲁道夫·努里耶夫,70、80年代的米哈伊·巴里什尼科夫,80年代末的伊戈尔·泽伦斯基。然而男人的舞蹈很难有荡气回肠的感觉,他们的舒展和跳跃老是有点钢筋铁骨的味道,因此大部分时间他们的表情都是风清雨微的。女角的蛊惑简直就是致命的。
我所喜欢的仍然是马拉霍夫。马拉霍夫是不一样的。他天衣无缝的弹跳可以造成悬浮片刻的感觉,他的四肢在半空中轻轻铺展,细细的灯影如碎雪一样落在他的肩上。他的脸上有孤芳自赏,性感到无法言说。
尤其酷爱他的《玫瑰花魂》,那一幕剧,他是主角。他穿着酒红色、绣满玫瑰的贴身丝质上衣,在微茫的灯光里寂寞地舞蹈并且深思。他的动作充满斩钉截铁的力量,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与忧郁的气质叫人想起普希金的诗歌,抑或是遒劲的中国古典书法。
马拉霍夫不怎么出现在媒体上。遍寻娱乐杂志,我仅了解他出生在1968年,母亲是钢琴家。他自小涉足舞蹈。他的老师是著名的芭蕾教育家,出名之后,马拉霍夫曾经神秘而虔诚地说,做舞者,首先需要学会倾听自己的身体。他对自己的身体有十足的把握。
再有是马拉霍夫的梦想。有人问他退出舞台以后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他的回答匪夷所思,他说:“做个兽医。”
除了芭蕾,马拉霍夫的生活大概与当年那些博物馆、抽象画统统无关,他是一名舞者,纯粹的舞者,而舞者本质的功课,便是对于自身每一缕肌肉每一根脉络的关注。
也许男人的芭蕾更多不是用来诠释人性的温存,他们的舞蹈有大自然蓬勃生长的气息,宛如苍翠的植物、凶猛的兽类。我相信马拉霍夫可以成为杰出的兽医,他懂得生命的一切哀伤与美丽。
不纯真年代
杨不过
曾经有过一个亲如兄弟的男性朋友,一次心血来潮对他说,我们要做《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和绿子那样的朋友,一起在自家的天台喝酒,然后边看着远处街上燃起的大火边接吻。当时觉得这是叫人脸红耳热的情话,说出来后大半个月没敢正眼瞧他。可现在看起来,简直纯情死了。
的确,那是一个纯情年代,纯情到看村上春树书里偶尔的狎妓情节都觉得难以忍受,于是不再喜欢,并且奇怪他的书怎么成了小资圣经。对我的埋怨,老爸一副先知面孔教导我说,要多看看老人的东西,他始终推崇沈从文汪曾祺那一派的,对我乱七八糟的品位摇头不已。但那时候,还看不惯那样的慢悠悠,喜欢的是神叨叨看起来充满哲理的,例如米兰·昆德拉,尽管后来的确觉得那不过是比较有头脑的言情小说而已。
直到不久前,看到新出的一套沈从文作品集,装帧不错,于是买椟还珠似的买回来。《边城》已经熟到不能再看,我现在经常无意识翻开的是《湘行书简》。也许是人越大就越没勇气轰轰烈烈地去爱,直接的后果就是窥探欲变强。1934年初,沈从文因母病还乡。每天给新婚妻子写信报告沿途见闻。那信上分明写着“三三的专利读物”,而我就这样厚颜无耻。
“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船主叫做童松柏,桃源县人。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所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沿河的船虽然万万千千,我的船你自然会认识的。这里地方狗并不咬人,不必在梦里为狗吓醒!”三三,二哥,他们的情话杳不可闻,单是这样的称呼也是再不可能有的了。
一度对名人逸事感兴趣得很,比如林徽音的太太客厅,据说有一次,沈从文几乎是哭着赶到林徽音家,说张兆和到苏州娘家去了,他每天都给妻子写信,但得不到回应。看起来他也就是一个为情所困且淳厚木讷的人,甚至完全不像曾写下那么动人心魄的文字。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据说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整整4年,写下了几百封书信之后才被接受。我是没有被人如此宠爱怜惜过的,完全无法想象一个女人面对这样的文字如何不动心。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调子,我相信不会再有任何一个男人对我说这样的情话,想起他们千篇一律的温柔就让我非常难受。
关于上面说过的那个朋友,现在他已在万里之外,当然他不曾知道,我一度想把一句话珍而重之地送给他,就是悼念沈从文先生的那副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那时候觉得他是天底下惟一能叫我动心的男人,认为等到了合适的年纪男婚女嫁是顺理成章的事。如今看来,那是多么的年少轻狂。
关于哈根达斯
林妹妹 图 谢峰
每次往返美国在东京的机场转机时,一般只会买两样东西。一个是日本果子,那些包装得无比精美的果子其实也就是一些糯米和豆沙或者栗子和绿茶做的小点心。总是很奇怪用这么简单的原料,国内为什么就做不出如此精致的点心?不过漂亮的日本果子价格也很可观,一般都要5到10美元一盒。价格昂贵的东京机场,有一样东西不觉得太贵,因为国内更贵,那就是哈根达斯冰淇淋。如同日本街头随处可见的自动售货机一样,东京机场的哈根达斯冰淇淋自动售货机也极方便,用2.5美元跟超市收银员换一枚币,投进机器,一小盒冰淇淋“咚”的一声就出现了。
在国外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店门脸一般都很小,卖的大多是一些基本口味。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在哈根达斯小店花1.5美元买两球冰淇淋,在国内好像一球就要25块人民币。有一次在纽约时和大学同学去她家附近的超市逛,那是一家华人大超市,各种中国食品应有尽有。冰柜里有卖大桶的家庭装哈根达斯,这在咱们这儿怎么也要100多块了,那儿仅售2.99美元。我那位同学,在纽约那么些年竟从来没注意过哈根达斯。听我说起哈根达斯在国内的风光,很是好奇地买了两桶,还很得意地算计:“这么说来,我今天买这两桶冰淇淋,赚了200块人民币。”
美国人认为冰淇淋是老少皆宜、物美价廉的休闲食品,随手可得,冰淇淋就是冰淇淋,吃冰淇淋只是因为他们想吃,他们可能对某个品牌有所偏爱,但是不太可能理解把冰淇淋上升为文化乃至品位的说法,所以他们会对哈根达斯的拥戴表示惊奇。
不过哈根达斯在中国的成功倒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范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创新精神,他们提供了在其他国家都很少见的多种选择和独特创意,比如冰淇淋火锅、冰淇淋月饼、冰淇淋寿司及有各种诱人名称的冰淇淋套餐和饮品。
有一次和在东京生活多年的好友在新宿野村大楼对面的甜品店吃甜品,她给我点了据说是最具东京特色的甜品。前段时间在哈根达斯的新品推荐赫然发现了这记忆犹新的甜品,叫做“东京丫弥酥”,点来一试,模样味道和配料竟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