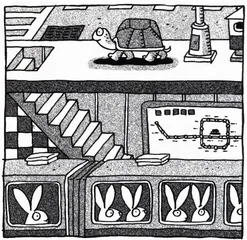生活圆桌(22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韩东 西闪 多美 张沙)
裸奔
韩东 图 谢峰
裸奔越来越时髦了,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被我们听见和看到,被我们说出和写在文章里。常听说有狂热的球迷脱得赤条条地在碧绿如茵的足球场上奔跑,警察慌忙上前脱下生硬灰暗的制服将其白生生的肉体罩住。又据报道,两个农民工酒后打赌,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如果你脱光了上街跑一圈,我就给你十块钱。这样的裸奔倒很符合中国之国情,酒后人胆大,并且也不是白脱白跑。
有一位导演,要拍一部“另类”电影,其中有一场裸奔的戏。他的设想是男女主角都脱光了,在满眼青绿的稻田里追逐而去。可到了现场,男女主角说什么都不肯脱,他们的借口是路上人来车往,又说剧组的人来得太多了。导演的电影是低成本制作,几乎不花什么钱,演员也都是免费的。因为这个原因,他说话毫无权威,人家不脱也只有干着急的份。于是一直相持到天黑,剧组收工,回去吃饭。在饭桌上,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摄像是个粗豪的男人,多喝了几杯,捏着酒瓶子说:这有何难,不就是脱吗?不就是当着大伙儿脱吗?我脱给你们看。
为了给男女主角做个榜样,饭后剧组又返回了拍摄现场。其时是晚上9点多,拍戏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此兴师动众只能解释为起哄。摄像想说明的是:脱,当着大家脱完全是小事一桩。于是他将衣服一件件地脱下,并有条不紊地担在左臂上,用胳膊夹着。最后只剩下白生生的一条向黑黢黢的稻田里窜去,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剧组人员站在这边的路上等着,好半天了都不见那白色的东西返回。大约十几分钟后,导演沉不住气了,他和几个小伙子脱了鞋下到稻田,一路向前找去。那摄像怎么了?是摔了一个大跟头,疼得爬不起来了?或者冷风一吹酒醒了,觉得不好意思躲在稻田里不肯出来?或是醉卧过去了?都不对。当一干人寻过去的时候,发现稻秆之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白屁股,正肆无忌惮地撅着,对着他们。那摄像的脑袋埋在下面,正双手着地在摸索着。原来,他这一裸奔,手机、钱包、钥匙等零杂物品从担在手臂上的衣服口袋里一路落了下来。月黑风高,稻浪起伏,摄像撅着他的屁股闷声不响地摸着他的钱包,这番情景的确让人忍俊不禁。
裸奔终于没有拍成。让导演聊以自慰的是,电影里总算是有一场脱戏。当然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庄稼地里,而是在水雾迷蒙的浴室,也不是一男一女,而是两个男人,模模糊糊的不甚清晰,但用毛巾搓背的动作还是看得出来的。

175米
西闪
故乡码头往上行,有一家问津饭店。青瓦屋檐,被烟火熏黑的木板墙壁角落能看见各种不知名的杂草。那是6岁时的记忆。那年父母带我在那里吃过一顿饭,鲜美味道自然非今日菜肴可比。印象更深的是,等我们结账时一个小乞丐悄悄踱来,把一盘鱼香肉丝的残汁舔得一干二净,然后又不失尊严地离去。在故乡的那些年月,不少乞丐出入饭馆干这等营生,以至于很长时间人们都把乞丐称作“舔盘子的”。后来,旧的问津饭店被拆掉,建了一幢六层楼的房子,楼下的问津饭店却少有人问津了。这崭新的问津饭店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一个:墙壁上一道血红的粗横线,上面写着:175米。
谁也说不清楚那道线是什么时候划上去的,但大多数人都知道那个数字的意思。
邻家的程太婆已经86岁了,她比我奶奶还长一辈,和巷子里同辈的孩子一样,我叫她“程祖祖”。勘测队的人对她说,以后将有一条铁轨穿过她家的后院。她很高兴地在巷子里来回走,逢人便讲她将看见火车了。尽管那年自来水管还没有铺到她家的后院,而且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晓得她多半是活不到17年后的2003年了。两年后她死了,悄悄藏了几十年的红漆棺材最终没有陪她长眠于地下,被她的曾孙女做了新婚家具。像故乡不少火化的亡者那样,程祖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用水泥封进城后那座像一块岩石屏风的山壁里。仲舂,我和中学同学们很爱躺在山壁旁的草坡上晒太阳。多少年来,山壁中已经嵌入了数不胜数的骨灰盒,亡者密密麻麻的朱红色的姓名面朝滚滚东去的长江,不合昼夜。亡者不知道,多年后将有一个数字将埋葬掉半个古旧的城市,将驱赶着故乡的生者走向未知的远方。他们站立在175米之上,站在城市的最高处,面朝长江滚滚东去,不合昼夜。亡者总比生者幸运。
1990年的夏天,我乘朋友的船去岳阳,第一次过三峡。黄昏,我和朋友在指挥舱外的舷梯旁喝酒,我看着余晖中的故乡缓缓地和我们拉开距离,缓缓消失在河道的转拐处,怅然若失。入夜,狂风骤起。我仍然坐在船头。江浪翻腾,水花飞溅,右岸一处的灯火明明灭灭,那是175米水线下的张飞庙。据说庙里有岳飞的亲笔书碑《满江红》。
大雨伴随我离开云阳,离开奉节白帝,忽然停歇。一弯残月穿过壁立千仞的夔门照耀着我。四野俱静,惟一能听见的是奔流在峡谷中的江水,那么急切又那么从容不迫。
我早已离开故乡,寓居成都多年。而到今年秋天,175米以下的故乡已经成为一片瓦砾。本来想静下心来回忆回忆那即将埋葬的岁月,再想想似乎又无话可说。
儿子对两性知识的科学探索
多美
我的儿子虽然只有6岁,但是本着对科学上下求索的研究精神和知无不言的诚实品质,我相信他对这个两性世界的精辟见解和准确判断都已经在许多成年人之上,不信,有他的成长记录为证。
儿子两岁时,看了《狮子王》,告诉我他自己是一只母狮子。我问为什么,他说雄狮子脖子上有一圈毛毛,而他没有,所以只能当母狮子。这是他对两性世界的启蒙认识,一切还算正常。
儿子3岁时,被蚊子咬了小包,我气愤地说“蚊子真坏”,他科学地指出:“是雌蚊子坏,雄蚊子不会叮人,它们只吸草汁和露水。”听得我不由得对雄蚊子肃然起敬,简直想替它申请成为绿色和平组织成员。31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所有的蚊子都是咬人皮、吸人血的,但出世仅36个月的儿子就让我对他的精细认识刮目相看了。
儿子4岁时,有了一本图文并茂的科普读物《多姿多彩的鱼儿》,在让我们给他念了无数遍鱼儿的生长过程后,他对生殖、受精、产卵、卵子、卵黄、卵胎、胎生、孵化等科学名词已经精通到张口就来的地步。从此我们家对此类事物再不能含糊地统称。比如春节回杭州过年,吃鱼时他外婆说:“多吃点鱼子,鱼子营养好。”儿子立刻纠正说应该叫“鱼的卵”营养好。他那思想保守的外婆深受非一般的刺激,连声问我们是怎么为人父母教育孩子的?
儿子5岁时,有一天我们照例开玩笑说他可能是从垃圾箱捡来的,因为他长得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奇怪的是这次儿子并不着急,他慢悠悠地说,他才不是垃圾箱捡来的,而是爸爸的精子跑到妈妈的卵子那里,并且强调说:“爸爸的精子必须跑得很快才行,因为精子有很多,卵子很少。”他还很内行而且充满理解精神地拍拍他老爸的肚子说:“爸爸,在你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精子,是吧?”这次即使是尊重科学的我们也目瞪口呆,互相翻着白眼埋怨:儿子是否太接近真理了?
儿子6岁时,全家人同食大闸蟹,他想知道怎样区分公螃蟹和母螃蟹,我只好把几十年前父母告诉我的经验传授给儿子:母螃蟹肚子上的盖子是圆的,而公螃蟹的盖子是尖的三角形。儿子继续问为什么母螃蟹的盖子是圆的而公的是尖的?他爸爸形而上地回答说:“因为母螃蟹有许多小宝宝,所以那块盖子要大一些,小宝宝好躲在里面。”然后就发生了令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事情——儿子立即揭开一只公螃蟹的盖子示范说:“我知道了,那么公螃蟹不用生小宝宝,所以他有一根细管子,是产精子的,你看它是不是像一根大炮?”
至此,他那可怜的老爸彻底对儿子甘拜下风,要知道他是在16岁进入大学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配偶!
慢点儿
张沙 图 谢峰
北京,祖国的心脏。放眼望去,满是行色匆匆的人群。倒是和周围新建起来的高楼大厦以及正在为工程做准备的断壁残垣很相配。国际化的大都市,本就该这个样儿。多少海外归来的仁人志士无不曾感慨过彼岸的高速发展,同时欣慰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生于斯,长于斯,每每出门,轻车熟路,无往而不至。和所有现在生活在北京的人一样,我偶尔走在街上,也是如箭离弦,义无返顾,到地为止。
后来我随波逐流俗不可耐的也出了国。初到国外,住在法国那个时尚之都往南边两百多公里的一座小城里。是地本是法国文明的中心,又是纯正法语的老家。当地居民口吐之法语,语音标准,毫不含糊。由于城市古老,所以自有一番世外桃源的景象。比方说民风淳朴,建筑古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还有,就是住在哪儿的人走路很慢,慢悠悠的,满吞吞的。我的北京速度初到时几乎有赶超街上公共汽车的架势。
偶然有事要找大使馆去办,动身去了巴黎。市中心蒙巴拿斯火车站的再下一层便是市中心的地铁站。我去换车,中间有一条滚动的传送带,就是机场里常见的那种。我已经开始觉得立在上面听之任之乃是平常事体,忽然惊见黑压压一团人压了上来,争先恐后地从我身边那一条缝隙里侧身而过(通道设计得太窄了)。其场面之激烈,情形之紧迫,表情之漠然,动作之轻盈均令我至今难忘。要是换做在大街上见着这样的阵势,绝对以为这是国际田联办的什么竞走比赛,除了服装不是那么专业。后来我发现,巴黎的上班族就是这样,飞蹿在那巨大的地铁网里,宛如洞中硕鼠。只有到了地面上,你才有机会见到一些悠闲而又安静的人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那些行走在地下的人们才是这座城市的主流。打开地图看看那些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想来莫不如此,原本好端端的城市都蜕变成了巨大的商业中心,住在里面的人也跟着变得怪里怪气。
现在我把家搬到了一个港口城市,这座城市不大不小,位居法国城市排行榜的第六。属于这里的速度适中,基本上可以让人喘息。所以我也算乐得自在,也便有空闲想想北京——一个据说原本无比悠哉游哉的风水宝地。可惜这种气氛如今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堪与拆房之快一决高下的快车和飞人。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选择折中一点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