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处苏州古宅能否买卖?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邱海旭)

“吴状元府”的最后一进是这座老宅惟一保存完好的木楼

保存完好的古宅已经成了稀有品
“吴状元府”和它的“七十二家房客”
邢杏珠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把马桶拎到弄堂外,等着人来收拾。她偶尔想起这条又黑又长的弄堂几十年前还是一条花园长廊,左手边斑驳遍布的墙上曾经有过镂空的花窗。
邢杏珠住在苏州平江区潘儒巷79号这所大杂院里已经有34年,和她一起的还有40多户人家,在他们西边巷子口就是举世闻名的狮子林。邢杏珠还能记得22岁那年嫁到这里的情景,“一进门就觉得古里古怪的,屋子又大又高,都是花格窗,外面墙上有好看的砖雕,有几进院子还有池塘和假山。刚来时候没有自来水,十几户人家合用后面的一口井水”。
如今,呈现在记者眼前的分明是个纷乱破败的大杂院,邢杏珠记忆里的那几处小园林早已挤满了自搭的小屋。由于下水不好,院角阴沟里不时散发出淡淡的臭味。在晾满衣服的竹架后面,一座残破的门楼依稀透露出这所老宅的历史,门上两块砖雕在“文革”中被铲坏,但仍能辨识出精刻的纹路。照壁上的题书只剩下“秀毓”两字,邢杏珠记得另外两个字是“英蛮”。落款时间是“乾隆丁亥年桂月”。
大院的居民把这所老宅称为“吴状元府”,苏州文管会前副主任、吴都学会秘书长王仁宇告诉记者,这里有可能是清代嘉庆状元、云南按察使吴廷琛的祖宅,但由于吴廷琛的居住情况未见载于史料,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王仁宇说:“古时苏州大户人家一般倚河为居,宅院多为五进三路,也有七进五路,中轴线上依次为门厅、轿厅、大厅、女厅,边上几路是花园和书房,有的叫花厅,闻名遐尔的苏州园林只是这些深宅大院的组成部分。”
“吴状元府”就是一所典型的五进三路老宅,从位置上看,邢杏珠一家住的正是原先的正厅。前面一进轿厅和后面一进女厅都各自居住着四五户人家,最后一进楼厅据说是小姐的闺房,是整个“吴状元府”保存最完好的木楼。刘善萍一家住在邢杏珠楼上,这200年前供宾客休憩的客房,如今被3户人家十几口人挤得满满当当。刘妈妈家里还能看到雕花的楠木门板,记者顺着咯吱作响的楼梯爬上去的时候,她的小儿子正在睡觉,床边搁电脑的是个明代的梳妆台,镶着铜拉环的红木小抽屉里塞满了光盘。
像邢杏珠、刘善萍这样的退休工人如今是“吴状元府”的常住居民,几十年岁月已经使她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较年轻的一代都已经搬了出去。“老房子房顶高,透气性好,邻居相互都有个照应。”刘善萍说。但也有让她头疼的地方:到处都很乱,屋里总有扫不完的木屑,那只用来洗澡的大木盆比她大儿子的年纪都大。“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昔日景象自然不会为这些老居民的日常情绪增添伤感,但邢杏珠还是比较喜欢几十年前那个有砖木雕饰和池塘假山的大宅院,在她眼里,这所宅院的衰败过程仍在继续。最近的两次损坏是:她家门前那堵摇摇欲倒的风火墙被拆掉了1/3,而自从请来泥瓦匠整修屋顶后,檐上的两个兽头就不见了。
古建“上市”之路
在苏州,像潘儒巷79号这样住满居民,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深宅大院有200多处,苏州市文管会为它们挂上“控制保护建筑”的牌子,除了能令它们免遭被拆除的命运,这块牌照背后没有任何具体的保护性措施来延缓它们衰亡的速度。而实际拥有古宅产权的房管所也没有足够资金对这些建筑进行维修。一位沧浪区房管所干部对记者说:“我们每个月只收住户十几块钱租金,修扇窗户都不够。”据这位官员介绍,要想把古民居彻底维修,必须将里面的住户全部迁出,这部分费用要比维修费用高出数倍,“80年代修俞樾故居时花了100万元,其中80万元是用在搬迁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州古建筑保护条例》中有关私人可以购买或租用古建筑的规定曾引人注目。实际上,苏州古宅的“上市”历程在《条例》颁布之前就已经开始,目前已有绣园、亲金德园和费氏老宅等控保建筑被私人收购,价格多在1000万元以上。
民营企业家陈慧中3年前投资100万元租赁苏州郊区的花山进行旅游业开发。花山是苏州历史文化名山,曾得康熙、乾隆二帝数次“驾幸”,目前山上的观音殿、莲叶精舍等景点都是陈慧中从苏州城里搬来的古建。“我如果不买下,这些建筑即使不被拆掉,也会自己倒掉。”坐在苏州著名的采芝斋茶楼上,陈慧中对记者说,“古建筑的每一个构件都做上标记,运到山上再重新组合。”最先引起陈慧中兴趣的是苏州木渎山塘街上的一座全楠木厅,陈慧中向市文管会出价80万元,要求将已经破旧不堪的楠木厅搬到花山上重建。但文管会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陈的提议。“文管会批复后两三天,楠木厅就倒塌了。今年7月份有媒体报道城东一所小学里发现了全楠木厅,说什么全苏州独此一家,其实早就有了。”提起往事,陈慧中不胜嗟叹。
苏州准备实施的古民居出售的一般程序是房地产开发公司从房管所取得产权,进行搬迁和整修后再卖给私人,试操作中的最大古宅出售项目是位于官太尉桥15号的袁学澜故居。袁学澜(1803~1894)为清代诗人,太平天国战乱后迁入城中,购得卢氏旧宅,经整修后题为“双塔影园”。据袁学澜自撰的《双塔影园记》所述,这处宅院“堂屋宏深,屋比百椽”,而袁氏最为得意的是利用宅侧隙地亩许,修筑成园。此外据民间传说,在袁学澜之前,此宅曾为金圣叹的故居。时过境迁,双塔影园最终沦落为苏州几百个大杂院中的一个,那个深得袁氏喜爱的花园早已荡然无存。
负责整修袁学澜故居的是苏州沧浪房地产开发集团,在已修葺一新的花厅里,董事长史建华指着几块楠木隔板对记者说:“大多数构件都是原物,这里的砖雕、木雕极具明清特征,苏州大部分控保建筑只是局部建筑符号有价值,袁学澜故居的艺术价值则比较完整。”史建华尤其强调故居和周围环境的相融性,“苏州有些古建筑保存得不错,但旁边被盖上高楼,欣赏价值就大打折扣。袁学澜故居则保持了边上有条河,门前几株树,周围一片粉墙黛瓦的风格。”
在1997年史建华决定投资整修双塔影园之前,这里共住着68户人家。“搬迁费每户10~15万元,再加上修缮、改造和维护的费用,我们一共投入了1600万元。”故居现在的花园是史建华亲自设计的,由于原来花园没留下任何图样资料,他在设计中参考了拙政园的布局。
袁学澜故居在叫停前标价400万美元,史建华称这个数字有点保守。据他介绍,来看房子的人已经有不少,许多是海外华人,一般还带个风水先生,也曾有台商考虑把园子买下来作为苏州台商会馆。然而看的人多,故居却始终未能出手,据了解情况的人透露,沧浪集团和史建华本人都为此面临很大压力,毕竟1600万元的投入不是儿戏。史建华承认双塔影园目前还缺少商业上的包装,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故居的使用价值如何定位?王仁宇当时是力劝史建华整修故居的专家之一,他说:“3000平方米的宅院用来做住家显然不太合适,花400万美元买来当古董养着也太奢侈。”王仁宇曾提出意见,将整个故居分割成几个小块分别出售,以提高房屋的实用性。

桌椅几案、花窗字画中蕴含着民族文化的韵味

修复后的袁学澜故居恢复了庭院深深的景象
苏州文化局文物处潘处长在向记者解释《苏州古建筑保护条例》时说:“《条例》的设想是反映了对古民居不仅要控制,而且要维修保护的要求,把维修、改造和日常保护性措施都纳入规范化管理,并确定法律保护的责任人。”但令苏州文保单位感到尴尬的是,《中国文物保护法》修订案在《苏州古建筑保护条例》颁布后一个月姗姗来迟,尽管修订案放松了对私人收藏文物的流通许可,但仍明确规定,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不得转让和抵押。
“两者确实有不一致的地方。”潘处长说,“我们的考虑主要是结合苏州的实际情况,苏州地面古建筑数量仅次于北京,政府财政有限,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是一条新思路。而且苏州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存在这样的社会需求。文物本身不可再生,也许私人买下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总比看着文物自然损坏要好。”
“对古建业主我们有严格规定,例如不能对古建布局、结构和装修进行改变,不得改换现代材料门窗,电线线路也要规范。《条例》对违反者都有明确的处罚规定。”潘处长最后说,“小法必须服从大法,我们将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法修改《苏州古建筑保护条例》。”继续探索新的保护方式。
最后一座私家园林
“残粒园”也许是其中惟一一座私家园林,位于名画家吴待秋故居内,属于吴待秋之子、前苏州国画院院长吴■木老先生。记者一路问讯找到了这所位于装驾桥巷深处的大宅。宅院前两进是和“吴状元府”一样的大杂院,门口阿婆告诉记者:“里面是个大户人家,大门从来不开。”
为记者开门的是吴■木的女儿,她说:“平时不开门是防止有人进来看园子,人一多东西就坏得快。”吴家大厅面阔三间,额题“春谷堂”,与外面的大杂院相比,这里的厅柱、梁架、花窗和砖雕保存得较为完好。厅里没有暖气,82岁的吴老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不时朝手心呵一口热气,一旦发现记者听不懂他的口音,这位毕业于复旦经济系的老先生就用英语解释一遍。
吴待秋于1931年从扬州姚氏盐商手中购得此宅,取杜甫《秋兴》“红豆啄残鹦鹉粒”之意,将宅后花园改名为残粒园。“原来整个老宅有五亩二分,公私合营后我们家留下一亩六分,残粒园也保留下来。外面的就都给改造了。”大厅西侧摆着几张画橱,吴老先生说是搬出来准备修理的,“一张是万历年的,一张是康熙年的,再不修就要烂掉了。”
今年6月,吴家刚刚把老宅修过,花了4万元,这样的整修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吴老先生说,这次只是“稍微修修”,因为整修过的效果“几乎看不出来”。
“修起来不容易,要请专门的工程队,还要严格依照古建标准。”吴老先生指着中间一根厅柱告诉记者,为了重漆这根柱子,他花大价钱请来一位祖传的漆匠,因为原来用漆的配料已经失传了,只有这位漆匠能够配制出同样效果的漆来。老宅仅有的几处损坏是‘文革’时被红卫兵弄的,吴老先生把记者带到院子里,让记者看门楼上的砖雕,那里白蒙蒙一片什么都没有。“是我自己搞的。”吴老先生略带得意地说,“我用石灰把两块砖雕糊上,红卫兵没有发现。”现在只要把石灰剥去,就能露出下面精美考究的砖雕。但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保护下来,像门闩的凹槽就被弄坏了,因为红卫兵怀疑吴老先生会在里面藏什么东西。
吴宅的精华所在自然是残粒园,“文革”中大部分时期,残粒园都被充作公共花园,红卫兵冲击吴宅时,嘴里喊的口号就是:残粒园为什么不让人民参观!等“文革”结束后再回到吴老先生手中,原先400平方米的园子就只剩下140平方米。好在池塘假山洞壑仍然一应俱全,栝苍亭居高临下,亭背有门与楼层相通,园门内侧上书“锦窠”二字,吴老先生说这是花园原先的名字,和“残粒”一样都是小巧的意思。池塘北面有一株一人高的梅树,是吴老为防止孙子玩耍落水而亲手栽种的。
吴老先生说残粒园是他们老俩口消遣的去处,平日作画之余在里面散散步,过去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生每年都要来残粒园考察,吴老先生就给他们做讲解,现在精力不济,就不欢迎他们来了。送记者出门时,吴老先生说:“我确实不欢迎外人来看残粒园,这是我的私家花园,我一直小心保护。”说到这吴老先生指了指门外的大杂院,“那里已经一塌糊涂了”。
专访前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吴都学会秘书长王仁宇
三联生活周刊:苏州古民居有哪些特点,保护古民居意义何在?
王仁宇:最反映各地城市特性的不是古庙古塔,而是古民居。古民居都是在当时文化经济情况和自然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苏州民居外观除了高低错落、粉墙黛瓦,并没有太多讲究,但是非常看重内部装饰,砖雕、木雕非常文雅,不像安徽民居讲求繁复。苏州园林其实就是古民居的延伸,是大宅里的花园,苏州人不爱露富,再漂亮的园林都是只开个小门进去。如果这个城市还保留着一大批传统民居,而且这些民居很有生气,居民在里面住得井井有条,那么宏观的社会、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
三联生活周刊:苏州古建筑保护的现状如何?控保建筑的情况和文物保护单位有何不同?
王仁宇:自1982年苏州历史文化名城地位公布以来,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都得到了较好保护,拙政园、虎丘塔等著名景点自然是由国家保护,此外学校等教育单位使用的古建也占很大比例。苏州是教育之乡,老学校大都建在古建筑里,例如苏州十中在原先的江南织造府,苏州幼师是李鸿章祠堂,景范中学是范仲淹义庄,在市里资助下,这些建筑都得到了较好整修。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古民居的保护。1982年和1984年我们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普查,基本确认了苏州城里控保建筑范围,有的是深宅大院,有的是名人故居,从外观上讲,它们是古城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内涵讲,它们是名人活动的集中地,是文化的特殊载体。我在文管会20多年,花了大量精力不让它们被拆掉,现在苏州古民居总体上保留下来了,但是严格意义上的保护、整修还谈不上。
三联生活周刊:造成苏州古民居年久失修、损坏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仁宇:解放后苏州城基本没造什么新房子,就是拼命把居民塞进一座座深宅大院,原先一个大宅院就是一家人,后来纷纷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随着新人口不断出生,乱搭乱建现象也泛滥成灾。这些大宅公私合营后产权归房管局,因此住户不可能像私家房子一样爱惜,破坏情况比较严重。袁学澜故居修过后很不错,但要知道解放初到处都是这样的好房子,花园也都在,就是这几十年时间里被逐步破坏了。现在的情况用四个字概括就是“每况愈下”,而房管部门都在搞房地产开发,文管会是清水衙门,没有钱,国家投的那点钱用在古建筑保护上根本是杯水车薪。这不仅是苏州的问题,定海拆古城、北京拆四合院反映的都是这个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真允许私人购买古建筑,是否真能解决古建筑无人保护的难题?
王仁宇:我是引入社会资金进行古建筑保护的提议人之一,这是个不得已的下策。最大问题集中在使用上,私人买这些古建筑干什么?要他们光尽义务不可能。现代家庭结构和过去不同,三四口人住这么大房子没意义。做博物馆?苏州哪里需要那么多博物馆?怎么从政策上与文物保护角度把握,是一个大问题。20年前建设部一个专家对我说:“老王,苏州有这么多好东西不得了啊,你保护好它,等五六年后国家有钱了一定会把它们好好整修。”现在已经等了20年了,不能再等下去了,因此我认为国家必须要担负起主要责任,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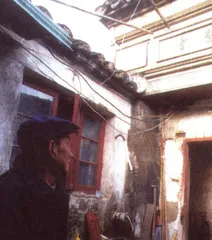
门楼照壁上的题书记载着快被遗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