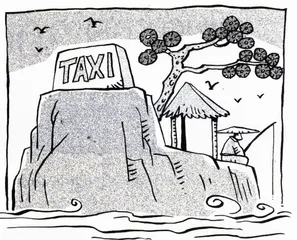生活圆桌(218)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任田 杨不过 无忌 西闪)
糙哥的糙
任田 图 谢峰
受了什么“钻石阵容”的蛊惑,姐姐我连做饭这等大事都撂在脑后,8点还没到就坐在电视机前静候《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莅临,傻笑并期待着。结果,事情和我想象得太不一样,第一集播完以后,我几乎要扑到我家12楼的阳台上放声痛哭。
我不否认,以今天的视角看来,央视版的《西游记》的确是落伍了一点。后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拍的新戏也乏善可陈,我虽然只是一介普通观众,可对道具质料还算有小小的见识,什么妖精是橡皮做的头,什么魔鬼是塑料做的肚子,什么天神的宝刀是个银样蜡枪头,我都能一眼识破……但公平地说,央视的《西游记》总体水平是不容质疑的。
现在来说无线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还没开播就听见锣鼓喧天,什么TWINS的神仙姐姐,郑秀文的观音菩萨,大S的色诱风骚,饭岛爱的性感蜘蛛精……孙悟空尚未见着,绯闻女友就出笼一大箩,把我美得心驰神往,恨不得也能提个石头变的馒头篮客串一回白骨精的小丫鬟。巨大的希望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失落,自打我看见张卫健像个玩杂耍的牵个小猴子,在一片不知是哪个公园的脏兮兮的草坪上得意地翻着二流筋斗,我的心就凉了一大截。后来张卫健回到只有20个人,哦,对不起,是20只猴子的花果山,我就更没法往下看了——所谓洞天福地的花果山水帘洞居然如此简陋!一只戴着黑框眼镜的假猴子出来冒充资深花果山土著给美猴王验明正身,于是其他武术班的小学员猴子就像听到班主任训话一样接受了新主子。在他们转身一起抢香蕉的当儿,我看到了人造毛猴皮中缝的拉链和扫把一样在地上拖来拖去的软尾巴。
失望,不是一点点。粗糙,又何止服装。女的还没出场,荧屏上只剩一群糙哥,穿着粗糙的服装,吃着粗糙的香蕉,唱着粗糙的“大笨象会跳舞”,糙得令人发指。
央视版的《西游记》固然有拘泥于原著的局限,可毕竟“胸中有丘壑”,起码场子大人物多手笔阔绰,加上作词作曲的功力,十几亿观众的追捧,再差也顶多是在“一袭华美的袍”上剪剪线头开个斜衩,修修边幅而已。可《齐天大圣孙悟空》亏就亏在,钱未必少花,大小也有十几位靓女出镜,糙哥云集更不在话下,本来可以辅以上好材料做一篇天地文章,岂料剧本太差结构松散情节乌龙,好像在破麻袋上绣富贵牡丹。台词更不如《月光宝盒》和《仙履奇缘》有趣耐推敲,只把个“大笨象”颠来倒去地唱,令观众不知导演意图何在?又在服装道具场景这些地方省些小钱,一场大戏生给拍得惨不忍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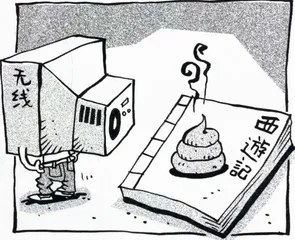
乌合之众
杨不过
自从成年以后,我很难在自己身边发现一个能够长久令人愉快的群体,和某些人在一起也能嘻嘻哈哈过一阵子,然而这些快乐转瞬即逝,多数时候会留下某些不愉快的联想和记忆。这些回忆有时候会叫人忍不住怀疑自己的品格,甚至会对人的团体生存失去信心。
小时候,大家都听过关于豪猪的寓言,它教导我们不要相互靠得太近,否则就会刺伤彼此。但这种小儿科的故事究竟能有多少教育意义,我始终表示怀疑。为了取暖,我们还是会彼此靠近,当然难免互相伤害。不过这种伤害也很有分寸,留有余地,像《红楼梦》里说的,就是防着不走了大褶儿的意思。大家还是会亲亲爱爱,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奸犯科者毕竟是少数,而且人人共弃之。
但乌干达的伊克人是一个有趣的例外。美国一个据说博古通今的哲学家跑到他们的村落里生活了两年,回来后把他们描写得极为不堪。作者告诉我们,伊克人以前是猎人,后来政府要把他们的狩猎之地变成国家公园,他们失去了山林,只好开始耕种生活。他们眼中惟一有价值的东西是食物。为了这个,孩子刚学会走路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子女会抛弃自己年迈的父母,让他们饿死。由于能量的缺乏,性活动也极少,而性的快乐被认为跟排大便差不多。死亡被当作一种解脱,因为死亡意味着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更多的食物。
正常人都会说,那是个下贱的社会。但在外人看来极度变态的社会形态,他们自己则甘之如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遭到灭顶之灾,反而保持得相当稳定。那本书的作者恶狠狠地吓唬大家说,如果传统文化遭到摧毁,我们都会变成这样。
大学时上传播学的课程,漂亮的女博士向我们推荐法国人勒庞写的书,讲的是大众心理,译名很好玩,就叫做《乌合之众》。在书里,群体被描述成狂热易变、容易轻信的动物。他们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既会随意烧杀抢掠,却也同意表现得极其无私,完全无法用我们惯常的概念来定义他们。从小被团结就是力量教育成长起来的我,听到这种理论觉得很是过瘾。
作者说,群体就是有这种“脊髓中的本能”,而妇女、儿童和原始人都是不用大脑而用脊髓思考的动物,他们盲目、轻信、缺乏理智,感情丰富而毫无用处。
就是这句话,让一直想成为一个头脑清醒干脆果断杰出女人的我记住了他。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确浪费了老祖宗们辛辛苦苦进化而来的大脑,只剩下了原始人的脊椎神经。
火锅的传说
无忌
杭州的朋友阿苏来了,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没成想,这个从小沐浴着杏花烟雨,喝龙井茶、吃醉湖蟹长大的家伙,吃起又麻又辣的街头火锅来,也是毫不含糊的。酒足饭饱、脑满肠肥地出得门来,他忽然想起什么:“问一下,我们吃的那锅调料,真的是以前人家吃剩的,没有换过?”
“那当然了,火锅调料从来只加不换的,有什么不妥?”听完我的话,阿苏脸上出现了复杂的表情,好久不说话,似乎随时等着肚子一痛,就满大街去找厕所。
几个“地主”不安起来,觉得有责任和义务使阿苏“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再纠缠吃下去的东西会不会有问题。我们告诉他,现在的火锅已经比几年前改进了好多。那时候,店少食客多,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看着一桌人吃得热闹,其实他们是好几拨根本不搭界的人。一个锅被井字架分成九格,中间一格烫毛肚鸭肠,公用,其他八格每人一格,自己确认了座位,相应地,就有了那么一个小格子的使用权。遇上同桌的先付钱走路,是最幸福的事情,我们就把筷子伸进他们的格子里打捞那些煮得火候正好的“遗产”。
阿苏听得一愣一愣的:“有这样离谱的事情?”
还有更离谱的呢。有一次我和女友在临江门城门洞那家老火锅腐败,一桌居然是由四组人拼凑起来的,一组坐镇一方。我们习惯了,也不管那么多,就开始喝酒吃菜,一边张家长李家短地聊开了。我觉得反常的是,我右手边的一位男青年,吃几口菜看我一眼,又吃几口菜,再看我一眼,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装做没看见,心想:无非是想搭“飞白”。我抓起一盘鳝鱼往锅里倒,他又看我,我恨他一眼。他说话了:“小姐,你一直喝我的啤酒,我没说什么,现在你又把我点的鳝鱼往锅里倒。其实也没什么,我请你就是了,但是吃亏在明处,我跟你打个招呼。”说完他坏笑,我听出来了,他其实是批评我吃他的喝他的没和他打招呼。我的同伴和他的同伴都同时大笑,这一笑之后,我们四个格子的菜就不分彼此了。后来,那位男青年抢着埋了单,再后来,我的女友嫁给他了。
这下把阿苏镇住了,两眼发直,做向往状。他嘀咕,现在怎么不安排陌生的男女搭配在一起吃火锅呢?我们告诉他,就是因为很多他这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堆在火锅馆门口,守株待美女,影响人家做生意,火锅馆就规定不可以这样了。
现在,这些火锅桌上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了传说,专门由重庆人讲给外地游客听,和那些流米石、望夫崖的传说一样。
隐于车
西闪 图 谢峰
寒风中呆立,看载了乘客的“的士”来来往往,忽然觉得做个“的士”司机会是个好职业。先不说一天里可以见识多少形形色色的人物,观看到多少无须彩排的故事,就说说我曾经遇见过的几个司机吧!
一次在出租车上遇见一位女司机,简直是香港电影的完全手册。一路行来,她为我办了一个香港电影知识的单人普及班。她单手握住方向盘,轻松自如地穿行在如织的自行车流中,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似乎那些香港电影和影星们的名字正漂浮在空气中,只需顺手拈来。随便提到一部十多年前的电影,她就能够报出导演、制片、主演和友情客串。
还有一次,和朋友在出租车后座上胡乱聊起时下的诗歌翻译问题不少。司机冷不丁接过话茬,对我俩的看法深表同意,并以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例对几个翻译版本的质量做出了评判。他甚至痛心疾首地引用了弗罗斯特的话来描述诗歌翻译的现状:“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让我俩大吃一惊之余不敢放肆。下车的时候,我恭敬地向这位看上去四十出头的司机大哥递上一张名片,心里想:世上有高人啊!
另一回,有辆空出租车驶来停在面前。我正准备上车,司机却探头出来说:“对不起,请您上车等一下。”他打开车门走过我身边,朝一个报摊小跑而去。不一会儿他跑回来,手里拿着一份《南方周末》,坐回驾驶座发动引擎时还不忘匆匆地瞄了一眼报纸的头版。
我觉得这司机挺有意思的,忍不住说:“这报纸比以前差了。”
他看了我一眼说:“还是可以,比其他的好吧?起码,朱学勤还在上面发东西呢!”
“哦?你喜欢读朱学勤?”
“是啊,我很喜欢。”
这个司机看上去年纪不大,一双眼睛大而有神,笑吟吟的样子。
我试探的问:“那你看过他不少的东西喽?”
“不多吧。我比较爱读他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这时有人在呼叫他。他拿起话筒:“哎呀,你们去吧,我待会儿就到。别打搅我,正和人讨论问题呢!”
“鄢烈山的文章也还在写呀!”他转过头来和我说话,同时麻利地一转方向盘驶上另一条大道。一路上,我俩谈了不少有趣的问题,有很多共同的看法。我只恨这路程太短,不能和他酣议一番。我真相信:大隐隐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