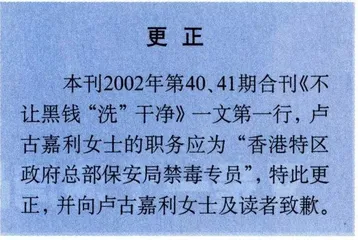读者来信(215)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张小树 徐都快 刘青潭 韦文 韩福东 周志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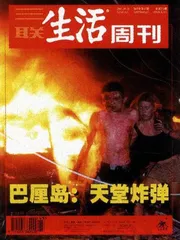
“接踵而来的爆炸、枪击、劫持等恐怖事件让世界的注意力暂时从艾滋病、战争、经济衰退中移开,一个在哲学上延续了很久的悖论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挥之不去,谁制造了这些事件,我们指的不是恐怖分子,是上帝吗?”
北京 张小树
一人五张身份证的制度环境
商人黄先生的户口在北京,2000年春节前到深圳出差时,被几个身着“迷彩服”的人当作“盲流”关了一夜,原来是没有暂住证。因为他要在那里长期做生意,于是找人花4万元办了个深圳户口,有了深圳身份证。此后,他不但不必担心查暂住证,而且做起生意来也受益颇多。于是,去年他在武汉、海口、郑州注册了分公司后,第一件事不是开展业务而是先给自己弄个当地户口和身份证。每次出差,他都带着“5张同名同姓却不同地方不同号码的合法身份证”。
怎么会这样呢?是什么东西造成了黄先生这样的尴尬?《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是1985年颁布的,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中有的规定现在根本不会执行或者无法执行,比如“对本乡镇以外的人来集镇拟暂住三日以上的,由留宿暂住人口的户主或者本人向公安派出所或户籍办公室申报暂住登记,离开时申报注销”。至于“对暂住时间拟超过三个月的16周岁以上的人,须申领《暂住证》”的规定,现在有没有必要存在都值得探讨,但不办《暂住证》要罚款的“实施细则”让执法部门将其变成了“执罚经济”。这个关乎1亿多流动人口的《暂行规定》一行就是17年了,也没有个修订改进,而且制定者是公安部,执行者是公安部门,这种“部门立法、部门执行”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所谓“盲流”问题。黄先生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所以没有当地的身份证;因为是出差,所以也没有当地的暂住证;没有这两证,那么,你就是“盲流”,所以被“关了一夜”。“盲流”这个名词诞生在50年前,当时的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说了这样一句话:克服农民盲目地流向城市。随之而来的一场“抓盲流”战役延绵近半个世纪,至今不绝,“盲流”被抓、被罚、被收容的报道时有所见。今天,在1亿多公民享有“流动自由”的今天,“盲流”是一顶荒唐的高帽。
杭州 徐都快
被警察摁在床上
西安有一对夫妻在家里看毛片被四个便装警察骗门而入,丈夫举棍反击,结果被警察摁在床上最后被光脚带走。完了还因为“妨碍公务”先被治安大队刑事拘留,然后又被公安局批捕。
关于这事网上争得热闹。不过焦点只有两个。一个是警察同志在入门“执法”的过程中到底有没有足够鲜明的证据表明自己是在执行公务。
另外一个焦点是关于夫妻在家里看毛片的。关于这点,我有两件事一直想不明白。一个是,从哪儿跑出来的这么无聊的“群众”要举报这种事情。对于这种热爱别人的“房事”活动的人,是不是应该治一个什么偷窥罪之类的东西?这种助长打小报告的行为,好像对于以德治国的方针没什么好处。另外一点想不明白的就是,咱们国家有明文规定禁止淫秽录像这种东西在市面上流通,可在自己家里看毛片有什么适用的法律法规呢?
西安 刘青潭
不集中居住的权利
10月21日《京华时报》报道:目前在辽宁大连旅顺口务工的外来民工告别“窝棚”和租房寄宿,已经全部搬进外来人口公寓或生活居住区。此举不仅提高了外来人员的生活质量,而且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公安机关的对外来人员的统一管理和治安防范问题。将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到一起居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控制和减少外来人口犯罪率”,也或许还能像新闻中所说的“提高外来人员的生活质量”,但即便是如此,这“成果”的获得依然是以极大付出为代价换来的。
这代价首先就是外来人口的自由居住权受到了侵犯。定居权应包括自由选择城市生活的权利及在一城市内自由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我既有权在这个城市生活,就也应有权自由选择居住之地,有不去不想去的地方生活的自主决定权。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将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与生活的人分为两部分,泾渭分明,其所倡导的究竟是什么?不管表面上有多么充分的理由,都无法掩饰这做法后面躲藏的不良意识。人不是动物,所以不能随意集中起来居住。人尽管职业、收入会有不同,但任何人的尊严与人格都应得到完全的尊重。
几则类似关于“外来人口公寓化管理”的报道中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即组织外来人员集中居住是不是一种强制性措施?里面的居民是否都出于自愿?
南昌 韦文
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
据报道,一场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干部学位、学历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有关部门表示,全国各级组织部门将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通过在职学习持有并载入档案的学历、学位证书,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清理,如果发现问题,将予以坚决纠正。这次清查工作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我不敢对它抱有太大期望,一则从贩假者手中购买的非正规文凭或可查出,通过正规院校流出的正规“假文凭”的清查存在困难;二则从报道看,对持假文凭者的惩处力度不够;三则仅靠一场运动式的打假必然产生反复,因为产生这种假文凭的土壤还在;四则清查工作能否按上级领导的意旨认真贯彻执行,还有待检验。学历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是开放社会的一对孪生子,而一个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整套能维系信任和社会秩序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的公正性又有赖公众的监督和各部门的制衡。从制度上建构游戏规则,而不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
高信任度是一个社会持续繁荣的必要条件。这些权力“黑客”的破坏行为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相互不信任,并最终影响了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在于文化和政府部门还未形成相互制约的独立关系,再加上当事者缺乏道义上的约束,于是供需双方产生共谋:我靠贩卖文凭获得经济利益,并且结交权贵。你则凭借“假的真文凭”仕途畅通。这种个体间的“双赢”最终却必将导致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惨败。
北京 韩福东
居民家底的“假象”从何而来
今年5~7月,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直辖市)进行了首次城市居民财产调查。10月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让我们看到了新世纪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底:截止到2002年6月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为22.83万元。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统计结论遭遇众多质疑。
针对22万元的平均值让许多人有挫折感,此次调查负责人之一、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综合处处长程学斌解释说,平均数是有假象的,它注定大部分的人都在平均数以下。在这次调查中,财产最低的人可能只有两三万元,却不可能是零,更不可能是负值;但财产最高的人就没谱了,可能是500万元,也可能是1000万元。在这种“上不封顶”的情况下,一个富人能把多少个穷人拉上来?我们看到平均值时感觉心理挫折也很正常。
我们相信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在调查统计过程中的态度是严肃的,步骤是缜密的,但统计为什么会出现“假象”呢?笔者认为,调查统计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底,应当按城市的大小与经济规模分类,这样得出的统计数据才更可信。众所周知,中国地区间发展并不均衡,胡鞍钢先生“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说法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将“第一世界”的城市与“第四世界”的城市放在一起加权平均,其结果只可能是“第一世界”不相信家庭财产会这么低——在北京住着80平方米的房子,仅这一项就值50万不动产;而“第四世界”则不相信家庭财产有这么高,对小城市的居民来说,由于当地房地产便宜,折算的价格比较低,他们会觉得22万元不可思议。22万元的平均值让许多人有挫折感,这不令人担忧。我所关心的是:这样的“平均”数据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合肥 周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