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国案件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金焱 王君)

在中国农行系统,丁志国及其相关案件是建国以来“级别最高”、“数额最大”的。
官运与精明
于保国是农行黑龙江分行公司业务处处长,他对数字的记忆很准确,比如丁志国离开牡丹江的具体日期,哈尔滨到牡丹江的距离等等。
于保国从1990年起就在农行牡丹江分行工作,一直到2001年从牡丹江行行长调到省农行做处长。1997年,丁志国从牡丹江行行长调到哈尔滨行做行长,那时哈尔滨行还是计划单列,直接归农行总行所辖,丁志国的调动因而引人注目。
于保国当时以主持工作的副行长的身份为丁志国送行,他很快成为丁志国的继任。于保国记得,他与前任牡丹江行行长丁志国先后成为全省农行系统“一把手”中最年轻的干部。这种巧合现在在于保国看来,有着更多非巧合的因素。
牡丹江到哈尔滨329公里的路程,于保国与其他几个副行长及退下来的老行长很隆重地一直将丁志国送到目的地。反过来看,从哈尔滨到牡丹江,同样也是很多官员常做的选择。
知情者说,前些年黑龙江旅游还不发达,景色旖旎的牡丹江因为有镜泊湖、火山口地下森林而成为接待客人的主要去处,而便利的交通网络对于在牡丹江的为官者来说,就有了更多接触“领导”的机会,比如牡丹江农行在镜泊湖就专门设了一个接待点。
在牡丹江市政府工作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丁志国在当地做农行行长期间,是绝对的“知名人士”,与市里很多领导都很熟。另一位后调到政府工作的负责人也一再强调丁志国的交际能力“相当强”——他用了一个当地的方言:“敞亮。”说他同省市领导在一起时办事比较爽快,“哪个领导求他办点事他都给办”。与此相关的一个说法是,丁志国案由中纪委直接立案,就是因为他与省里一些领导关系相当不一般,“在黑龙江很可能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这些表象引起很多私下里的议论,人们说丁志国的势力在牡丹江时就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不过省农行办公室的负责人提醒记者,牡丹江行在省农行系统里各项指标完成情况都处在前面。这里面的一个背景是,黑龙江“地处不发达地区”,农行黑龙江分行经营始终比较困难,而牡丹江分行显然是一个亮点。于保国也说,牡丹江资源丰富,综合经济较强,城市经济体系直接决定了牡丹江的富裕,这种资源优势是丁志国在黑龙江农行系统脱颖而出的一个基础条件。
同样有过牡丹江行行长经历的于保国说,丁志国在牡丹江农行呆了8年,从最开始跨地区交流干部时的正科级做到副处级,从副行长做到行长,“牡丹江给他带来非常关键的转变”。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转变是丁志国在依兰农行做行长的经历。1979年人民银行与农行分家,丁志国来到依兰农行,此前他已经在银行系统干了十年左右。一位熟知他的县农行人事科负责人说,60年代末高中毕业后,丁志国回到富锦县,在乡里的信用社做事。从出纳到出纳股股长、会计股股长,直到农行行长,这样的经历使他对银行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十分精通,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丁志国前期升迁的评价都是:他纯粹是自己干出来的。
不过在依兰,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丁志国的精明。依兰距哈尔滨东部251公里,是一个在三江汇合处的农业县,自然风光之外有五国城遗址。张峰说,因为皇帝曾经呆过的缘故,这里的烹饪技术远近闻名,在其归合江地区管辖时,就是从哈尔滨到佳木斯必经的“打尖”之处,农业县里农行的位置显然有很多机会与地市领导打交道,丁志国的精明也在这时开始在权力体系里有了伸展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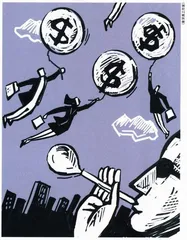
行长与长官
1997年在丁志国来到哈尔滨,哈尔滨的金融机构分业管理已经进入第二年。哈尔滨在继1995年撤销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所办的信托投资公司,改建为支行后,1996年又撤销市农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改建为支行,三家信托投资公司和部分信用社下属证券部的转让和撤销工作已经完成。
这段时间也是农行发展跌宕起伏较大的时期。哈尔滨农行的一位中层干部说,信用社先分了出去,然后农业发展银行也运行了一段,有些项目运行得并不理想,于是有一部分农副产品收购等企业又回拨给农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等同于财政资金的替代,政策性的扶贫贷款也都加在农行身上,“这些政策性的东西让农行在效益上生存更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说话有时平卷舌不分、身上有时也表现出官气与傲气的丁志国在哈尔滨并未表现为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者。丁志国不太讲究穿着,但他注重社交。张峰说他听到丁志国唱歌时很惊讶,想必丁志国的专业水准不会特别出色,但是他让人惊讶的基点是他的农民出身,对丁志国而言,这只是他融于上层权力体系的一个努力。
无论丁志国在哪一级农行行长的位置上,他都更像一个行政官员。农行的一位前分行行长举例说,行长首要的任务并非业务,“大到不能叛国、走私、吸毒,小到计划生育、门前三包你都得管,也就是一把手负责制,这就使银行的行长不能一心研究怎么赚钱,而是肩负着政府管理的职能”。他说,如果不注意这些就是不注重社会形象,文明先进评不上,就直接影响银行行长个人的地位和政绩。
而一个人是否有资格做银行的行长,有关人士指出,过去的评价标准首先是要对会计业务比较熟——而现时状况是银行会计业务比较简单,银行本身的业务就较单一;第二点是政策把握得准,其他是政治上的要求。
于保国说,农行为农业服务在黑龙江有更深层的影响。他说,最近几年不提“黑龙江是商品粮基地”了,换成了发展“绿色农业”,而其实产业政策的调整造成很大的不良贷款。另外重要的一点是,“财政体制没改,经济体制改了”。
丁志国有相当数额的财产获得无法被认定为犯罪,其中包括丁志国一儿一女的结婚庆典等场合下收到的礼金。在媒体披露的行贿者名单中,民营企业占相当比重,而这些民营企业有一部分就是从乡镇企业发展而来。“过去的政策是让农行支持乡镇企业,现在乡镇企业纷纷倒闭,留下大量的风险和呆死账。”
在这样的土壤下,被评价为“精通银行本币业务”的丁志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个人关系网的建立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金融教研室副教授王雅杰说,在1999年之前,国有银行的信贷体制是由总行下达信贷指标,再层层下达,有了这个指标,给谁不给谁就有了学问。她说她曾到鹤岗搞一个货币政策的课题,下面的人告诉她,由信贷结成的关系网很厚。
对于丁志国罪行的追诉,最早的一笔是在1995年7月他任牡丹江农行行长期间,他由牡丹江市农行副职提为正职时间不长。那次丁志国是为牡丹江一家药厂贷款出力,收到的回报是5000元人民币和2块雷达表。丁志国更为熟练地施展权力带来的方便是在哈尔滨期间,这在检察机关对他的起诉中也能得出相同的结果。
其中一笔的行贿者是黑龙江省青冈县县长。当地人介绍说,青冈县两届政府都因为县里的项目工程而向省农行申请过贷款,其中一位县长现已升职。另一位县长为感谢丁志国以黑龙江分行行长的身份促成此事,以2万元人民币及一部价值4500元的手机表达了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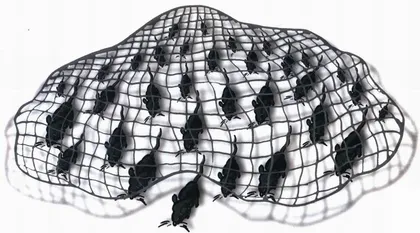
更多谢意来自企业。丁志国连续两年春节收到福顺集团分别送来的10万元钱,还收到牡丹江市某商业大厦送的一块价值7800元的名表,原因都是他提供了贷款帮助。
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说,丁志国在专案组面前一气交待了十余笔受贿问题,其中包括1998年6月,他把市农行楼的工程发包给某房地产公司。这样一个工程的感谢费是4万美元和一块价值4万港元的手表,据说丁志国在事隔二年后,又向该公司负责人索要了5万块钱。
此事的背景是1998年夏,在任哈尔滨农行行长期间,丁志国开始为农行职工建家属楼,还在道里安升街购买了部分家属住宅。一位农行干部事后说,农行待遇不好,丁志国这次让职工得到了好处,不过很多人觉得他的魄力更多的是一种“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做就做的魄力”。
中国农行总行有关人员透露,家属楼的工程还将当时主管基建的哈尔滨农行副行长牵了进去。在有关文件中,这一事件被描述为:该副行长把一部分钱以工程费的名义转到开发公司,开发公司又将80万元人民币给了承包工程的那家公司。知情人说,钱最后到了这位副行长手上,目前这位副行长初步被认定,其受贿金额达到1000余万元。
制度裂缝
丁志国的几次移居都伴随着职位的升高,他的迁移方向也几乎以哈尔滨为圆心行进。不过在1999年前后,他升任农行黑龙江分行副行长之后,他的麻烦明显多起来。
很多农行职工都还记得1999年1月份那次查信用证事件。有人总结说,丁志国在位期间是黑龙江农行系统贷款发放最混乱的时候。早在 1998年,农行总行已经提出下面各 行应成立贷款审查委员会,以确保 贷款发放到位,比如要有会议纪 要,说明有哪些人参加,哪些人投 票,这些都应作为档案永久保存。
不过在当时,这些制度并未 建立起来,基本的做法还是几个 人私下里串联一下就定了。工作人员说,就在丁志国出事后,农行总行来查记录,依然是失望而归。但问题并不等于没有。人们回忆说,总行主管业务部门也曾来查过,也曾发现过一些小的问题,但也都通过内部关系摆平了。
1999年1月份那次清查真的查出了问题。这样大规模的查处私下里的说法是因为不停有人在告。那一次的矛头直指丁志国,因为他主管国际业务。焦彦文与张庆贤这一次被纠了出来,他们因违规开信用证被降职处分,不过这种处罚并未掀起大的波澜,大多数员工认为这只是从规章制度的角度简单处理一下。
事后有人抱怨说,国际业务部既是一个部门,也是一个支行,对于信用证他们基本没有额度限制,想开就开,也不管合格不合格。最主要的疑惑是,丁志国因为“不知道”而没受任何牵连。
黑龙江省委工作人员于先生原来与焦彦文在一个单位,两个人的爱人都是独生女儿,他们还曾一起去要过第二胎,现在焦彦文的大女儿上了大学,二女儿学习也非常好。于先生说,当时检察院去查金额达一亿多元的信用证查了好几次,几次都没有突破,他们私下里听说是丁志国帮着“扛过去”了。所以丁志国出事后,身为哈尔滨市农行国际业务部经理、主管审批国际信用证业务的焦彦文也保不住了。
焦彦文的有趣之处在于,《哈尔滨日报》记者韩云鹏报道说,焦彦文在省农行金融案查处过程中,主动找到专案组以示清白,结果由于紧张而辞不达意,最终反而自投罗网。后来焦彦文几次反复,甚至“装疯卖傻”,检察机关为此还请来了精神病专家。
更有趣的是,于先生说,焦彦文被他们称为车轴汉子,身高只有1.65米左右,矮而胖,当年他是他们中间“挺懂法”的人——当时农行里出了一个贪官,是焦彦文帮着办的案子。
焦彦文被查实的事件发生在1997年12月至1998年8月间,而农行总行从1998年开始的查处行动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让人吃惊的是焦彦文权力经营的动作之大。检察机关指出,一家塑料制品公司董事长以公司名义,从焦彦文处申请了三张国际信用证,合计金额为259.8万美元。然后,他从日本进口了24台旧水稻收割机,只用去了8.4万美元,余额由对方从银行全部提出,以现金的形式给这个董事长汇回1900多万元。
张庆贤是焦彦文的副手,也因信用证问题而立案,不过他显然只是小打小闹。哈尔滨南岗区检察院工作人员说,1998年5月,张庆贤为哈尔滨颇具盛名的“隆马特”公司王安祥违规办理了信用证,王安祥为表示感谢,通过市农行开发区支行副行长张伟平做中间人,送给张庆贤人民币10万元。不过,张庆贤惧怕上级查出此事,把钱又退给了张伟平。而在事前,王安祥为了保证自己公司的信用证保证金比例不提高,已经先行送来一部8700元的爱立信手机和2000美元。
市农行国际业务部结算科科长刘俊镅是焦彦文与张庆贤的下一级权力核心。1998年1月至9月,王安祥为保证其下属的盛泰、盛祥电子有限公司能在未向银行交足信用证保证金情况下,从黑龙江省农行哈尔滨市分行国际业务部办理出信用证,先后送给刘俊镅5000美元、电脑一部和桌椅等(价值10840元),以及去欧洲旅行的费用15000元。此后,负责办理信用证审核的刘俊镅,在为王安祥公司办理信用证业务时总是一路绿灯。
一位已经离开农行黑龙江分行的人听到丁志国等人出事的消息后说,在许多银行中,长官意志不可避免,“愈上层离市场愈远,愈下层离市场愈近”。王雅杰则在实际调查后说,银行的裙带关系很重,额度大一些的贷款一下子会牵连到很多人几乎是必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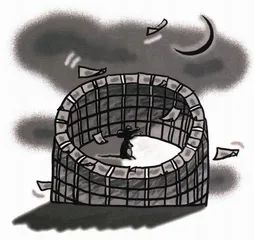
信贷的垂直管理直接带来大量权力空间。农行的一位中层干部不无反感地说,以前开发客户不是以市场为导向,一些部门不是研究怎么开拓市场,而是自己这个部门拥有哪些权力,哪些权力可以对下面形成制约。这种积重难返的矛盾现在刚刚开始有所转变。
黑龙江农行系统主要面对农业,农业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直接影响到农行的改革;每年农行的信贷都有一些大的原则,比如今年支持一些大的方面,这样执行起来就有了充分的游离空间。
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冯学林处长谈起丁志国案件,最感慨的是监督空位。他说,企业实行的是上级党委任命制,这样下级不敢监督,同级没法监督,上级离得太远又不了解情况。“中国的一把手的共同问题是,从决策的角度他的权力都与经济相关,叫做一重三大,包括大项目、大资金和重要人事任免等,这样领导权力过大,权力容易失控。”在冯学林看来,这个问题在银行里“显得更严重”。
关系和交易
黑龙江省海天律师事务所韩振华律师9日从朝鲜回国,他是丁志国为自己指定的辩护律师。在电话中,韩振华还为两件事而感慨,一个是“丁志国的认罪态度”。韩振华转述丁志国的话说,当时有关部门抓他时,涉及到的问题均未查实;而对丁志国交待的问题也毫不知情,“我办了二三百起刑事案子,像丁志国这样的认罪态度真是罕见!”韩振华的另一个感慨也由此而来。他向记者回忆起丁志国案开庭时的情景,“气氛很压抑”。
几乎同样的感慨来自丁志国的女儿丁辉的一审代理律师。他说,代理了这么多案子,惟有这一次是“没有办法做工作”。丁辉在2000年的圣诞节被逮捕,而为她找代理律师的是她爱人的哥哥。丁辉的二审代理律师、黑龙江省孟繁旭律师事务所丛彪解释说,丁辉进去时,她的哥哥丁瑞、母亲和爱人都在逃,留下丁辉的孩子由婆婆照看。
31岁的丁辉与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她的上司和同事对她一致的评价是,大专毕业的她人很聪明,比较懂业务而精明;父女俩另一个相似之处是,有关部门本想通过丁辉了解她父母的问题,没想到她父母的问题没了解到,丁辉自己供述出受贿20万元。
丁辉所在的省农行直属支行计划科是农行里面的热门科室,丁辉是科长,银行具体业务的权力主要掌握在信贷手中。媒体报道说,检察机关发现丁辉的个人财产高达400多万元,包括大量的银行存款和股票。现在我们无法获知这400多万元的来龙去脉,但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向记者描述丁辉的退赃经过倒颇有说服力。据说2000年9月,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长城建筑公司与建三江七星农场发生债务纠纷,七星农场副厂长孙成尧为避免偿还债务,以能帮贷款为由,介绍长城公司经理常成团认识了建三江农行副行长于海岩。但因当时建三江农行没有贷款指标,于海岩找到熟人丁辉,让其帮忙弄一笔200万元的贷款指标。
知情人解释说,以前的信贷体制是资金规模双向管理,由于当年的贷款指标已办完,丁辉“要”来了第二年的指标,批出200万元的指标。常成团得到该款后,从中拿出20万元,通过孙成尧,委托于海岩专程赶到哈市表示感谢,作为“提成”送给了丁辉。检察机关解释说,在黑龙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利息照付的前提下,贷款的好处费是10%,而在中国的一些先进地区,“信贷谁都不愿意做,银行行长中也只有最小的那个管信贷”。
丁辉的退款据说非常快,“她的几个朋友在她打过电话后不久,就拿了一玻璃丝袋子钱来了”。
于保国说,曾有一句话叫政治任务商业化经营,而希尔顿•鲁特指出,“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交易在中国非常盛行”。“如果金融中间人具有优先获得政治决策信息的能力,在交易时,他们的信誉就会明显上升。这些中间人实际是公共信息的私人经纪人。对他们来说,规则的隐蔽性或模糊性至关重要。如果中间人有很牢靠的关系,并能获得有关国家、国家财产以及国家重要决策的信息,他们就能决定相关资产的业绩。因此,金融市场被这些公务员形成的关系网取代,对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实权的官员自然会想办法找机会谋取私利。”
围绕着银行的关系与交易中,“企业家”集团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庆市北方汽配城是大庆市最大的也是“根最深”的汽配城,大庆首届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就在北方汽配城开展。有如此规模的一个背景是:1999年5月,由省农行副行长丁志国牵线搭桥,大庆市农业银行行长王世国为大庆市北方汽配城贷款三次,共计2800万元。一个月后,大庆市商业银行筹备办主任张英达(后升任大庆商业银行董事长)又审批给北方汽配城1000万元贷款。
此次丁志国系列案中,与北方汽配城不相上下的是林甸县碧港淀粉有限公司。在黑龙江某报社副总编辑王某帮忙下,该公司通过省农行营业部副总经理张辉找到了大庆市农行行长王世国。经王世国帮忙,大庆市农行报省农行批准,给该公司贷款1500万元。
原来农行的五级分类是:总行、省分行、地市行、县支行和营业所,现在变成了三级管理一级经营。赵立国所在的林甸县碧港淀粉公司属于大庆,而赵立国就在省分行、大庆行和林甸行三级系统内总共行贿49万多元,对象包括林甸县农行行长孙攀山、该行副行长吴建忠、该行信贷部副部长周维生;省农行营业部副总经理张辉、省农行专项信贷处处长黄希武、副处长张朝民等人。
媒体报道说,丁志国本身还有无法认定是犯罪行为的灰色财产,并点了数家企业的名。知情者说,其中一家民营企业老板专门用贷款来的钱建了一幢200万的豪宅,与赖昌星的“红楼”相似。这家以木材加工起家的民营企业,不断鲸吞财富的资本就是贷款,用贷款建成的财产再做抵押,再换贷款,循环往复。
丁志国案件又一次印证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传统:“关系”,它在 双轨制经济中仍然十分重要,由此政府官员和公司经理的“个人关系”控制着资源的分配。公司经理不得不与相关 的政府官员和其他公司的经理保持 很好的关系,来保证能够得到维持生产所需要的资源(例如电、水等)和及时地将所需要的 原材料与中间产品交货。
有学者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能够有效分配信贷的高度竞争的市场,为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筹措资金。对中国的未来来说,建立高度竞争的金融市场同发展高度竞争的产品市场一样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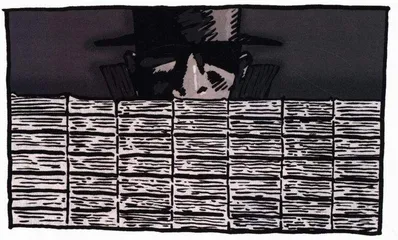
贿贷与丁志国们
王君
数年前从事金融监管,经常面对违规违纪的银行和“丁志国”们,心情之压抑有如医护人员不得不面对病患之痛苦。虽有职业性的表面平静,然而内心深处终究不如身临运动场时能够体会到的健康向上气氛。这里需要事先申明,本人与丁某从未谋面,更无过节,因此加上引号意在泛指一种现象。表面上看,“丁志国”们并未直接抢夺他人财物。但究其实质,贿贷(这里权且将以贷索贿和以贿求贷的行为统称为“贿贷”)造成的后果,最终还是要全体纳税人承担。
几年前在瑞士巴塞尔与各国银行监管的高官们,一起讨论修改《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记得会上对于如何防止银行的称谓被人滥用,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在核心原则中规定,使用银行字样,须经监管当局批准,可见此事非同小可。而银行家的称号,又何尝不是严肃的事情?前些年在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人,政治头衔、学位、职称一大堆,但是心态、思维与行为方式与真正的银行家相去甚远。这是因为,一个合格的政府官员,未必就是称职的银行行长,因为这两种职位对人的素质和训练方面的要求,有很大差异。
真正让人不安的是,丁志国一案涉及到数十人,有那么多农行内部人员卷入,并且多年来互相之间行贿受贿,像是一个从里边往外腐烂的桃子。尤其是丁本人,一边作案,一边升迁,结果能够供其支配用于贿贷的资源也随之膨胀。这种没有正式组织形式的团伙作案,尽管背后的原因是收受贿赂,但是或提拔或放贷,书面上一定都会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些我们往往无法从案件本身直接观察到。
本来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经营的是他人钱财(other people's money)。银行把吸收来的公众存款,贷放给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既为经济增长提供融资,又给存款者带来必要的回报,如此才是银行经营的正道。然而就在这一存一贷之间,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学对风险的定义,就是这不确定性。银行家即使殚精竭虑,也不见得总能把每一笔贷款都及时足额收回。但是,如“丁志国”们所为,则几乎可以断定,经这“省城信贷第一支笔”发放的贷款,十有八九收不回来,最终一定沦为损失贷款。
迄今为止媒体的报道还是集中在此案的犯罪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贿贷事实如山的案例面前,探究贿贷造成的银行资产损失,会给人一种文学作品中犯忌的反高潮。待到尘埃落定,如果有心人锲而不舍地探究“丁志国”们到底给黑龙江省农业银行系统造成了多少烂账,相信必有所获。
这种本来不该发生的故事,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在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贪污受贿虽时有发生,但是像“丁志国”们这般规模和频率,则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力。然而,僵化的计划经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到了转轨经济条件下,原有的规矩打破了,新的制度尚未健全完善,各种寻租的空间,不仅比计划经济条件下大,比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也大得令人瞠目结舌。有些银行信贷员和经理人员,发放贷款如同拨付财政资金,贷的时候就没想要收回。几年前检查银行贷款质量,居然发现有些贷款连合同都不健全,更不要说其他一些必要的文件和程序。同理,在银行、企业、政府部门的财务管理方面,明显存在大量扭曲的规定和由此造成的漏洞。否则那些大额的贿赂资金,怎么会在行贿与受贿者之间顺畅地流通?一般来说,偶然作案易,连续作案难,因为银行内部控制再不济,哪怕上级审计部门每年审计一次,也不至于让贿贷连续发生;中央银行的监管,无论是现场检查还是非现场监控,总应该对“丁志国”们有所威慑。这些媒体在报道中都未曾涉及,给人留下了一连串疑问。还有,那些行贿的企业,似乎毫无财务纪律约束,给人以每一笔贷款背后都必有贿赂或者回扣的印象。前不久一位韩国同事告诉我,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政府甚至把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赠款,纳入财政预算收入,与税收收入一样受到严格的监督。仅此一点学到手就能使我们受益匪浅。
“丁志国”们虽然性质恶劣,毕竟已被捉拿归案并将被绳之以法。问题在于如何从制度和激励机制上,防止产生新的“丁志国”们。这和不良贷款的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只有从根本上减少在未来滋生贿贷的土壤,才能指望把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
行文至此,忍不住提及一件虽不十分重要但却让人产生某种黑色幽默的现象,那就是媒体报道中列举的以美元行贿的故事。这几年不止一次地读到,某某收到的贿赂中有多少美元等硬通货,似乎用于腐败的媒介正在出现一种“美元化”倾向。众所周知,我国是外汇管制国家,在境内的各种交易必须以本币计价和结算。虽说行贿受贿不是公开、合法交易,因此讨论其币种的构成似乎有书生气之嫌,但是从法理上看,难说不是一种违反外汇管制的行为。不知法学界的朋友作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