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宪法遇到监督法
作者:巫昂(文 / 巫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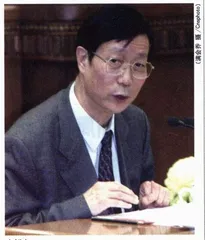
应松年
三联生活周刊:对监督法的设想由来已久了吧?
应松年:宪法里面本来就有一些关于监督的内容,1984年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在监督方面需要有更加细致的规定,国外通常就是放在宪法里,而中国根据自身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与监督。这个草案对监督宪法实施也做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基本上是对宪法和《立法法》等现有规定的复述,长期以来对于设立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呼吁,在草案中没有得到响应。
三联生活周刊:因此,您主张拟建宪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相关职能,现在基本上属于由那些机构在执行?
应松年:宪法委员会主要监督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有无违章违宪的现象。从理论上讲,现有规定关于宪法监督的框架似乎比较完备,这套体制自建立以来成效不大,以致长期以来宪法监督没有很好地落实。
现在人大下边设立了好几个专门的委员会,比如内务司法委员会、环境资源委员会、财经委员会等等。它们是针对各个集体方面,比如我兼任全国人大内务与司法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机构负责司法(公检法)与内务(人事民政等)的执法监督,要派出代表,针对某个专题,比如去了解残疾人保障法这几年在国内某个具体省区的实施状况。当然,这些机构不针对具体事件与案件,那应该是由法院与公安部根据司法程序具体操作。我认为,宪法委员会可以作为全国人大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由全国人大授予一定职权,明确审查程序,这样既符合我国的宪政制度,也有利于解决实践中最迫切的法规、规章合宪性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宪法委员会是不是宪法法院的前身?
应松年: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是这样,但宪法委员会有其特别之处,目前中国单设宪法法院的可能性还不大。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普通公民比如我,发现比如北京市交通规则条文与全国的不相适应,其对交通违规的处罚金额要高于全国的规定,有什么渠道能够反映给这些监督机构呢?
应松年:理论上讲,要是地方法规与行政法规有冲突,个人可以直接去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此进行审查。比如你举的这个例子,如果是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到国务院法制办去反映;但如果是市人大制定的地方法规,就比较难办了,还是要到人大去解决这个问题。目前人大常委会通常没有力量来处理这类问题,如果成立宪法委员会,它是个相对独立的,它就经常要独立判断,有没有这类问题。《立法法》现在规定五个机构(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市的人大常委会),就违法、违宪问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人大常委会交给专门委员会后,最后一定要给予回答。除此之外的各部委、各级政府、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可以去提,但是是否一定回答,《立法法》没有相关规定。事实上,连前者目前都还没有什么动静,这让我们意识到程序还是不太理想。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第二点意见中,谈到了公民普遍关心的对司法机关的监督问题,因为司法公正永远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您能否进一步谈谈?
应松年:的确如此。这次草案规定了“不代行审判权、检察权,不直接办理案件”的原则,值得称道,但草案在具体规定时,似乎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比如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可以决定将有关案件向有关审判、检察机关初步询问核实。专门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将有关案件交审判、检察机关处理,并要求报告办理结果;专门委员会研究后对办理结果不满意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报告情况,并提出处理建议。”这一规定似乎与草案确立的权力机关“集体行使监督权”原则和“不代行审判权、检察权,不直接办理案件”的原则不一致,在实践中是否可能导致变相的“包办代替”,令人担忧。
有些学者仍然不赞成后者,认为法院应该彻底独立。但是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法院的独立性仍较差,原因首先是因为与政府设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包括人财物,其次是地方法院常常因为地方经济问题,要保护地方利益。这是要不得的,法院应该是全国法律统一的标志,司法改革要应对的正是这些问题。如果公民在司法中无法得到公正待遇,他们当然要求助十立法和监督机构人大。我赞成“有限监督”,但是地方上,有相当的省市的各种权力在直接监督与介入。
三联生活周刊:草案并没有官员的述职评议一项,但您认为这还是有相当必要的?
应松年:述职是由人大选出的官员或者部门负责人,定期排好队来做一个报告。然后由委员对其工作提出意见。以往述职通过通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述职的反对票有时候会超过1/3,所以很多学者就开始议论,万一不通过,应该怎么办?目前的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规定。好像广东不久前就有个环保局局长因为述职没有被通过,辞了职。
有人认为,目前述职评议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不规范,甚至走样。但是,经过几年实践,从立法上确立述职评议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何况,正是因为它不规范,甚至走样,更需要监督法把它规范起来,避免混乱。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工作报告未能获得人大通过的见解很特别,您认为其根本是对监督对象的工作不满意?
应松年:辽宁沈阳中级法院的工作报告被人大否决,引起了各方关注,它好像是第二年又做了一次。这是一个新问题,现在草案的规定仍然比较含糊,它规定不通过的县级以下的应该在两个月内再做一次,县级以上的规定更含糊,说是“可以由大会主席团提出处理意见,提请大会决定”。首先,人大否决工作报告,是因为对监督对象的工作不满意,不是因为工作报告的文字不够漂亮,所以,允许再做报告于事无补。何况,不排除第二次报告还不通过的可能,草案没有规定解决办法。我认为,应该让代表先把问题了解清楚, 一旦报告没通过,应该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抽几个人大代表,最好懂行的,调查清楚为什么没有通过,应该如何改正,如果是领导人的责任,有关责任人应该辞职、停职,甚至罢免。国外有“不信任案”,是针对内阁的,我们虽然不会有类似提法,但针对某一个工作报告还是可行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最后一条意见提在国家特别重大建设项目的报告制度上,具体如何操作?
应松年:重大问题的决定权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有职权之一,既然国家特别重大建设项目“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投资巨大”,那么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议案并由后者做出决定是完全应该的。不存在可以报告也可以不报告的情况。这一报告制度也适用于地方。重大工程每年进展状况如何,也应该是单独做出一个报告,并将其基本情况向公众公开。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草案会很快面世吗?
应松年:我们猜测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讨论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