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见了冤家不要命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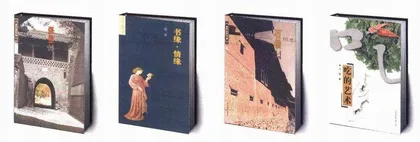
8月初外出休假,临走前在季风书园的新书中看到了一本《吃的艺术》(刘枋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刘枋是位祖籍山东长在北京居台多年的台湾女写家,文章写得朴实顺畅,有一种家里有点老底子的过来人的从容。10天后归来,听说这本书在季风已经卖掉一二百本,每天能走十几本!刘枋谈吃,是有治厨经验和社交空间的主妇谈吃,她胃口好,饭局多,而且会烧,能品味鉴艺。她的文章都是大白话,不过平实道来有时倒会显出若干机锋。信手翻翻,特别喜欢其中的《红绒线炖豆腐》。她先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大富翁,要考验他的儿子谁最能懂花钱,每人发一两金叶子,要他们不许与人分享,一顿吃光,再贵的山珍海味也花不了这些钱,结果只有一个儿子做到,他用一两金子买了很多红绒线(那时候最贵的绣花线),两块豆腐,用绒线当燃料,炖了碗豆腐。接着刘女士说了很多豆腐虽贱实贵的好处和做法,通篇说豆腐,临到结束却把话锋一转——“肉是冤家,豆腐是命,我却是个见了冤家不要命的人。再见吧!豆腐!”读红绒线的故事,觉得古人比今人聪明,当今贵人,碰到这样的难题,最高明的也就是把金叶子换成银票烧了炖豆腐,他不会去买红绒线,兜不了那么大的圈子。没有红绒线,这个秀气的故事就会变得很粗鲁。而“见了冤家不要命”的说法真好,就因为“见了冤家不要命”,凡人难得超度,凡人也不太想超度。
刘枋谈吃,在目前内地的出版物中算是最好的一种。内地读者的不幸是至今还无法读到中文谈吃第一圣手唐鲁孙的文集。几年前画家孙梁向我推荐唐先生的文章,找来一看,不是了得,是不得了。唐鲁孙和刘枋之间的距离,等于马拉多纳和郝海东之间的距离。唐先生谢世快要20年了,内地读者还是无缘读唐,这真是大陆书界的悲哀。
近些年,一批新潮知识界领袖刊物的专栏女作家悄然到位。扎西多、恺蒂、毛尖、娜斯、沈双……已经成为这些刊物的灿烂卖点。这些女生,初中之前想来都是乖孩子,差不多都有良好的双语教育背景,经过社会生活、知识生活的多次蜕变,终于修成正果。在如狼似虎的当打之年,她们出手了。她们那些叙述生动文字感性见解可靠的文章,热情地向国人介绍西潮引进新知。恺蒂的新书《书缘•情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就是她近年刊物文章的结集。恺蒂新书中介绍的人和事,在英国大概是当地读书人的文化常识,在中国多少有点海外奇谭。不过恺蒂小姐讲故事的本领很大,娓娓动听,东绕西绕,让你不知不觉就意犹未竟地把故事听完了。有时候有兴趣再听一遍,还会觉得新鲜。
常读这些美丽的文章,真觉得写作其实是非常女性的事业。翻成白话,就是说写字是件特别娘儿们的活。七尺男儿,如果别人向你陪笑脸,不是问你借钱不是要你批条子甚至不是求你去帮忙打架,只是向你约稿,换句话说,别人觉得你有劲的地方,不是你的财力不是你的权力也不是你的体力,只是你的笔力,那你差不多就像我现在这样,基本废了。
《石桥村》(李秋香撰文,楼庆西摄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张壁村》(陈志华撰文,楼庆西摄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是图文书“中国古村”系列的头两种。这套书的装帧版式和三联的“乡土中国”系列极为相像,但实际内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从《石桥村》、《张壁村》的内容来看,它们好像都属于一个中国古代乡村建筑调查的科研项目,谋篇布局的严谨和表达的规范无可争议。这两本书是按照学术要求撰写的。所谓学术要求,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半证据也不说十分话。不过公共的阅读视野有时候反而成了学术眼光中的盲点。譬如说,晋中张壁村古建筑中,最令人迷惑的是它近万米“保存完好的上、中、下三层立体古代军事地道网”,这张地道网的蹊跷之外是这么大的工程却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张壁村的其他古建筑都有文献材料)。这条地道是谁干的?干什么?当时为什么要搞新闻封锁?这样的历史之谜最能撩拨普通读者,《张壁村》的作者以存疑的学术态度将这个总是放过,没有尽全力破解。非专业的读者大概会有一些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