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08)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马小山 张卫 韩福东 钱万里 张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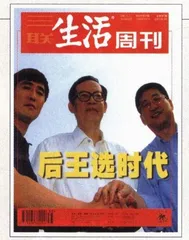
“王选自己就曾经是年轻人的榜样,那么,如何做后王选时代的模范?教年轻人赚更多的钱、卖更多的东西?不管怎样,方正做了榜样:如何将一个校办工厂转化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司。”
北京 马小山
35万人该去义务劳动吗?
就在昨天,重庆市给吃低保者作出规定:如无正当理由,一个月内必须三次参加社区义务劳动,否则将停你的“食”。新鲜。乍想,这也太苛刻了嘛!明明,吃低保者作为城市的救济对象,是弱者。他们的焦虑、困窘、失落与苦痛,别人很难体会;社会本该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关爱。毕竟,他们有劳动能力,只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落伍了,有力使不出,能全怪他们吗?
如果深一步想,觉得这规定又不算过分。因为,在重庆这座不过500余万城市人口的山城,吃低保者竟有70余万。据调查,这70万人中至少一半尚有劳动能力,因为他们正值盛年,力气和经验都不缺。那么,让这35万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诸如辖区里的环境整治、绿化美化、治安巡逻、公益宣传和学习活动行不行呢?应该行。然而,每当你经过香港人投资的得意世界广场,经过十八梯茶馆,经过东水门陋巷时,那见缝插针摆下的一桌桌搓得山响的麻将,桌边围坐的一张张正值壮年的面孔,又难免令人心悸:这中间,有多少人宁愿将时间不舍昼夜地消耗于斯,也不愿做哪怕指甲壳那么点事啊!以至,得意广场的满地纸屑、十八楼茶馆前的污水、东水门陋巷的垃圾没得人管,居委会要想心不烦,还得请民工来打扫。于是,许多吃低保的壮年男女越来越懒——反正没别的事可做。多少年了,义务劳动好像只是大学生和军人的事,特别在某些时日,媒体对此推波助澜,大学生、军人便成了义工、志愿者的代名词。这便让人混淆:义务劳动只是为了彰显某些时日,而尽义务者也成了特定的。为什么不能让享受低保者明白,权利与义务应该对等、享受低保就应该给社会尽相应义务这一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呢?事实上,人都是有惰性的,没有鞭策、激励和引导,懒人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重庆 张卫
反思文化生态
南海市里水镇华展造纸厂一名工人上夜班工作时,不慎将手夹在机器中,待负责看缸卷岗位的工友发现刘克超已经是360度旋转时,第一反应并不是当机立断将机器停下来,而是跑到约500米外的4号车间找到另外一名工友后,然后再一同跑到数百米外的办公大楼将厂长从睡梦中叫醒。待厂长赶至事发现场后,出事的这名工友因伤及大动脉流血过多死亡。
首先,我想说的是,这位工友的反应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所谓理性,就是在逻辑指引下的思考。正如刘克超的另一名工友阿龙所说,“请示来回的路程等花费了半小时,如果不这样做,他也许能够得到及时抢救,至少不至于丧命。”但更值得倾听的是阿龙的辩解:一天24小时机器都是在运转之中的,除非有厂长指示,谁敢擅自剪断生产线?生产停下后重新安装以及延误生产所有的一切损失谁敢负责?据说厂里300多名工人都很熟悉厂里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机器一旦运转,没有厂长批示,没有人敢私自做主剪断生产线。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判定,那名工友看着刘克超手夹在机器中360度旋转时,是在经过自己的理性判断之后,才作出选择的。在这里,他显然也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每一种选择都是有代价的。立刻关停机器,对刘克超有利;但自己违反了厂里的不成文的规矩,可能要付出代价。请示厂长,自己不必承担擅自停机所造成的后果,但刘克超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他选择了后者,问题是他为什么选择后者——刘克超得救的价值在这里显然要超过停机的损失。
这位工友作出的是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至少他认为是有利于自己的。因为他按照规定(不成文)办事了。但在这里仅考虑一个人的利己动机是不够的,他的选择本身有强烈的观念熏化影响。我们缺乏对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导致了对人本身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爱护。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确实又是深入骨髓的,以至于在看到刘克超遭受死亡威胁时,这位工友没有立刻升起救人第一的念头。这位工友如果当时停止机器了,他受厂里处罚的可能性大么?这其中,他与工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又最终导致他不敢确信停止机器后自己是不必付出代价的。他是一个打工仔,在当下的中国,打工仔的常态是处于一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弱势地位。在工厂中他们根本就没有话语权,处于权益常常受损的境况中。如果这位工友当时停机救人,事后被厂长处罚,他可能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劳资双方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无故拖欠工资的事都时有发生,根本不需要理由的,更何况这次(假设)他违反了不成文的规定,给工厂造成了损失(虽然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人命的丧失)。我要说的是,工厂里也缺少一种人性化的空气。这一点从死者老父在瓢泼大雨下被保安硬性从厂里拖出来可见一斑。一个工厂只是一个缩影,“人本位”的价值观的缺乏,影响着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选择。我还要强调阿龙的辩解,它说明当时现场换成另外的工友,他也许还是会先去请示厂长。所以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与其谴责那个不立即救人的工友,还不如去反思我们的文化生态是否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人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产物。
北京 韩福东
被我们抛弃的信用评级业
如果将信用评级业称为一个行业,那么这是个非常小的行业,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内对信用评级行业的前景普遍看好,一时间呼啦啦成立了近90家信用评级机构,到了今天,只剩下不到10家。
国际评级公司的中心业务是债券的评级。在债券市场发达的美国,每年新发行的企业债券达8000亿到9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每年1000多亿的股权融资,债券信用评级业务因此在国外评级公司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国内债券市场容量极小,近几年企业债最大不过200亿规模,评级公司的收费标准,不到千分之一。日子的艰难又带来另一个问题,虽然说每年企业债都还有一定发行规模,但发债主体都是国有大型企业或者是大型基建项目,其中不少要不是政府担保发债,就是银行担保,因而,投资者很少去关注投资事项的信用级别,对于评级结果是由哪家评级机构做出的更是完全忽略。另一方面,就连评级业业内人士也承认,国内评级机构所给的级别普遍偏高。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评级成了一种装饰品,信用评级公司赖以生存的诚信度、评级结果的公正性也被大大地打上了一个问号。
其实,评级业不仅包括债券评级,还有金融机构评级和银行贷款证评级等。但在我国以国有银行为主干的银行体系上,因为有国家信用,国内银行间的借贷不需要评级。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应该由评级机构完成的工作被当成了和游戏一样的玩意。于是,本来可以成为某种指标的信用级别就这样被我们抛弃了。
北京 钱万里
飞机和火车的跳水表演
最近,德国航空公司和铁路公司的低价竞争十分好玩。
去年“9•11”事件后,欧洲航空市场一片萧条,德国汉莎公司也惨淡经营。这时,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爱尔兰小飞行公司瑞安(Ryanair)以9.99欧元法兰克福飞往伦敦之类的让人不敢相信的低价引起了人们注意。与欧洲大航空公司的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Ryanair、EasyJet和Go三家小航空公司在欧洲中短程飞行市场上进入黄金时代。
受这些小公司的启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压力,德国的航空公司也开始准备加入廉价航班竞争行列。不久前,德国最大的旅游集团TUI宣布,从今年12月起提供中短程廉价航班,起飞地点是科隆和波恩,从那里飞往德国境内目的地的起价是10欧元,飞往欧洲其他地方(例如伦敦、巴黎、米兰等等)的起价是25欧元。
汉莎航空公司参股的“欧洲之翼”航空公司不甘示弱,立即宣布将上马一个“德国之翼”品牌,提供同样从科隆和波恩起飞的廉价航空服务,其底价甚至仅为4欧元(不过还要再加上税和机场费)。
有趣的是,天空中的价格大战让地上跑的德国铁路感到不安。“德铁”表示,在今年年底引入新价格系统时,将考虑廉价航班的竞争因素,为乘客提供很多比汉莎廉价航班更便宜的路段价格。德铁对柏林的一家报纸说,经过分析比较,如果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结成团体旅行,许多旅程乘火车要比汉莎航空公司新近引进的优惠价格系列要便宜。汉莎公司最近公布了价格改革计划,今后将提供起价仅为88欧元的德国境内汉莎航班。
不过,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都像是一场不顾后果的跳水表演。
柏林 张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