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登山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青春的激情和冲动在这些年轻的登山者眼中闪耀 (陶子 摄)
和尚与珠穆朗玛
在登山者的酒吧里,照培法师是个话题,很多登山者都告诫记者,不要过多地描述照培,会产生“误导”。照培原是一位从没登过山的和尚,今年5月他一个人登顶珠峰,随后安全返回。
记者在北京西郊见到了这位传奇的和尚,他今年28岁,身材瘦削,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居室的墙上贴着西藏登山协会颁发的《珠峰登顶证书》。照培1992年在五台山出家,4年后到北京佛学院学习,随后进入广济寺,2000年离开,开始云游天下。
2000年时我想走出去看一看,在寺庙的修行太舒服了,我要去外面体会众生疾苦。我向我姐姐和朋友借了钱,出发时终于有了两万元。我每天都走,日夜不停地走,困了就靠在车上,一年下来没怎么住过店。在新疆时我经常只买一个馕吃三天,一年中我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县。那一年的11月,我从新疆叶城进入西藏阿里,从阿里到拉萨搭大货车走了10天。路上我许了个愿,要去爬珠穆朗玛,主要目的就是“立信”——我会说到做到,以此来考验我的判断力和忍耐力,这是实现我宗教理想的第一步。
我在此前从没登过山,但我并不是蛮干。2000年云游归来后我开始准备,其实在北京,我所有对珠穆朗玛的知识只来自一本书——科莱考尔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这本书我看了半年多。所有的朋友都反对我去,但他们还是给了我最大的资助。2001年下半年我开始准备器材,到三夫户外店去买冲锋衣,他们甚至都不肯卖给我,认为会害了我。2002年1月9日我从北京出发,14日到了拉萨,朋友介绍仁青平措做我的教练,他今年59岁,曾经担任西藏登山协会副主席。我那时就住在西藏登山队的驻地,他们一天只收我5元床位费,还借给了我一顶炊事帐篷和若干设备,我一天也只吃一顿饭。我并没有做任何的体能训练,在拉萨也只是每天绕城走一圈。但我有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心态,我没有什么欲望,我只是亲近山,我不会紧张也不会恐惧。我向西藏登协申请时说:“我能爬到哪儿,爬过就行了。”另一件是我的忍耐力,2000年行脚时,在西藏我10天都没有合过眼,我可以不吃不喝走一两天的路。
3月9日我和仁青老师出发了,3月11日到了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此后一个月我在大本营接受仁青老师的登山训练,学习各种器材,爬遍了周围的一些山头。4月11日我第一次上到6500米,建立前进营,仁青老师也跟我上来了。很奇怪我一直都没有高山反应,6500米是一个坎,很多著名登山家到这里都睡不着觉。每天睡觉前,仁青老师都问我怎么样,我的感觉跟在平地差不多。直到8300米以后我才开始吸氧,后来我回北京后称了一下体重,一斤没少。这时候仁青老师相信我会成功的。4月24日我攀登到7070米建第二个营地,到28日我一共往返了7次。我没有雇佣夏尔巴人,都是自己背。开始我不知道,夏尔巴人最多也只能背40斤,而我第一次就背了这么多,把我累坏了,我后来就减到20斤左右。后来,很多登山者一直把我当作夏尔巴人。有一次我掉进了冰缝,但我马上就用冰爪制动,一点点爬
了出来。我开始只有两顶帐篷,在大本营又买了一顶,花了430美元。5月15日我上到7900米,这一段路我雇了一个夏尔巴人向上运了3个氧气罐,16日上到8300米的突击营,给了他800元人民币。我的运气很好,接下来是一个晴天,17日凌晨3点我出发了,12点一刻登顶。有人问我在山上是什么感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看照片上我还是傻呆呆的,也没什么喜悦,只是我做到了。我注重过程,我的心灵很安宁。这次登山一共花了12万元,国外平均一个人要花上3~5万美元,如果现在银行里我有5万元存款的话,我会把希夏邦马和卓奥友都爬下来。
张为:登山就是郊游得厉害一点
12年前一个夏天的黎明,清晨5点,一个男孩儿穿着短裤,骑着自行车驶出清华,他的目的地是200公里外的塘沽开发区。10点钟时候他会找个地方休息,躲过午后的骄阳,会吃自己带的馒头,5分钱一个的馒头,喝清华园带来的凉白开,买不起公路边一角钱一斤的西瓜。这个男孩叫张为,清华登山队的创始人,他现在已经36岁,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
我要去和开发区加利加制鞋公司的老板谈赞助,那年我和北大同学组织去登玉珠峰。我没有一个公章,没爬过雪山、没有一张与雪山的合影。凭着酷暑中北京到塘洁的三个自行车来回,感动对方,得到7500元和10双鞋子。为了拉到赞助把很多事说成‘首次’,这是件很难堪的事。我的背包是中国登山队的一位队员送的地质包,他几年后登梅里雪山时死了,那个包连钢骨都没有。我们没有钱,火车票都没买几张,男生藏在座位底下,女孩子背着药箱在车厢间窜来窜去逃票。现在人爬长城都带GAS罐,我们当时没有,带的是汽油。在大雨里走了12天我们才进了山。记得我和北大登山队的拉加才仁登上山顶,他说你看那是什么,山顶上有一座铁塔,那是50年代军队上来时修造测量高度的航标塔。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说,直到30岁以后回到清华登山队,说在我们登上玉珠峰多少年以前,就有战士背着水泥、石头上去过。从玉珠峰下来,我们倒在沼泽地上走不动,是12个淘金人开着拖拉机把我们送到大本营去的。我们回来后像英雄一样,但照片上没有救了我们的淘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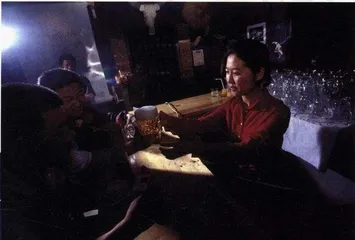
登山爱好者们在交流中很容易就凝聚在一起 (陶子 摄)
陈杰:一个人的登山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具体的登山者仅仅是无意中完成了一个集体的梦想。2002年,登山史还不到两年的陈杰,登上海拔为8201米的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我是民间个人登顶8000米以上山峰的第一人,但这绝对不是故意的。”陈杰说,“我认为攀登之于人,是一种本能,但我现在非常矛盾,不知道该不该放弃。”
这位以“本营”之名更为人所知的登山者,是某国家部委的公务员。
我每个白天上着有规律的班,为了训练,晚上11点多加班回来,还要跑到1点多钟。最麻烦的是,我是家里的老单儿,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在父亲过世后,更为要紧。其次,就是要占用大量工作精力,同事们只知道我喜欢爬爬山,不知道我其实那么玩命。更要命的是,收入不高,为了登山只好省吃俭用,并熬夜写稿挣点外快。常常买的是装备是“尾单”和“甩货”,就是老外订成千上万件货,多给一个零头的材料,国内工厂留下来自己加工,廉价买出的高山装备。比如甚至可以花600到700元,买到正品为5600元的一件冲锋衣。
我三次进藏,连布达拉宫都没去过,而是三次登山。三次登山用的是三次假一一献血假,国庆假,登卓奥友时用的是探亲假。我以为,登山者是用肚子来登山的,于是他平日在家,自己做酥油茶,自制炒面,自己和在里头,做成“糌粑”,训练着吃。平日熬夜登山,打破生活节律锻炼;进行耐寒训练,常年用凉水擦身,洗凉水澡,每天早上喝凉水。登山时候,因为经费紧张,吃得不好。伙食费预算只有1500元,决算是1700多元。曾在前进大本营吃了十天以面条就咸菜,土豆加白菜叶子为主的伙食,因为从不挑食,而且能吃糌粑,否则体力堪忧。但我在山上能吃能睡,这是一个优点。
登著名雪山时,容易遇到来自各国的登山者。在那次登卓奥友峰时,就遇到了世界顶级的几位登山家。一是正带领商业登山队的职业高山向导罗赛尔,他曾经12小时登上希夏邦马峰,90次登过阿尔卑斯山的主峰博朗峰。他们的装备非常好,甚至备有加莫夫棺材(便携式高压氧舱)。另一个高手是妇女,她叫克里斯汀,是疯狂山峰队的CEO.也即《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主人公费希尔的继任者。她登过五大洲的最高蜂。我还亲眼目睹了一位前天还在一起喝酒、唱韩国民歌《倒垃圾》的韩国登山队队长,因为体力不支而死在众人面前。这件事对我心理震撼非常之大,更有神秘意味的是,在他闭眼片刻之内,五六群乌鸦突然出现,低低地盘旋着,让我觉得生命真是很脆弱。
不久之后,即开始登山,登卓奥友顶后下撤,我体力下降得很厉害。罗赛尔等三个结组小队比我们先下山了。不到一小时,陪我攀登的藏队的小其米很快下了山。我在最后自己走。当时我的包里有一盘30米的结组绳,一个空氧气瓶,有一个灌满水的1.5升的不锈钢保温壶。还有8块高山食品,一些备用电池,两个快挂,连上接近6斤的包,总重大约20~25斤,越走越沉。我感到迷迷糊糊而劳累,突出的感觉是特别困乏,特别想睡觉。在8100米那个硬雪壳或者说是粒雪冰地带,冰爪只能踩上白印。当时我有点糊涂,差点滑坠。我反复提醒自己,动作不能变形,一次动作的变形就会产生严重后果。默念‘翻身压镐翘腿’的六字决,终于通过。
国内有个诗人写过一首名叫《大雁塔》的诗,大意是我们上了那里能干什么,不过是登到高处,看了看,又陆续下来了。在那个开阔无比并略显凄凉的顶峰平台上,我来回踱了四十多分钟,那时有短暂的诗情画意,但是很快又被下山的忧郁取代,因为只有活着走下山来才算真的成功。一个著名的登山家写道:“在登山中,最让人激动的,不是登顶的瞬间,而是下山后看见第一片绿色的瞬间”。
登山爱好者们在交流中很容易就凝聚在一起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登山就像其他任何一件事一样普通,就是运动量大一点的郊游。登山是件私人的事,是个人追求自由的过程;而现在的登山太像体育运动了!我不喜欢“山登绝顶我为峰”的英雄气,我们怎么可能是山峰呢,我们不过是山上的一朵小花。以前我每天跑10公里,周末跑30公里,绕着操场跑75圈,吃不起馒头,就把米饭捏成团带着,以为天下我最苦。错了!一次我们走到雅鲁藏布江边,一队修路的武警在休息,我取出相机给一位战士照相,没想到他站起来追着要打我,后来被他的班长劝住。班长很客气地对我说:“他实在是太累了,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在受苦。”
1991年攀登格拉丹东,是一个旅店老板送我们进去的,和我们一起走了12天,他有两个藏族孩子。出来后,道班的白段长问我们能不能给这位老板200元钱的误工费,我们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怎么那么低级。但当时我给他钱,他死活不要。我今年36岁,这些年一直在反思。我尊重每一个生命。北大登山队是一支优秀的队伍,如果我们批评北大,不如先批评自己,批评社会。
我更欣赏登山家麦什拉尔的态度:“登山只是我每天做的事情,我登上山顶,并不挥舞意大利的国旗,而是像一位农妇,爬上自家屋顶晒玉米,轻轻地挥舞手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