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个物理学家在现实中国的作用
作者:苗炜(文 / 苗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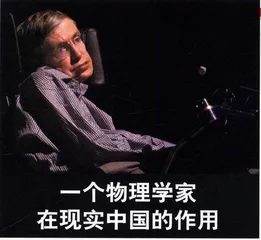
(陈柏 摄)
托尼·罗思曼在《曼迪逊大街的物理学家》中说,一个物理学家在现实世界中是没什么用的。这句话显然带有玩世不恭的味道,罗思曼的作用就是写科普文章,并在哈佛大学教授广义相对论,但在理论物理研究领域,他可能真的没什么用。
霍金来中国,让我们见识了一下物理学家在现实世界的号召力。他是一个人类智力的偶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担当着战胜疾病、不屈从于命运的斗士的形象。1985年,霍金在芝加哥为公众演讲时,坐在轮椅上的退伍越战士兵向他挥动拳头叫——你是对的。
与霍金同时在中国访问的纳什则没有受到太多的追捧,他的故事因《美丽心灵》这部电影被人了解。这两个人的出现为北京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做出了铺垫,在这个大会上,会有更多智慧的头脑。遗憾的是,另一位偶像级人物,英国数学家约翰·怀尔斯(Andrew John Wiles)并不打算来参加会议,他因证明费马大定理在上一次(1998)的柏林“国际数学大会”上获得了特别奖。
怀尔斯与霍金相比,好处在于他在证明的东西大家都明白——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X^2+Y^2=Z^2,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勾股定理,它有正整数的解(3,4,5)。1630年左右,法国数学家费马在一本古希腊的《算术》书的空白中写道:“任何两个正整数的3次方和不可能等于另一个整数的3次方,……一般来说,任何两个正整数的N次方之和不可能等于另一个正整数的N次方,只要N是大于2的整数。”
费马说他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证明,只是这地方写不下,然而,怀尔斯的证明过程却占据了1995年5月《数学纪事》的一整本(纳什获诺贝尔奖的论文据说倒只有两页)。1993年7月,美国数学研究会在旧金山向公众介绍费马大定理的研究情况,5美元的门票被炒到25美元,虽然这远比一张球票便宜,但还是说明了“公众对文化与科学的珍视”。
同样道理,霍金在中国所作关于“膜”或关于“弦”的演讲也表明了公众对科学的尊重与珍视,继之而来的“反思”也顺理成章——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薄弱,博士毕业从事研究工作也就挣2000块钱,好学生去学电子、计算机和金融去了。
《纽约时报》科学版副总编辑丹尼斯·奥弗比说:“1957年前苏联令人惊异地发射了火箭,这成为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决定性的时刻。自此以后,科学与技术成了国家的头等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全问题。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最好的和最聪明的学生都被吸引到科学研究上来——而10年后,最聪明的学生都上了法学院,20年后,都上了商学院。”
美苏争霸可以当成是科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加以大书特书,莫斯科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拓朴学在苏联的发展、兰德公司的对策论等等。事实上,当我们拥有自己的偶像陈景润时,除了获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前途设计之外,我们也升腾了一些民族自豪感。在即将开始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数学家能不能获得1小时演讲时间也多少和民族自豪感有关(以往,吴文俊这样的中国数学家只得到过45分钟演讲的邀请)。陈省身教授提出的“21世纪数学大国”也是个动人的号召,青年人献身科学研究是一个美丽的场景。假想一下,1963年,21岁的霍金懒洋洋地坐在剑桥大学的屋子里,录音机里放着瓦格纳的乐曲,四周堆放着许多科幻小说。那个霍金远比现在这个发出金属声音的霍金更可爱。
在中国能不能产生霍金这样的科学家不关我事,在我们对一种智力活动表示尊重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不懂的玄虚前承认自己的愚钝。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恩曼的演讲比霍金的演讲更适合于中国听众,他说:“我认识许多人,他们的智力正在遭受侮辱。……认为普通人是愚钝的这一观点是十分危险的,即使真的是这样,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对人们的智力进行愚弄和侮辱。”他说,如果从技术应用的角度说,现在是一个科学时代,但是,“如果你理解的科学时代是指在艺术、文学、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相互间的理解方面,科学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我们的时代绝不是一个科学的时代”。
按照费恩曼的逻辑,如果我们这里诞生了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他并不能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或科学的社会里。如果我们承认官僚制度或司法制度也算是科学的发明,那么,我们平凡的智力受到侮辱的感觉越少,创造性的活动更得到鼓励,我们的生活才算幸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