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鸥的第一宗诉辩交易
作者:李菁(文 / 李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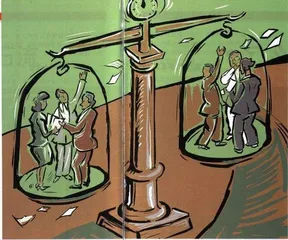
(插图:象牙黑工作室)
“你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你是第一个吃毒癞蛤蟆的人。”——自从国内第一起“诉辩交易”案被媒体广泛关注后,这桩“交易”的首倡者,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吉鸥便被各种议论包围着,赞成者有之,但不乏许多尖锐的批评。
吉鸥强调,自己的“第一”只是实践意义上的“第一”:“其实在理论界,(关于诉辩交易)早就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探索了。”
引发国内“诉辩交易”第一案的,是一桩简单的伤害案。2000年12月18日,黑龙江绥芬河市的孟广虎因车辆争路与吊车司机王玉杰发生争执。孟广虎几个朋友闻讯而来,双方都大打出手,混战中,王玉杰被打成重伤,经医院诊断为小腿骨折、脾脏破裂。案发后,除孟广虎本人外,其他6名同案犯罪嫌疑人均潜逃外地。公安机关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抓捕,仍一无所获。2002年3月20日,孟广虎以“故意伤害罪”被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但这桩看似简单的伤害案在审理过程中又显现出几分“特殊性”。“从司法鉴定来看,致使王玉杰小腿骨折、脾脏破裂的主要凶器是铁棍,而孟广虎只承认打了王两拳。由于场面混乱,王玉杰也无法指证究竟是谁打的。”孟广虎的辩护律师丁云品向记者介绍。由于本案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丁律师认为认定由孟广虎承担具体的重伤责任“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控方则认为,此案因其他犯罪嫌疑人在逃而无法判定被害人重伤后果具体是何人所为,证据收集也困难重重。但被告人孟广虎找人行凶造成被害人王玉杰重伤,理应由他承担全部责任。双方意见严重分歧。
吉鸥是两三年前在黑龙江大学学习期间第一次听说“诉辩交易”这个名词的,“我当时就特别感兴趣”,“去年是高法提出‘改革年’,提倡实行审判方式的改革”,“正好碰上了这件适用于诉辩交易的这种案子”。不过,吉鸥也坦承,“推广过程中不是进行得很顺利,各种议论不绝于耳,还是上级法院帮助我们下了决心”。
无意中成了中国“第一例”,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院长周宝成当时的感觉是“千万别有什么闪失”,为此,“省院领导也亲临指导”。2002年4月11日,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对控辩双方达成的诉辩交易予以确认——由孟广虎赔偿被害人王玉杰经济损失人民币4万元。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广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当时,孟广虎已在看守所羁押15个月,而本是举债买车经营的农民王玉杰,也陷入生活无着看病无钱的境地。所以,“交易”在这两位当事人那里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这个结果对当事双方都是‘双赢’的。”法院院长周宝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但他也谨慎地强调“诉辩交易”的确“很复杂,不是所有的案子拿起来就能用的”。孟广虎的辩护律师丁云品也用“非常满意”和“非常同意”来形容原、被告方的态度。他认为,可以在国内许多类似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子上尝试“诉辩交易”,“既避免浪费许多人力物力,也避免了对当事人超期羁押”。
但目前与首倡者吉鸥的境遇一样,周宝成也陷入一片“褒贬不一”的议论中,甚至“说孬的更多”,但周宝成强调“我们是司法实践,不是作秀”。他说普通老百姓的反应一般是一提“交易”,就有各种不好的联想。理论界的讨论目前还在热热闹闹地进行,但吉鸥、周宝成、丁云品坚持认为,“现在基层有大量类似案子,被害人长期得不到补偿,在这种情况下,诉辩交易不失为一种有效率又相对公正的解决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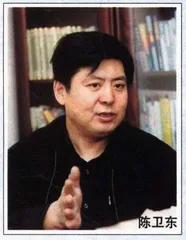
给辩护律师一点权利——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东
电话采访时,陈卫东正在贵阳参加关于“诉辩交易”的研讨会。作为组织者之一,陈卫东说正是这起全国“诉辩交易”第一案引起的热烈关注,使他们快速反应发起了这场研讨会。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学界和司法界对“诉辩交易”的争论主要在哪些方面?
陈卫东:讨论焦点集中在诉辩交易在中国是否适用?如果借鉴这种制度,我们的程序应该如何设计?诉辩交易最大的优点是高效,它减少了诉讼环节、降低诉讼成本,但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刑事审判能否引用商业运作?这是不是对公正原则的挑战?为了换取有罪答辩,检察机关可能有意拔高指控程度,以迫使被告达成交易。事件之后,高检有一个精神,认为诉辩交易可以研究,可以探讨,但暂不能用。准确地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诉辩交易的明确法律依据。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司法土壤还不适宜这种“交易”,甚至有人说这会导致更多的权钱交易或黑箱操作,一定程度上扩大负面效应。\
陈卫东:这也是一部分人的担心,但我认为花钱买罪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控方是不会同辩方交易的。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也不会同意有罪答辩。即使在交易的情况下,无论哪一方面的让步,都要得到另一方的认可;而且交易不是单独的、私下的交易,我们有法院的审查监督。
三联生活周刊:从法律意义上说,诉辩交易是控方与被告辩护律师的“交易”,那么被害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
陈卫东:这正是美国诉辩交易的缺陷而我们强调的题。黑龙江这个案子的社会效果之所以好,就是因为辩交易得到了被害人的同意,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保障。所以如果我们引用这种制度,在程序设计上一定要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体现。
三联生活周刊:复杂的司法程序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诉辩交易的确体现了它的效率性,但是否因为追求效率性而忽视了公正性?
陈卫东:我对此有一些不同看法。西方有句谚语: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如果大量案件长期积压,得不到处理,两方面利益都得不到保障,何谈“公正”?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诉辩交易有其积极性。绝对的公正追求不到,相对的公正也是一种公正。
三联生活周刊:诉辩交易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而中国则属于大陆法系,不同的司法理念是否会形成冲突?
陈卫东:英美法系是对抗式的诉辩模式,注重被告人利益,而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奉行的是职权主追诉模式。但留心一下你会发现,从90年代起,我们的司法改革有些向英美法系学习的地方,如“证据交换”、证据制度等。当然,我们的整个司法理念、司法环境不一样,就像有人打个比方一样,“如果单独引进一部机器的零件,这架机器无法运转良好”。我的总体看法是我们不会把诉辩交易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我们应当改进的是它的诉讼规则所体现出的诉讼理念、诉讼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专门研究诉讼法的学者,您个人对诉辩交易在中国的发展持什么看法?
陈卫东:我们的司法实践是以公正和效率为目标的。在有限的司法资源和不断增长的案件的矛盾条件下,我认为引进这种司法制度,把实践中存在的黑市交易变成看得见的交易是有益的。因为诉辩交易可以强化辩、审、控各项职能。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目前日益萎缩的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遏制司法权的无限膨胀,减少公诉风险。现行的司法制度下,法官既定罪又量刑,诉辩交易实际上也是分解了一部分权力给控辩律师。
资讯
陈卫东介绍“诉辩交易”
诉辩交易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美国面临经济迅速发展,积案越来越多;司法机关力量有限,难以应付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同时,陪审团判罪时无罪的比例较高,检察机关常常面临着诉讼风险,于是将民事中的合同契约精神引用于刑事诉讼当中。
诉辩交易是以控方降低或减少指控,以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它包含两方面内容:一,关于定罪的交易。控方可能降格指控,减少指控。比如著名的“李文和案”正是通过诉辩交易解决的。控方原起诉59项罪名,李文和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后被指控一项——将核武机密下载至某部不合安全规定的电脑里。二、关于量刑的交易——如果被告认罪,控方提出较轻的量刑。孟广虎案则属于典型的此类诉辩交易。
目前,美国有89%的案件是通过控辩交易处理,只有少量案件才提交法院审判。诉辩交易的基本要求是,被告人必须出于自愿而非强迫。法院对诉辩交易的结果进行审查,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这种审查基本上是表面化的。辩诉交易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伴随着极大的争议,但它又在争议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目前,诉辩交易不仅是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英国、意大利、德国都有类似的法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