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06)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布丁 包包 蘑菇 张矣)
我们聊点什么
布丁
我到X城之前,就听到这里地下色情泛滥。但第一个晚上就被这里的营销方式震惊,那天晚上吃完饭,发现车门上被塞进了一张卡片,上面印着个漂亮姑娘,下面有联系电话,广告词是“另一种心灵体验”。回到酒店,我就迫不及待的打电话给她们。
接电话的是个妇女,听声音在30岁以上,她说她们那里都是女大学生或者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服务方式和别家决不相同。我问:“有什么不同?”她说我们这里只陪客人聊天,决不陪客人上床。而且我们聊天的层次很高,小姐有权利选择服务对象,如果她不想和你聊下去了,她可以转身就走。
这套说辞有点新鲜,我说:“你给我找一个来吧?”她问:“你要什么水平的?”“当然是高水平的。”“那你是什么学历?”我有点不好意思,同时有些诧异,不明白这样一个软色情的聊天和学历有什么关系,但还是诚实地说我只有本科学历,上大学学的是中国文学。她沉吟片刻,说我给你找一个擅长中文、层次适中的姑娘吧。
半个小时之后,有人敲门,来的姑娘自称丽丽。坐下来寒暄几句,她问:“我们从什么说起呢?”我说:“我只会瞎说,一般你们从什么说起呢?”她白了我一眼说:“我最近都是从李欧梵说起的,你看过李欧梵的新书吗?”我一下惊呆了,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没想到陪聊业务已经到达这样的高度,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没看过他的新书,但我看了他在《书城》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书城》杂志,我知道,那号称是中国的《纽约客》。”我连忙顺着她的话头说:“你还看《纽约客》吗?或者董鼎山?”丽丽回答:“我不能跟你聊董鼎山和美国人的东西,那是外文部的业务。我是中文部的,但我可以和你聊聊董桥。”这说法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问:“外文部和中文部有什么区分呀?”丽丽一下激动起来:“她们就凭着多知道几个外国人名,每小时比我们多挣50块钱呢。其实他们聊的有什么呀,罗兰·巴特、乔姆斯基、哈耶克、萨义德,这些东西我也会聊呀。”
我替她打抱不平,说:“怪不得把你算是层次中间的,原来能聊外国人的东西才算高级的,这是什么规矩?”丽丽随声附和。接下来我不免好奇地问:“你们算是中间的,那什么算是低一级的呢?”丽丽说:“聊电影的算低一级的呀。我们一小时是100块,聊罗兰·巴特是150块,电影是50块。其实分得还不够科学,我觉得聊贾樟柯应该贵点儿,聊美国电影就应该便宜。”
诸位看官,到这里我要承认,以上文字是瞎写的,是剽窃伍迪·艾伦的小说《门莎的娼妓》,伍迪·艾伦在那个小说里让妓女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语言,并且将许多美国文学评论家绕在里面。我在1000字的篇幅之内编不出故事来,作为一个低能儿,我只好把它弄成一坨恶毒的狗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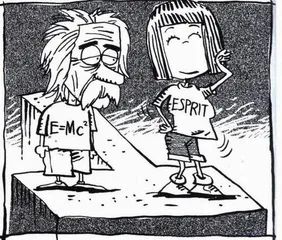
与才智无关
包包 图 谢峰
苏在读书的时候,时髦是出了名的。那真是一种眼巴巴的艳羡,并不是谁都会有一个母亲嫁给一个香港人,然后在香港定居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没有什么品牌意识。每每夸起苏的衣衫漂亮时,苏便对懵懂的我们提这个叫ESPRIT的名字。当时我翻过字典,查出ESPRIT有个让人神往的意思叫“才智”。苏的成绩在那所重点中学糟得有点不堪入目,所以这个法语单词的意思让人记忆犹新,多少带点揶揄味道。
仿佛跟苏过不去,大家都考上了大学,苏落榜。苏身上才有的“才智”,却在那一年的夏天,在城市的闹市区,夸张地开了一个很大的门市。也许惟一可以令苏释怀的是,300多元钱一件的衬衣或400多元钱一件的毛衣,绝非我们这些穷学生能买得起。所以,三年后的暑假,和老同学在家里聊天,无意中有人讲起,最近苏所在的银行赈灾捐款捐物,苏捐了一旅行包八成新的ESPRIT时,好几个女孩(包括我在内)都大惊小怪、大呼小叫了起来。天哪,连林青霞都跑出来口口声声地称“我只穿ESPRIT”,苏为什么偏偏这时候反其道而行之呢?
后来,大家也就很自然地毕业、工作、赚一点钱、买一两件ESPRIT过过瘾。年少时候被苏撩起的欲望,在年纪稍长时终于如愿以偿。慢慢地,身边的服饰色彩越来越斑斓,选择越来越多样,ESPRIT曾有过的独树一帜也终未幸免,被流行大浪逐渐吞没。于是,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曾有过的热烈向往。
今年7月底,苏来杭州参加为期一周的业务培训。那天,我和她坐在杭州一家购物中心的星巴克喝咖啡,东聊西聊就聊到了ESPRIT。苏说,这个牌子早在1996年我就不碰了。我感到落伍的尴尬(要知道,1998年我才有第一件:ESPRIT的T恤),便问为什么,喝完咖啡,苏说,你跟我来。然后两人绕购物中心的二楼一周。绕完,苏说,就在刚刚这一圈,她看到了穿在女孩子身上的。ESPRIT衬衫三件、T恤两件和背包一个,外加标有“SALE”字样的塑料购物袋若干。
望着不远处对折打得热火朝天的ESPRIT专柜和身旁如今一身正装打扮的苏,我无端地觉得这样的反差很搞笑。
十年之后,翻开字典,ESPRIT,字面上的意思仍是一样。但,穿或不穿以ESPRIT命名的服装,与才智无关。
香水
蘑菇 图 谢峰
在玩“大富翁”的时候,出于某种恶毒心理,我最喜欢看着钱夫人开车被炸弹炸到,她娇呼一声“哦,我的夏奈儿”,绞了手哭哭啼啼地去医院。
我不害怕可可·夏奈尔的断言:“不用香水的女子没有未来”(其实那是她喜欢的诗人Paul Valery的诗句)。但我喜欢另一位时装大师路易·费罗的诗句:“香水是为转瞬即逝雕建庙宇。”
世界上约有40万种香味,人类能感觉到的气味约有10万种,远远大于人类可以辨别的颜色。《追忆似水年华》序章里关于“小马德兰点心”的著名段落形容道:“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在我物质并不丰富的童年里,带着铁匣气味的万紫千红油脂、粉质单薄的宝贝霜、开着轻柔白色花朵气味的紫罗兰,油腻甜香的金刚钻发蜡、檀香皂,混合着杏仁粉和滑石粉的香粉,带着强烈酒精味道的麝香花露水,构成了我根深蒂固的气味记忆中关于女性世界的一切。
我长大后,开始喜欢四处看香水,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巨大无比的抽屉,里面装满了各种小小的香水瓶,我每天翻弄它们,让玻璃瓶子发出炒田螺一样的“哗啦啦”声响。我喜欢在有阳光的天气拉上窗帘,迎了光,把香水喷向空中,轻浅收敛地呼吸,看像微尘颗粒一样的香水纷纷坠下,仿佛就此能对香气多些形象的把握,感受它的体积、颜色和质感——因为气味本身是很难用语言保存、重现的。
我有一瓶香水,是一个美国公司在巴黎的盗版基地生产的。瓶子上“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写着“本香水possession与Calvin Klein的注册商标产品obsession没有任何关系”。我把香水当玩意儿买回家,玩味着它的名字,obsession一一迷惑,possession——拥有,我想不仅仅是对香水,对世间一切,贪婪的我们所渴望的,都是从迷惑到拥有吧。
前两天,又一个不务正业的朋友要去法国,我问她想去学什么,她想了想半真半假地说:“你觉得,我去学调制香水怎么样?”朋友告诉我,想到当调香师也许是中了小说的毒——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里写着:“年老色衰,米亚有好手艺足以养活。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

胡天胡地爱
张矣
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同寝室的七个兄弟在喝高了之后相约各讲一个同窗四年中最秘密的故事。其余五人讲了什么我都忘了,原因是老六的故事太让我惊心动魄了。他说大三时咱们的同班同学××有一次约他出去玩,他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不料那女生竟直接拉他去了火车站,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在一个荒郊野外下了车,然后又租一辆自行车到了一片类似原始森林的地方。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那女生带去的一张床帷上,我们的老六经受了有生以来最具诱惑力的挑战。然而可惜的是,他虽然有了人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但在最后关头,他不得不偃旗息鼓。我们一致认为这不是我们老六没本事,而是那女生浪漫过了头。
受此刺激,我在心底暗暗发誓,将来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姑且称他为老八吧,一定要在一个别人都料想不到的地方来一次。
卫慧的禁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幕是倪可和他的日耳曼情人在洗手间里匆匆了事。泰坦尼克号上穷小子杰克和贵族女孩露丝在一辆马车里完成了他们身与心的最充分交融,从此我的老八便不能与大海、轮船、马车、卫生间之类的场所沾边了,否则难免抄袭与模仿之争。一部《EYES WIDE SHUT》就谋杀了我不少好去处。按照轮船的思路,我曾想到过飞机,可《太空城》中的最后一幕就是詹姆斯·邦德在驾驶舱内和他的邦德女郎翻云覆雨。抱怨之余,却又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创造力。八卦杂志曾爆出好莱坞影星在摄像机前假戏真做的新闻。让我的老八在摄影棚献出他宝贵的第一次,这是打死我也不会干的,因为那感觉不像是写小说,而像是在拍A片。
此外还有哪些地方呢?《本能》里道格拉斯用一只皮包挡住了莎朗·斯通伸向他敏感部位的手,也挡住了电梯间人们的目光。好在他们的动作只是挑逗,如果想在此基础上延展的话,电梯间也还有值得挖掘的潜力。但没过两天,我又看到法国AXE香水的广告片。受一点残存香味的蛊惑,那位漂亮的小秘竟然按停电梯,收拾起了一位上门推销的小瘪三。这种创意我是想象不出来的。
池莉的小说《水与火的缠绵》,书中写道,因为没有房子,曾芒芒只有揣着结婚证书和他的爱人同志到外面解决生理问题,他们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长江大桥下的观江平台。那地方我太熟悉了,那临江大道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大街啊!想想当年那一排倚着栏杆用长风衣都挡不住的节奏单一但也不失谐调的舞蹈动作,我不由得为我那再也不会出世的老八长叹一声,世界如此之大,为何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