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车和它烧掉的90%行政开支
作者:巫昂(文 / 巫昂 秦翠莉)

底数
在国企和政府机关内部,“车改”进程,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公共财政博士焦建国说:“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一份反腐报告中称,全国共有2.1万辆超标车,占全部公务车的1%。也就可以算出,当时公务车总数在200万辆以上,还不包括那些没有清查出来的。”
而2000年第一季度,在北京试点的是六家国企:城建集团、北辰集团、中建一局四公司、兆维集团、燕莎商城和北京国际经济合作公司等。据北京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办公室所做的调研报告,这六家企业一年的公务车用车费用共计1.3亿元。公务车据该调研报告称,养一辆桑塔纳公务车的年费用为7.5万元,一辆奥迪则高达14万元。
据拥有3.69万名员工的北京城建集团公司纪委提供的资料,该集团系统现有各类非生产性公务车1249辆,其中半数为小轿车。仅2000年,养这些车就花去了4339.78万元,包括养路费285.6万元、车船税38.17万元、车辆保险费392.6万元、汽油费1021.46万元、车辆修理费928.6万元、事故损失费29.76万元、人工费(司机)1578.95万元、其他费用支出64.73万元。如果加上新车购置和外租车的费用,这个消费额则上升为更加惊人的5669.18万元,而集团公司2000年的利润总额为7000万元,两个数字比例为0.81:1。“这种用车的权利并不是一种货币化的制度,”服务于某国家部委的陈令(化名)说,“而仅仅是一种待遇,就像信用额度,达到一定级别的公务员可以拥有其使用期限。”
改革
他们实行的三种车改模式里,首先是取消领导的固定汽车配置,其次是实行交通费用补贴,如燕莎商城领导层交通补贴分为1000元/月和400元/月,前者为自购车补贴,后者为其他情况补贴。最受非议的可能是第三种模式,即精减车辆公开出售处理,如中建一局四公司将原有企业公务用车出售73辆,回收资金330万元,平均每辆的出售价约为4.5万元。城建集团机关出售30辆,回收资金176.3万元,平均每辆约为5.7万元。燕莎商城出售39辆,回收资金122.42万元,平均每辆约为3.1万元。这是由集团的租赁公司将所有的原公务配车进行了公开拍卖,谁出价高就归谁所有。
亚汽资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分析师张豫向记者讲述了公务车的档次之于职务的门道:“在这里边,排汽量2.0,车价25万元是道坎儿,这以下,是属于处一级干部的公务用车标准,所以现在很多处级官员的用车都是1.8升排气量、20万上下。局级官员多为2.0排气量、价格在30到35万元之间。而部级官员则可享受3.0排气量、40到50万元奥迪车的待遇。现在常用的公务车,除了奥迪外,还有桑塔纳、帕萨特、别克、本田雅阁等品牌,基本上是国产车。每年公务车销售总数约为十几万辆,占目前汽车市场的10%左右。”
有关统计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中高档公务轿车产销量同比增长200%。与此同时,普通轿车(2升排气量以下)产销量却下降了25%。
另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不管是汽车经销商还是售后维修公司,都喜欢跟公务车的采购与维修者打交道,公务车的购买一般集中在年底,因为每年都有各单位该项预算项目,过期作废。他告诉记者:“在车价、维修配件价格与服务质量方面,他们一般都无所谓,有时候,这些商家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回扣,或者用一般的配件维修,却开进口昂贵配件的发票。”
北京市监察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职务消费中的车辆消费占单位行政经费的绝大部分,约为90%左右。而焦建国掌握的数字是,这笔费用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在很多县级政府中,这笔开支比人头费(比如工资)还要高,当然,这依旧是保守估计。
预算
财政部财务会计研究室研究员李明认为:“与车相关的开支就国企的财务制度而言,分两块,一块是新车购置费,买新车是作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其中可能只有一小部分列入当年的折旧费里,作为企业成本的组成。买车属于资本性支出,它造成企业银行存款减少(或者欠账),但是资产增加。而汽车的保养费、司机费则归入企业的管理费用上。政府的固定资本通常是不计折旧的,没有收入和费用的对比,政府每年本年度10月份做明年的财政预算,到明年的12月份做决算。但政府的钱,通常是混在一起用的。”
“仅从公务车消费的问题上看,这还是中国特有的家计财政和国家财政不分的体现。”焦建国说,“现在的国家财政问题,不在于缺钱,而在于缺规矩。从预算开始,就没有细化的,把人头费、车辆费在预算上搞清楚。现在财政部代表政府每年向全国人大提供的预算数字,很多都是粗化数字。而职务消费在本质上就是家计财政,改革目的,应该是官员个人消费必须跟公共开支分开。在车改多年后的1998年,国家公车消费保守估算仍有2000多亿元,而当年的国防开支为934亿元。另外一个数字是1995年的,当年的公车消费也是2000亿元,而公款吃喝为1000亿元,相比年度财政10000亿左右的收入,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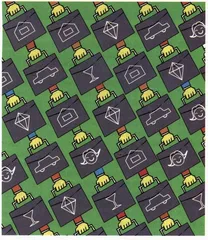
矛盾
对于出于解决公务车职务消费而采取的“第三条”买车政策,焦建国开诚布公地说:“从公共决策的制定角度而言,这就是一个利益问题,当面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时,政府用自己的刀削了自己的刀把,在改到自己的头上时,未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而自己选择一种非透明化、非程序化,有利于资产流向‘特权集团’的政策,是非常荒唐的。这跟以前的房改如出一辙。”
他还认为,单纯去谈车改或者职务消费货币化,没有意思,其深层意义,还是要和政府改革的框架联系起来。政府是一切规则的制定者,自己立法自己执行自己解释,这本身就很难说彻底代表了公共意志。公务车的不当消费及无立法的再分配,正好是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力合一的表现。正好合乎了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公共选择”。
回到六企业车改的例子上,本着“没有花掉的钱即挣到的钱”的原则,车改成效在调研报告上是如下表述的:“中建一局四公司车改在当年(即2000年)节约费用200万元,城建集团机关节约182万元,燕莎商城节约238万元,北京国际经济合作公司节约45.9万元,兆维集团节约30.32万元,共节约1221.22万元……车改后企业车辆费用普遍比上年度节约10%至40%。”报告中间,它还颇为温情地说,“按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计算,可以支持下岗职工42700人。”
但“车改后集团的私车占到80%左右。”城建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配车的级别是固定的,一般是奥迪100,现在变成货币化后,开的车成了私人爱好,什么车都有,有的比原来还提高了档次。”
在沉默中得利的是少数人,没有人追问,那些转化成私家车的公务车,折旧后到底其价几何。也就是说在一次似乎合理的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中,到底在有意无意中流失了多少国有资产。“这种改革的成本太昂贵了,而官员和企业经营者更为勤快地买更昂贵的车,也为腐败中的洗钱提供了一个借口。”焦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