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乡是否天堂依旧
作者:李伟(文 / 李伟 巫昂)

扎龙渔业资源的衰减十分明显,国营渔厂早就破产了,村民打上的鱼越来越小
火后扎龙
距扎龙28公里外的齐齐哈尔,很多人对去年的大火记忆犹新,他们都能看到远方的黑烟。“火从8月烧到10月,此起彼伏,开始时是烧苇子,但后来你会发现泥土也在着火。实际上不是土在烧,是火烧光了地面的苇子,钻到地下烧芦根。”仓福杰说,整个扎龙就像一块巨大的蜂窝煤。冬天火灭下去后,春天扎龙又着了一把。李晓民告诉记者,实际上火并没有完全止息,而是转入了地下。由于芦苇是多年生植物,地下根系相当发达,当地人称“草母子”。而且往年的死芦苇沉降后形成了一个厚实的泥炭层,深达一米都没有土壤,冬天或进入地下“焖了起来”,“这就好像东北老乡烧的土灶,火在灶膛里燃,烟囱伸到户外,如果外面风大,烟抽得快,灶火就燃的旺;扎龙春天的火就是被大风‘抽’起来的。”李晓民说,扎龙几乎小火年年有,因为当地老百姓要烧荒,往往火烧到水面就停了,但去年整个沼泽都快干了。在此前1996年春的大火就曾燃遍扎龙50%的土地。芦苇有两种生长方式,一种是种子萌发,另一种是靠地下根茎发出新芽;由于根茎被烧毁,记者在保护区看到的芦苇十分稀疏低矮。
为湿地解渴的惟一办法只有调水了。
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1979年成立,目前人工饲养了60多只鹤
“如果没有今年春天调入3亿立方米的救命水,这里可能还是赤地千里。”王建成对记者说,他是齐齐哈尔水务局水利设计院院长,“现在有了水,过火的大部分地区生态当年可以恢复,还是生机盎然;特别严重的话,就多花两三年时间。”王告诉记者,省里和水利部门开了几次协调会,决定从嫩江中部引水,“当时我们测算,需要至少4亿立方米的水才能维持平衡,保证30厘米高的水面。”整个工程由“中部引嫩管理处承担”,修建了400余公里的明渠。最终费用3家分摊,黑龙江省林业厅100万元,齐齐哈尔市政府70万元,大庆市政府130万元,总共300万元,调水3亿立方米,1分钱1吨水。由于嫩江流域用水矛盾同样尖锐,3亿立方米已经是一个极限。
黑龙江自然科学院博士倪红伟曾长期考察湿地植物,接受采访时,他也很难估计这3亿立方米能支撑多久;参与调水的王建成肯定地认为,“每年至少补充两亿立方米水,湿地才可勉强维持。”而明年怎么个补法,还未成定论。
干旱的乌裕尔河
“旱,这两年太旱了”,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李长有向记者解释着火的原因,“去年几乎没下过一场雨,自1998年大洪水以来,几乎年年如此。”李长有在保护区工作了13年,几乎每年都要为水发愁。去年从保护区管理局到唐土岗子的船道都已干涸,步行即可通过。
发源于小兴安岭西麓的乌裕尔河和双阳河都是无尾河,行至扎龙自行消失,其中乌裕尔河是扎龙湿地的主要水源。“在达斡尔语中,乌裕尔的意思是‘不确定的河流’,这条河的年际流量实在是差别太大。”王建成说,“1961年径流量18.95亿立方米,1977年只有0.56亿;1998年大水,扎龙湿地为它调蓄了近20亿立方米的洪水,但这两年这条河基本快断流了。”记者从齐齐哈尔气象部门拿到的资料显示,松嫩湿地平均年降水量为416.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801.6毫米,扎龙的蒸发量经常达到1500毫米。春旱频率达到了70%,其中大旱占20%,加上相对不旱年份的短期旱象,真正是“十年九春旱”。夏季由于降水变化大,时空分布不适宜,干旱率也达30%,春夏连旱的频率约20%。而且一个大旱年之后,往往2~3个降水较正常的年分,渴水的局面也缓不上来,必须遇上降水量很多的年份才能缓解。而年降水量超过500毫米的机率只有19%,平均5年才有一个雨水丰沛的年份。
全球变暖加剧了扎龙的干旱:自1988年以来该地区已经出现了10个暖冬,冬季平均气温比40年前高了近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下的天数仅相当于40年前的1/5。“按照水文记录,扎龙每24~26年为一周期,丰水期和少水期轮回交替;自1995年扎龙已经进入少水期。”根据王建成的统计,干旱将在本世纪初一直持续。
干旱的同时,人类也在和湿地抢水。这一地区的主要供水工程有:新嫩江运河、东升水库、连环湖输水干渠、龙虎泡引水工程,1994年在双阳河上游的依龙镇富饶乡之间修建了大型水库,库容2.98亿立方米,拦截双阳河来水;主要是为了下游输水和农田灌溉。大庆油田位于保护区东部,每年开采油井都需要大水量回灌地下;油田的引嫩工程就横穿保护区,减少了进入沼泽地的水源量。乌裕尔河上游水位受东升水库和赵三亮子闸门控制,春旱时水库库门关闭,沼泽地内水位低。“很长时期以来,东北的水利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发,只调不蓄。”王建成说,“现在嫩江上游投资700万元兴建了尼尔基水库,就要考虑更大范围内水的综合利用。”
湿地的面积在急剧减少。扎龙村的关老汉告诉记者,去年旱得最厉害时要走百八十里才能见到水面。鹤被称为湿地之神,是“环境的气压计”;扎龙保护区有3种沼泽:漂伐苔草沼泽、芦苇沼泽和苔草沼泽,其中芦苇沼泽和苔草沼泽是鹤最喜欢的生态环境,丹顶鹤的繁殖区多为芦苇沼泽。然而芦苇沼泽的面积缩小得相当快,20世纪60年代的面积是17.33万公顷,70年代后只有8万公顷,李晓民指着地图说,现在大多数野生鹤大都压缩在大庆的林甸县内。鹤具有很强的领地性,一对丹顶鹤的领地是2~3平方公里,最大的有5平方公里。芦苇沼泽再小下去的话,则很难容得下目前300余只野生丹顶鹤。
同时水位降低直接影响到了鱼的产量。沼泽地内的鱼类大部分无法越冬,1995冬到1996年春季,保护区内扎龙湖的冰层几乎到达水底,水面解冻后,湖边飘满了死鱼。“鹤虽然是杂食动物,但繁殖期的鹤,必须要有鱼吃。”李晓民说。
污染的水质
鹤类的另一大威胁来自水质污染。
保护区管理局曾以家鸭为对象进行了毒理试验,水面放养的家鸭每个个体心、肝、脾、肾、胰均发生不同程度的病变,共性特点是心脏褪色、肝脏出血、脾胆增大、肾增生、脑充血。保护区内的野鸭和鱼的解剖也发现了不同程度的病变。李晓民说,目前由于鹤类是国家保护动物,还无法直接进行解剖研究,但推测污染物肯定侵入了鹤类机体。在保护局的检测中,东汉潭、连二泡子、龙湖、扎龙湖、赵凯、卧牛岗、葫芦形、老马场的水质均为5类,主要污染物是高锰酸钾和总磷,局部为砷、汞和挥发性酚;其中高锰酸钾超标2.06~41.68倍,含磷量超标0.25~30.25倍,总氮含量最大超标15.3倍。

左图:一个村民一上午可以割两麻袋“白梢子”,打一斤草籽,卖两块钱

中图:仓福杰说,以前家谱是不给别人看的,只有除夕晚上,全家人吃过 饭洗了手,拿出来拜一拜

右图:扎龙湿地是人和鹤的共同生存空间
扎龙保护区横跨铁峰区、富裕县、林甸县、泰康县、泰来县、杜尔伯特盟等6区县,界内多是农区和牧区。王建成坦率地告诉记者,即使如此,区内的水质仍只有4~5类;“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湿地的水属于静水体,易产生污染;此外两岸的工农业影响很大,有些排污都是直排的。二类水质才是正常的。”乌裕尔河沿岸及附近的克东、克山、拜泉、依安、富裕、林甸,分布着制糖、酿造、食品、纺织、造纸、机械、化工、医药、建筑等为主的工厂,现有企业541个;克山、克东、依安县的工业废水直接通过自然水沟排入乌裕尔河,富裕、林甸两县排入沼泽地。一年的总污水量910亿立方米,相当于最高来水量的50倍,仅齐齐哈尔和富拉尔基的二十多座大型工厂日排污水9300吨以上。其次是农业污染,区内灌溉面积有4万公顷,一年用化肥10200吨,用农药90吨,还有大量的杀虫剂、除秀剂流入保护区。
“虽然这是一块保护区,但人类开发的足迹已经遍布区内。”倪红伟说,很多大工程,比如301国道、大庆引水渠将湿地切割成一块块岛屿,水体难以互通,动物往来不畅。
“都统”的后代们
丹顶鹤一般将巢筑在人迹罕至的芦苇深处,“巢址周围的苇丛高度都在120厘米以上,丹顶鹤、白枕鹤的巢址周围30米内必有小水泡,丹顶鹤对水的要求更高,多在10米左右。”李晓民说,鹤是一种机警的动物,尤其在繁殖期,它们常常为了躲避人的干扰而在沼泽中游荡,甚至推迟繁殖期。“每年村里人割苇子,就像剃光头,鹤找个筑巢的地方都不容易,只能栖息在稀疏幸存的‘哑巴苇子’里。有人还在繁殖区内搭窝棚、捕鱼、放牧,这些活动对蓑羽鹤的影响最大,这可能是目前蓑羽鹤在本区繁殖很少的主要原因之一。”1981年、1984年两次对丹顶鹤进行航空调查,观测丹顶鹤的集中繁殖区域,1984年向北移动了,主要原因就是南部沼泽被开发为农田。“保护区内目前还有29000多居民,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建区之前他们就居住在那里。”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李长有说。目前区内人口只许迁出不许迁入,还鼓励农民进城,但1979年保护区成立后,人口数量仍增长了36.88%。
湿地边缘的扎龙村有600多户人家,2000多人口,村内仓、徐、关三大姓都是满族人。仓福杰拿出了一只塑料袋,里面是一个黄布包,打开黄布包是一张叠了数层的羊皮纸;由于时间太久,纸色发黄而且印着一圈圈水渍,折叠处已破损,被贴上透明胶带——这就是他们仓家的家谱。“俺们当初都是皇上底下的人,出了不少官,而现在是一代比一代熊了。”仓的母亲说。家谱用满文和汉文书写,名字便记录了他们的官职,三品、五品或是披甲。仓氏的祖先是库仑德,向下四五代后是仓福杰的爷爷——成和,再往下就没有记载了,仓福杰这一支人丁最兴旺。家谱边的说明文字是由满文书写,虽然周围几个乡镇居住的都是满族人,但没人看得懂这些文字。村民们说,他们的先人多是两三百年前迁来戍边的。东北三省为满族的发祥地;清初设八名副都统统管全境,齐齐哈尔即是一军事重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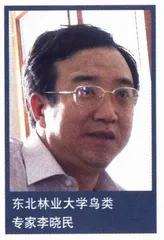
东北林业大学鸟类专家李晓民
不知从何时起,都统们的后代定居在这片苇塘边。根据保护区的统计,解放前扎龙村初只有400人,80年代就达到了1500多人,土木克解放前无人居住,80年代达到了500多人。他们至今还维持着很多满族人的风俗,房子一定要有西窗,不吃狗肉。而扎龙、赵凯、土木可、唐土岗屯都是鹤类的集中栖息繁殖区。记者在保护区里遇见了关老汉一家,他们正在割“白梢子”(一种顶端长满草籽的野草),近处的“白梢子”已经被割光了,他们只有走得更远。关老汉告诉记者,有人收购“白梢子”的草籽,去西北种草,他们每个人一上午可以打一斤,挣两块钱。
扎龙的居民们是以草为生的。
扎龙的土质多为盐碱地,可以长草但长不好粮食;扎龙村居民每人只有6分地,种点玉米。由于是夏天,很多家庭还只吃两顿饭。“这里的农业还是靠天吃饭,没有灌溉,生长期又短,去年我们种了点黄豆,因为霜下得早,都完了。”仓福杰的二哥仓慧杰说。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割苇子”。苇塘平时并不承包,只是到初冬,村里按人口平均分配收割区,一般一个人的面积是10米宽两公里长的长方形。最常用的工具是“推刀”,像一台手推车,底端固定一把很长的镰刀。仓慧杰说,每年冬天割苇子就像一场劳动竞赛,整个村子都空了,因为你收不完自己的地,别人就会来割你的。仓慧杰的老婆是邻县的人,不适应这种重体力劳动,每年他都会雇一个人。苇子由村里统一销售,卖给造纸厂或者编织芦席,一个人一般收入1000多元,这笔钱占他们全年收入的一多半,扎龙村每人的年收入也就在3000元左右,大部分的人都住着土坯房,屋顶盖着厚厚的芦苇。仓慧杰还养了一头奶牛,每天能挤70斤奶,一斤卖四毛五钱,但除去料钱,也所剩不多。
谁养活了谁
捕鱼是村民们的另一项营生,一般白天下网,夜里两三点钟起床收鱼。网有两种,一种是地笼,由窗纱制成,圈在湖沼中,由于网眼细密,鱼苗都不放过,这种网又称“绝户网”。另一种网叫花篮,圆筒状,网眼略大一些,鱼从两头进入卡在中间出不来。这两种捕捞方式都是灭绝式的。“一方面,生在沼泽中的鱼体型都比较小,下大网捞不到鱼。”李长有分析说,“另一方面,出于生存压力,村屯的老百姓不论大小能捕就捕了。”在扎龙附近,小鲫鱼都能卖到5元一斤。
仓福杰帮记者提出了几个“花篮”,里面的几条鲫鱼最大的也不过手掌的2/3。扎龙渔业资源的衰退从70年代就开始了。齐齐哈尔扎龙鱼场1963年产鱼量801吨,1980年只生产20吨,下降了26.7倍,杜盟1963年鱼产量是4949吨,1980年只有750吨,下降了6.6倍;林甸县1973年产量6868吨,1979年只有300吨,下降了2.9倍。李晓民分析,现在的鱼类产量与10年前相比下降了5~10倍,鹤类的食物链十分脆弱。
倪红伟向记者分析扎龙生态问题时,认为保护区的体制是一个先天的缺陷,“保护区没有土地使用权,它不能限制老百姓的开荒和渔猎”。土地使用权是地方政府权力,但保护区并不是地方政府。李长友告诉记者,齐齐哈尔市政府每年拨给他们30多万元,自己门票能挣50万元,林业部会视项目给几十万元,总共收入在100多万元。事实上,即使拥有土地开发权,也很难有足够的财力让老百姓迁出或转产,而保护区管理局目前也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些临时工的职位。
采访中,扎龙村的居民说他们从来不打鹤,祖上以前还养鹤,就像养狗一样,会跟着人走。仓福杰站在苇塘边,感觉今年的苇子不错,“如果不是保护鹤,上面就不会放水保湿地,没了水就没了苇子,俺们就得饿死”。
中国鹤的数量和现状
1996年ICF(国际鹤类基金会)报告全球丹顶鹤数量为1700~1900只,其中中国有700~800只,占将近一半。1997年冬,人们在江苏省盐城自然保护区数到了1020只丹顶鹤,为丹顶鹤越冬的最高记录。而此前,80年代前期,黑龙江省自然资源研究所等单位对黑龙江夏季丹顶鹤种群数量进行了地面和航空调查,当时查明黑龙江共有丹顶鹤502只,其中乌裕尔河流域有193只。1984年的黑龙江、辽宁和吉林省的调查发现中国繁殖地丹顶鹤数量为676只。分布区主要为辽宁盘锦、吉林向海、莫莫格、黑龙江省的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1988年到1989年美国、中国、日本等调查世界丹顶鹤为1145只。
丹顶鹤繁殖于中国东北及内蒙古,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部、东南部沿海越冬。近似繁殖地区的鹤类还有白枕鹤,其越冬地主要集中在都阳湖。1985年见1165只,1986年见有2143只,1994年报道世界共有白枕鹤6000只,其中3500~4000只在中国。1988~1989国际联合调查表明世界白枕鹤为4658只,国际水禽研究总局1989年1月公布调查数据为:中国6966只,日本1416只,似乎估计有些过高。1992年,世界鹤类讨论会估算全世界有白枕鹤5000只,笼养300只,JIM HARRIS1996年报道鄱阳湖有白枕鹤3000只,1996年ICF报告全球共有白枕鹤数量为4900到5300只。
白鹤不在中国繁殖,越冬地主要在江西省鄱阳湖、湖南洞庭湖和升金湖也有少量过冬,白鹤数量估计为:鄱阳湖1985年见到1482只,1986年见到1784只,1988年全世界估计有白鹤1800只。1988~1989年美国、中国、伊朗等联合调查,白鹤为2689~2692只。同年,国际水禽和湿地研究总局公布的数字是3331只,1992年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召开的世界鹤类讨论会估计白鹤数量为2500~3000只,JIM HARRIS1996年报道鄱阳湖有2877只,占全世界总量的99%,1996年ICF报告全球白鹤数量为2900~3000只。
白头鹤在中国的繁殖记录过去记载为乌苏里江流域和海拉尔附近,但以后再未发现。直到1991年发现黑龙江省通北林业局有一处繁殖地,见到巢和卵,数童为2到3对,后来又在内蒙古发现52只夏季集群,未见到幼鸟。白头鹤的越冬地主要在长江下游,1996年ICF报告全球共有白头鹤估量为9400~9600只之间,鹤类研究专家马逸清估计中国有1000~1500只。
蓑羽鹤和灰鹤由于其非濒危并分布较广,故研究较少,中国蓑羽鹤的繁殖地在新疆北部、甘肃北部、内蒙古、东北北部。1996年ICF报告全球蓑羽鹤数量为200000~240000只。中国灰鹤的繁殖地为新疆天山、东北西北部及黑龙江省扎龙自然保护区,越冬地在四川及华南地区,1996年ICF报告世界有灰鹤超过10万只,马逸清报告有9000~12000只。
黑颈鹤繁殖地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越冬地在云贵高原中部,黑颈鹤几乎全部分布在中国,1987年以前数量无准确记录,1983年境内越冬的黑颈鹤为900只,1988年到1998年,美国、中国、印度等联合调查得出黑颈鹤数量为705只,但1992年卡尔加里鹤类讨论会上估量为5000到6000只,1996年ICF报告全球黑颈鹤5600到6000只,其中中国有3600~4600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