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融真假出局
作者:朱文轶(文 / 朱文轶)

中国民营汽车业是否能继续成长?
(罗健 摄)
仰融的“布局”与“入局”
5月底,华晨开始悬念迭起。一方面中华轿车成功获批上市,与宝马合作项目的最终落实也日渐明朗;另一方面,市场不断传出仰融“被中国政府调查,并被限制出境”的消息。接下来,华晨股价开始连番跳水。所有关注华晨的人都意识到,仰融和他的华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6月19日,在香港上市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CBA)宣布,其创办人兼主席仰融不再担任主席一职,由副董事长吴小安接替。吴小安在当天出席一个基金分析员会议时表示:“由于仰融不能照顾股东利益,与大股东中国教育基金意见不合,董事会已经解除了其主席职务。”然而就在此前6个小时,吴小安仍在向媒体澄清传言“公司已向仰融求证,仰融并未因违规事件被调查”。基金会副秘书长贺增强向记者透露,仰融遭解职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仰融在重大问题上与基金会意见不一;二是仰融一些经营决策的失误导致股东对其信任度下降;三是仰融自己的健康原因。表面化的解释回避了更实质性的问题,6小时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任何局外人不得而知。
无论华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以及这个麻烦到底有多大,仰融十几年前开始演绎的民营汽车与资本的故事显然已经到了高潮。李安定对记者说,弄清华晨是民营还是国有,“可能一切疑惑都会迎刃而解”。
记者了解到,在6月初由摩根斯坦利安排的一次恳谈会上,仰融曾向多位香港基金经理表示,华晨股权并非国家所有,只是为了符合美国上市要求,暂由在百慕大注册成立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代管,管理层将收购华晨股权。仰融力推管理层收购的举措与他不久前在公开场合的强硬措辞相吻合:“原始股本上,国家没有给一分钱,基金会没有给一分钱,任何部门也没有给我一分钱,任何时候也没有国家给我一分钱的凭据。”很明显,澄清悬而不决的华晨产权成了仰融最迫切的一步棋。
至于向来对产权问题避而不谈的仰融在此时急于出牌的原因,一位华晨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华晨运作的三大汽车项目都即将上马,仰融殚精竭虑的十年几乎全都是为此作铺垫”,能否真正从玩资本过渡到玩产业,“仰融的确到了一个槛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背景的仰融从将华晨汽车控股沈阳金客并赴美上市这第一步棋开始,将一系列石破天惊的资本运作玩得天衣无缝并构架了只有他才能亲自开启的“华晨迷宫”,而他和他的华晨也入了自己布的这场局:仰融没有以私人控股的形式去上市,这让华晨的产权归属在启动华晨系大厦的融资中起到决定作用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上发生了争议。这意味着,一旦持有华晨近40%股权的基金会全部转让给辽宁省,华晨将被收归国有。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尽管在中小国有企业纷纷由私人承包经营的大环境里,民营企业收归国有尚未有先例,但在华晨三大汽车项目均已酝酿成熟,且其中中华轿车与宝马轿车落户沈阳的情况下,辽宁省利用这个机会实际掌握华晨运作,这个想法不论是从地方利益还是从产业布局考虑都不算过分。”
苦心造就的华晨是否继续属于仰融?李安定告诉记者,仰融曾向他提及自己要在健康的时候退休,并且要留下一个完整而健康的企业。现在看来,能否跨过这个“槛”成了仰融能否化解“迷局”的关键:困难超过了他原先的想象。
仰融“出局”之谜
从一系列公开的事实看,结果有些顺理成章:仰融自设迷局最后“作茧自缚”,华晨被辽宁和宁波两个地方政府瓜分,对华晨三大项目失去影响力的仰融似乎已经彻底出局,与他亲手缔造的华晨系渐行渐远。
而注意到华晨内部变动的人表示,“一切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采访中,有人向记者提到与仰融卸职几乎同时发生的是华晨系下另一家上市公司申华控股的人事调整。5月31日,申华控股第五届董事会第37次临时会议上,董事苏强、吴小安、洪星、何涛未出席会议。这是仰融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前的最后一次调兵遣将。知情者把这次人事变更比喻为“‘华晨迷宫’的一次重新挪位”,并据此推测,“仰融很可能在布一场新局使自己摆脱产权困境”。
6月6日,仰融一系列新的排兵布阵在华晨公告上得以体现:“因工作变动,免去苏强总裁职务,由汤淇(原申华副总裁)接任”,苏强和一批旧部将被调往沈阳CBA。同日,新的两个人物薛维海与秦荣华粉墨登场。申华控股发出了“关于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的出资人的补充公告”,该公告称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台湾敏孚企业有限公司出资人秦荣华。第二天,正国投向申华董事会提出增加董事的提案,宁波正运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薛维海补充为申华控股公司董事。
据一家媒体报道,“秦荣华与仰融有很深的私交”,观察者分析,熟读《孙子兵法》的仰融用的是“暗渡陈仓”的办法将华晨人事重心往宁波的申华控股转移。
华晨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大格局在更早的时候已经确立——就是在宁波落户的发动机项目。据介绍,宁波发动机项目设计能力是年产30万台,华晨汽车所控制的两大项目中华轿车与宝马轿车的配套发动机均由宁波提供,“早在去年上半年,宁波的征地拆迁就已经悄然进行”。采访过仰融的记者李岷回忆说,仰融曾向他阐述过自己的汽车产业理念,“在中国搞汽车,得发动机者得天下”,而选择宁波,因为它“背倚上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成本优势”。
一位曾与仰融打过交道的人士推测其用心:有意抛掉沈阳华晨汽车(CBA)旧部,而将宁波申华控股培植成为他的新嫡系,“这样,当仰融退居幕后的动作完成的同时,他凭借宁波发动机项目重新控制华晨的过程也就完成了”。“即便CBA真正收归沈阳,仰融仍然保存了‘仰融华晨’的实力。”
而在普遍的产权问题面前,中国民营汽车业是否能继续生长?仰融的消失,说明谜团还未到拨云见日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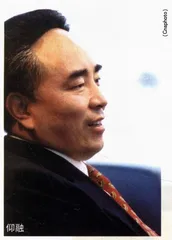
仰融
(Cnsphoto)
谁来接管中国民营汽车业?
面临困境的不惟仰融。
在民营汽车制造业风头稍逊仰融的李书福更早就遇到了麻烦。与仰融不同的是,吉利集团祸起萧墙。最初依靠集合民间游资以及与各种资本合作而完成企业扩张、打造巨额资本的“吉利”,在“吉利”新车即将获国家审批通过,吉利帝国一路高歌凯进时,李书福与李国顺兄弟间的官司打上了法庭。据介绍,吉利产业是李书福的,工商营业登记也是李书福的,而吉利下面的各个分厂由像李国顺之类的个体资本实际投资,当吉利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许多个体资本开始纷纷举旗,试图把自己的产权合法化,再和总当家的李书福分家算钱。
汽车是公认的高度资金密集型产业,巨额资本是其血脉。民营汽车业起步首先要解决的都是资金链问题。仰融用的是金融市场上的资本运作;李书福用的则是集合民间资本的方式,二者侧重不同,却在汽车产业的膨胀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曾帮助民营汽车崛起于政策挤压时期的融资手段,都因为遗留其中的“产权模糊”的历史问题,成为民营汽车做大后的新难点。
有人评价说,在这个意义上,强悍的仰融与李书福们也异常脆弱。而与目前国有汽车业的大重组相比,华晨、吉利等的处境更为艰难而微妙:资产如何处置,权利如何分配,究竟是个人还是国家能最终整合民营汽车业?与仰融是否出局的疑团相比,对中国大汽车业而言,这些悬念更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