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我爱香格里拉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菲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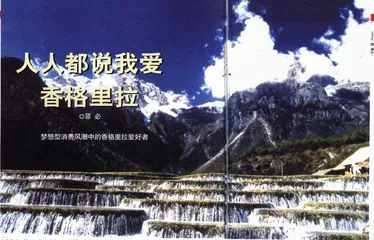
玉龙雪山、丽江、东巴文化……为香格里拉注入了更多美妙的元素
1922年5月9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特约撰稿人约瑟夫•洛克第一次看见玉龙雪山。这里丰富无比的植物让探险家、科学家洛克欣喜若狂,在他那部著名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里尽是各种植物名称、海拔高度和气候的考察数据,读起来枯燥无味,这就是最初洛克眼里的丽江:一个巨大的植物学标本。但最终,他被另一个丽江所征服,那是东巴民族心中的丽江:古老,诗意,遍布神灵。洛克后来对采集植物学标本感到厌倦,他着迷地崇拜起东巴文化,编写《纳西族英语百科辞典》,收集研究东巴经。当时他已经感受到东巴文化正面临灭绝危险。1949年8月洛克不得不离开他居住了27年的丽江,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将在来年视局势的发展,如果一切正常,将返回丽江去完成我的工作。与其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我宁愿在玉龙雪山的杜鹃花丛中死去。”洛克最后在夏威夷的一张钢丝床上去世。
2000年赵野和王超计划拍一部以洛克为原型的电影,春节过后赵野从成都开车出发,第一次来到了香格里拉。两年中,赵野几乎每隔两个月就动身去香格里拉,他描述:“在北京呆上两个月就很烦,到那儿人就变得开心简单。丽江是自然环境与世俗生活的完美结合,而四五月的中甸,美得像个天堂。”赵野的电影计划现在并没有结果,因为他需要的投资过于庞大。不断地去香格里拉采风收集资料,对香格里拉越来越了解和喜欢,他原本的电影计划反倒搁置起来。
赵野由此转向另一个计划。在6月20日的北京凯宾斯基发布会上,他宣布关于香格里拉的文化工程正在进行,一群艺术工作者希望围绕香格里拉的人文和地域创造其相关文化产品。工程包括在香格里拉建造一座影像博物馆,拍摄电视剧、记录片、电影,举办音乐会、全球性香格里拉论坛。在前期的200万人民币投资之后,一张音乐专辑《最后的香格里拉》——小柯创作、王子璇演唱,一部30分钟的音乐电影《布农铃》,一本肖全摄影的概念画册已经完成。
“玩得越大越好,玩总会有一个结果。”另一位策划人黄燎原乐观地评论这个工程。在被要求比较《最后的香格里拉》与《阿姐鼓》时——两者都是虚无缥缈的女声演绎相对遥远的地域,黄燎原特别强调前者的非商业化意图,“说白了吧,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商业利益。现在的资金可以充分支撑,商业考虑少了,创作自由度就大了”。“这两种音乐相差还是很大,我感觉一种是在玩音乐,它跟音乐的距离感更大一些。而小柯做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自然的成分更多。当然朱哲琴从嗓音到演绎技巧都更好,她有一种直达的东西。”
关于这个文化工程的另一个消息是不愿露面的投资方将继续投资800万至1000万人民币,“这件事比较舒服的就是一切都比较自然,功利的目的比较小,起码做到现在我们不用为它能否挣钱发愁,可以让它自然摆渡。随心想到一些事情,就能够干一些事情——这事儿好像是神话。”黄燎原说他们几乎是抱着理想主义者的态度。
在发布会上,香格里拉(中甸县)政府代表列举香格里拉地理资源的种种数据,还作出一个不寻常的决定:请歌手王子璇担任香格里拉的形象大使——从未有过个人充当一个地方的形象大使,这堪称中国首次。
三九广告公司在6月18日也发布了8月将在丽江举办“雪山音乐节”的消息,据说这将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音乐节——连续48小时不间断的演出被主办方宣称是一场伍德斯托克式的音乐节,地点在丽江玉龙雪山下的野外草甸。如果可行,雪山音乐节将每年举办一次。
著名的真人秀电视节目《生存者》的中国版本《走进香格里拉》去年在全国范围内播出,只有10根火柴和10天食物的18名志愿者在海拔4000多米的香格里拉生活30天。导演陈强对为什么选择香格里拉的回答是:“我们想借助这里来表现都市与荒原、精神与物质、个体与虚拟空间群体、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关系。香格里拉更虚拟化,能很好地实现我们的想法。”
赵野则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求的就是自己有感觉、能够发挥、有经济效益的工作。“我们对外宣称是寻梦,寻找自己的兴趣,实际上,香格里拉集中了各方面的有利因素——自然环境、文化民俗、有说法、有文化底蕴、有洛克。”赵野说的香格里拉,是大香格里拉构想:从西藏南部、四川西部到云南西北部,阿坝、迪庆、德钦、稻城、大理、丽江都包括进来。

丽江——这个美丽的小镇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
香格里拉这个美妙的名称正在带来更多的财富:仅中甸去年的游客就超过了120万,丽江游客数目则在200万以上。在云南,一种叫“香格里拉•藏秘”的青稞干红和干白葡萄酒裹挟着神秘的气息上市,据说是根据当年法国传教士的秘方酿制。而一种叫“香格里拉”的香烟正在由昆明卷烟厂配制。
随之而来则是旅游与保护的冲突。《纽约时报》报道说,这里同样面临着其他地区失败了的挑战——如何发展才能保护他们的资源与文化。问题是如果发展不能顺利进行,保护的动力也非常脆弱。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办事处高级顾问和德华说:“如果不能清楚地向人们展示我们的项目可以从哪些方面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就无法成功地保护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
迪庆曾成功地拒绝了中日联合登山队第四次攀登梅里雪山,德钦也拒绝了将道路修到明永冰川冰舌处的建议,拒绝了投资者在冰川上修建索道的设想,使进入这些地区只能依靠当地马帮。但对于以文化之名进行的工程,香格里拉几乎是雀跃地欢迎。三九广告公司总监郦辉“狡猾”地说:“雪山音乐节的举办地实际是在玉龙雪山保护区和丽江开发区之间的空地,一边看得到雪山,另一边是高尔夫球场——我们不想被人们指着鼻子骂。”赵野评价香格里拉工程则不无世故的意味,“我们只能说,先让大家认识这个地方,然后再苍白地保护它。这里有两个层面:当地政府希望打旅游牌,在吸引足够的人气之后,当城市人民要表述他们的某种关怀,就由当地政府再解决”。
诗人于坚曾写下:“从根本上来说,世界之所谓进步,就是要回到那个只存在于过去的叫做伊甸园的地方。当洛克如此想的时候,他已经背叛了他到玉龙雪山来的初衷,被改造成了一位诗人。不仅如此,荒,还有它更伟大的力量。但现在,我不能肯定这种力量是否依然存在……在丽江那昔日使人把握并且坚信永恒的玉龙雪山的‘荒’中,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建造高尔夫球场。”
事实上,甚至连这样的感慨也显得苍白无力。21世纪的人们不缺乏物质,但在神话和传奇方面极度贫乏。举一个梦想新型消费的逻辑例子:目前在丹麦,市场上50%的鸡蛋都由放养鸡所产。消费者不喜欢让鸡呆在狭小的笼子里,而希望它们能自由接触到天空和大地。消费者需要的是一种“回归产品”,他们希望鸡蛋用古老的方式生产出来,这意味着鸡蛋越来越贵,而消费者情愿为鸡蛋背后的故事多付15%~20%的价格,他们宁可多掏腰包也要得到关于动物伦理主义、田园风情和美好往昔的故事。这是经典的梦想社会逻辑。
人们越来越期待能够打动心灵的消费,而非理性的消费。在这样的心理下,我们对故事的需求目前难以得到满足,即使在最宏伟的自然丰碑前,戏剧成分也开始慢慢地蒸发掉。据说每年攀登上珠峰的有80多人,其中不乏一些尾随的自费旅游者。藏族人民坚持说珠峰是圣地,拥有净化灵魂的神奇力量,而现在这个故事正随着永恒雪域里任意丢弃的空瓶子、塑料包装纸而走向幻灭。我们即将用完真实的童话,所以必须用梦幻编织出新故事。
关于香格里拉的另一个消息是英国人花费了3年时间拍了一部记录片《云之南》,在英国播出颇为轰动,许多人在媒体讨论着“剧情”该如何发展。丽江的外国浪子越来越多了。
在消费梦想的时代,你怎么能不是一个香格里拉爱好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