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比粽子还冤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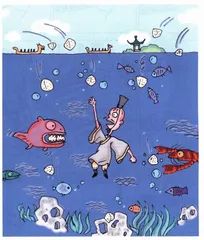
端午的来历,最早起缘于上古三代的“兰浴”。按照《大戴礼记·夏小正》的解释,“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目的是“此日蓄采众药,以解除毒气”。古人相信,五月五日这一天阳气至极,万物茂盛,正是“毒气”最旺的日子,故端午之为节尚得服药,多少有些“排毒养颜”的概念。
然而,朴素的“天人感应”后来还是被复杂的“人人感应”所取代。端午传闻一:伍子胥是辅佐吴王阖闾完成霸业的功臣,阖闾死后,伍子胥逐渐失宠,新吴王夫差听信太宰的谗言,赐剑令他自尽,还把他的尸体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扔到钱塘江里。于是江浙一带的百姓于每年五日初五祭祀之。
传闻二,见蔡邕《琴操》:“介子绥割其腓股以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惊悟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传闻三,见《会稽典录》:“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上。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沂,涛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
不难发现,不管被纪念者是男是女,是民是官,这些人几乎拥有一个共同的死因,一个字:冤!当然,端午民俗中最传播最广、有教育意义、最能和粽子发生直接关系的,属于“纪念屈原”说。
与伍子胥、介子绥和曹娥这三位男女“冤友”相比,屈原不算是死得最冤。尽管伍子胥、介子绥及屈原三人皆因“投人与回报”的高度不对称而死,但是就“投入”而言,屈原为楚国所作的贡献,远不及伍子胥之于吴、介子绥之于晋。不过在我看来,死得最冤的,既不是上述三个男人,也不是小女人曹娥,而是曹娥的老爸。作为一名汉代的“神职人员”,曹父因“涛迎波神溺死”,冤就冤在这个传说中的“波神”不是别人,正是“四大端午冤魂”之一的伍子胥。“波神”这个光荣称号,是江浙民众在伍子胥的尸体被扔到钱塘江里之后赠送给他的。
不管怎么说,这四个人都是死于五月初五(曹娥之父溺于此日,曹娥本人则于七日后投江),然而,惟有屈原一人的死直接或间接地为我们创造或维持了吃粽子的习俗。端午食粽之“纪念屈原说”,始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回日: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绿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
屈原死于公元前278年的农历五月初五,这一点争议不大。但是,关于“蛟龙所惮”的说法,有人是持怀疑态度的。如闻一多教授生前就坚持认为,包括粽子和龙舟在内的种种端午礼俗,实际上与“持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有关。也就是说,沉入江中的粽子很可能只是单纯地为了拜祭蛟龙,而不是作为深水炸弹去“恐吓”那些对屈原不利的蛟龙或者转移它们的注意力的。
端午食粽之“纪念屈原说”虽然不尽可信,但就连“纪念屈原说”本身,也在经年累月的民间语文中发生了难以避免的变异。小时候听大人说,把粽子扔到水里,是为了怕屈原的尸体被“鱼”吃了。“蛟龙”变成了鱼虾,“惮蛟龙”改做了“喂鱼虾”。然而不管是“惮龙”还是“喂鱼”,目的都是为了祭祀,为了招魂。其实,按照屈原时代的楚文化传统,屈原本人在临死之前就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两篇招魂的文字材料,即《招魂》和《大招》。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发现,招魂工作所需要用到的素材十分繁复,而且堪称奢侈。仅吃的就包括五谷杂粮,猪狗龟鸡,飞禽走兽,美酒佳酿。此外,负责引诱“魂兮归来”的还包括十六位“朱唇皓齿,丰肉微骨,小腰瘦颈,姣丽施只,体变娟只,美目腼只,善留客只”的美女,供尊贵的游魂“态所便只”。
自认真研读过《楚辞》之后,每一次吃粽子的时候,我都会为了我们碗里的那一小堆相比之下显得寒酸之至的叶子包米而不好意思。不过,我仍然认为用往水里扔粽子的方法替溺毙者招魂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品味,至少,比我们今天忙着在水里打捞什么“黑匣子”要风雅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