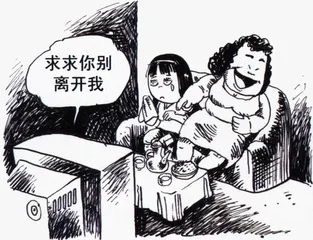生活圆桌(19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何冬梅 马宏敏 布丁 夏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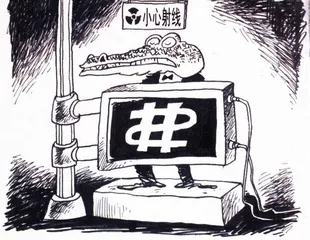
大鳄大腕与大款
何冬梅 图 谢峰
中国新兴的财富阶层花起钱来绝对不比老牌欧洲贵族手软。他们通常扎堆住在一座座打着贵族标志,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豪宅里。豪宅的lorby是他们表演的舞台,一幕幕场景是他们有心或无心导演的人生戏剧片段。这里有名震世界、酷到多一句话都不肯讲的导演大腕;也有令全亚洲女人疯狂的男明星,只是她们不知他是个gay;有钱多得不知要怎样“造”的男女民间大款;也有跺跺脚便会让地产界金融界企业界哆嗦的大鳄。更有无数星光闪烁的女明星。
他们相遇时都故作清高假装不识彼此,私下里却极其热衷从保洁或保安那里探听对方的隐私,要么就相互揭露各自未起家时的落魄或者积累财富时的利欲熏心与不择手段。相识的人表面上惺惺相惜转身便翻脸不认人。地产大鳄骂广告大鳄是个没文化的女个体户,女大鳄回击男大鳄是个土匪加强盗。某女明星每日装模作样戴着墨镜做害怕被别人认出状,让更有名的女大腕气不打一处来,“不就一破唱歌的吗,至于天天弄得跟瞎子阿炳似的,以为别人都得找她签名留念”。骂人的女大腕又不知怎的惹恼了广告女大鳄,女大鳄揭露女大腕打着唱歌跳舞表演三栖演员的旗号,私下还干着把中国人民运送到世界各国的女人贩子工作。比较而言那些英雄莫问出处的男女民间大款就安静许多。顶多哪个烧包男大款在晴空万里时,叫嚣着让一群服务生开着一辆辆豪华加长轿车,奔上高速公路让服务生们遛遛车过过瘾。要么就弄一大帮千奇百怪的各色人等在家开party,弄得服务生恨不能用十台造冰机制作冰块以免挨他的骂。还有一个黑瘦的年轻男人,每天带回不同的欧洲列国妖娆女郎,倒也不枉此生,嫉妒得让服务生弹落眼睛,但说到底他折腾的是自己。但那两个老少女大款却让所有服务生犯怵。老女人年轻时感情上受过创伤,曾经一度钱财两空,刚开始还算正常,后来恶劣到一见英俊男生就两眼发直,一副花痴状。可怜小男生见她如见女鬼,他们中有个小滑头可以搞定老女人,方法就是握住她干姜般的“玉手”不放,两眼泪汪汪盯着她,柔情似水地夸她像嘉宝。另一个小妇人极乖戾,老公一不回家就借酒撒疯让服务生陪她聊天,聊着聊着就聊上了床。
倒是也有众多让人羡慕的绅士与淑女,令人如沐春风,体现出真正的贵族风范。真不是崇洋媚外,这些人大都在国外成长或有着多年的海外生活,懂得节制与收敛的美德。这里的贵族要么就是财富积累得太快,要么就在积累的过程中遍体鳞伤受尽折磨,如今这点放纵与张狂又算什么?!
二进版纳
马宏敏
十多年前,大学实习的时候我曾到过版纳。我们去的那个寨子叫黑龙潭寨,寨边是碧波荡漾的黑龙潭,几乎环绕了整个山寨。一个小小的寨子旁,竟然有如此浩大的湖泊,真有点蔚为奇观的味道。湖边长满了翠竹丛丛,湖水里倒映着美丽的傣家竹楼和满天绮丽的云霞,间或有一群群身披黄袈裟的傣族小和尚或者是一群挑着箩筐,摇曳多姿的小卜哨走进画面,那种美丽更让人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我们安顿下来就开始走村串寨。记得我们几个女生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缅寺。缅寺高大巍峨地挺立在寨子的最高处,翘起的飞檐弧形优美,带着流水一般的韵致。缅寺的大佛爷年纪很轻,大概不到20岁,他像其他傣家人一样充满了热情,每逢小和尚化缘回来,他总要让小和尚捏了一个个硕大的饭团塞在我们手里。傣族和尚出家有点像汉族的小孩子上学,主要在缅寺里学一些傣族的文字和宗教,一两年后就可还俗。所以在寨子旁边的小学教室里,经常可以看到小和尚和小卜哨一起大声朗读课文。也许是这特殊的文化吸引着我们,我们一趟趟地往缅寺跑,全然不知道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姑娘是不能随便在缅寺里穿堂入室的。
当时正逢过傣族的开门节,是和尚的静居斋期,寨子里经常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一切都以缅寺为中心。记得一次放孔明灯,大佛爷专门请我们去看,我们才走到寨边的小路上,大佛爷手下的那些小和尚就敲着象脚鼓迎了上来,围着我们跳起了傣家舞蹈……
在黑龙潭寨十多天,我们一群小女生,简直就像被宠坏了的小孔雀,走到哪里都有笑脸相迎,也常常被傣族老乡拉到家里做客。走的那天,几乎全寨人都来送行,到处只见人头攒动。大佛爷特意让寨里的人给我们做好了糯米饭和各种菜蔬,用芭蕉叶包好了递到我们手上。
去年我终于又二进版纳。去了以后才发现我再也找不到那些穿筒裙的美丽少女了。景洪街头被豪华的酒店搞得面目皆非。街上看不到一个当年身披黄袈裟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的小和尚。在橄榄坝的寺庙里倒看见了小和尚,刚抬起相机要照,一个小和尚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抬起手来摇了摇。手腕上的钢壳手表在阳光下锃亮地闪烁了一下,我满腔热忱的心里顿时被划了一道生硬的伤痕。在景区里倒是常常看到穿着艳丽筒裙的小卜哨,可是这些盛装出场的小卜哨总给人一种很假的感觉。在曼真八角亭,一个4岁左右的小姑娘,穿着艳黄的筒裙,打着一把小红伞,画着浓黑的眼线,涂着鲜红的口红,一个劲地追在我后边喊:“阿姨我最漂亮,和我照一张吧,只要一块钱……”
外国诗
布丁
有个诗人,诗写得不好,就改行写足球评论。2002年世界杯,他想凑齐32个国家的诗句用在球评里,英格兰、德国、爱尔兰都好办,有大堆的诗人等着挑,巴西、韩国也好找,惟独塞内加尔比较费劲。他这么一折腾,倒让我想起自己读过的外国诗,十多年前有个文学丛刊就叫《外国诗》,好像只出了一两期就没有了,我读外国诗就从那里开始。
那时候,我喜欢一些狠叨叨的诗句,比如狄兰•托马斯的 ——“而死亡也不能征服,赤裸的死者会同风中的人,西沉明月中的人合为一体,当骨头被剔净白骨变成灰……”还有“当我用液体的双手敲击子宫,让血肉涌入之前……”后来,这些恶狠狠的诗句被我忘掉了,惟独一段 ——“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动花朵的力/催动我绿色的岁月;炸裂树根的力/是我的毁灭者/而我暗哑,无法告知佝偻的玫瑰/同一种冬天的热病压弯了我的青春。”记住这段,是因为我曾经翻字典查“佝偻”和“暗哑”的读音。
做一个诗人要写几万行诗,而我们用于诗歌的情怀并不足够大,经历好多年,能再背诵出几句来,那几句也许就是诗人最伟大的地方。留在心底的这几行诗就是对伟大诗人的敬礼,来段里尔克 ——“尽管世界变化匆匆,有如白云苍狗,所有圆满事物一同复归于太古。在变化和运行之上,更宽广更放任,你的歌在继续唱,弹奏竖琴的神。苦难未被认识,爱情未被学习,在死亡中从我们远离的一切也未露出本相。唯有大地上的诗歌被尊崇被颂扬。”
读诗和背诗不一样,《四个四重奏》我读了44遍,可我能背出来的只有三行 ——“在那些时候,我对我的灵魂说,静下来,不怀希望地等待/因为希望也会是对于错误事物的希望;不怀爱情地等待/因为爱情也会是对错误的事物的爱情。”艾略特的宏伟篇章被我的记忆缩减为几句酸溜溜的情歌一样的东西。
有的伟大诗人被我遗忘得特别干净, 比如海涅,他写出“乘着歌声的翅膀,我的爱人”,这首诗很像蔡琴唱的《张三的歌》——我要带你到那美丽地方看一看。最近的一个晚上,我乘出租汽车回家,出租车司机帮我回忆起海涅的诗篇,这个一脸汗迹的汉子背诵出全篇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祈求;我们的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他对我们只是愚弄和欺骗。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还把我们像狗一样枪毙。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这里只繁荣着耻辱和罪恶,这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腐尸和粪土养着蛆虫生活。我们织我们织,梭子在飞,织机在响,我们织布,日夜匆忙。我们织我们织。”
司机说他17岁上高中的时候学过这首诗,20年来一直会背。有时候他会把“我们织”改成“我们开”。
这个世界不是为你这样美好的人准备的
夏至 图 谢峰
有一天从超市拎着两大塑料兜子的柴米油盐回家,在小区门口看见一对高中生模样的少男少女背着书包站在树底下,好像是闹别扭了,女孩儿抬头望天微微地噘着嘴。这时候男孩不知说了句什么,她忽然就笑起来,说:“云真好看。”我累得不行,放下东西也顺势望望天,没找到什么好看的云,就觉得他们脸上透明干净的青春才真好看。
记得我上中学那会儿还不怎么流行早恋,暗恋就够课余时间使的了。后来到了大学,爱得元气大伤,在倾盆大雨里死死抱住那个要出国不要我的人哭得歇斯底里。再后来伤口慢慢平复了,又昏天黑地开始恋爱,结束也不觉得就是世界末日。现在逛商场,总有促销小姐说您皮肤挺好就是还不够亮试试这个吧,可惜那些化妆品大都让人看起来像油脂分泌过旺的亮 ——就算SKⅡ也不能让关之琳的脸上有18岁的光芒啊。
可那光芒究竟是被什么摧残了呢?有句歌词怎么唱来着,这个世界不是为你这样美好的人准备的。每次看到这样的话我就为自己正在和这个世界越来越相得益彰有点郁闷,至少要吃完一顿水煮鱼才能忘记。不过大部分时候我都对改变安之若素,每天每夜,我朝自己曾经嘲笑轻视并且以为永远也不能将就的那种生活快步走过去,可这也没什么不好的。我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天使在人间,只有奥黛丽•赫本和童年的秀兰•邓波儿那样的精灵才能用美好两个字来形容。
况且这样的肉麻话也只能出现在歌词里,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我现在顶受不了偶像剧式的露骨表白,一见到电视里有人声泪俱下地说“求求你别离开我”就赶紧闭上眼睛换台。这样豁出去不要脸面自尊的爱情让我替他们感到难堪,全然不想自己当年也是这么一副“只要你不走怎么都好”的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