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看西看:义工,非赢利工作,募捐晚会
作者:娜斯(文 / 娜斯)
我的“慈善”活动少得可怜,不过因为青基会的事,说说也算个介绍。有些事看了是让人糊涂。基金会跟“非赢利”(non-profit)是分不开的词,所以青基会把捐款拿去投资,不管动机如何,让国外的人听了是得吓一跳。国外的基金会投资债券,那跟存银行风险差不多,所以才可以。做基金会的人应有理财能力,有管理能力,但不需要你赚钱。你需要做的是怎么说服赚钱的人掏腰包,你再安排谁最需要这笔钱。你的工资等于是捐钱人和受赠人因为你的工作而给你的报酬,如果你嫌工资不高,你应该去公司工作,你不会选择非赢利机构。
其实,谁也不指望你是雷锋。有些非赢利机构工作虽然发不了大财,但是比华尔街的工作轻松许多,所以,也不算什么奉献。当然,那些在世界各地难民营工作的救援人员又是另一回事,对他们我充满敬意。
非赢利机构工作跟义工是两种性质,非赢利机构需要日常运作人员,也有义工,前者拿工资,后者是志愿,没有报酬。我在美国“圣经协会”打过工,这就是一家非赢利机构,推广《圣经》的。我到这里去工作,不是因为我想为宣传基督教教义而奉献,而是因为正好有这么一份工,我到这里工作是领工资的,但顺带得到了不少关于《圣经》版本学的知识。这个工作9点上班,5点下班,真的是朝九晚五,我还从没遇见过,于是得出非赢利机构工作清闲的结论,实际上这跟救灾救难的工作不是一回事,是白领的非赢利工作。在这里工作的基督徒不少,所以还是有不少人是出于宗教原因选择到这里工作的,他们每星期一早上有个礼拜,唱圣诗念经文什么的,我也被当成教徒请去胡乱祷告了一番。
美国“圣经协会”可想而知钱是不少的,总有教徒捐钱吧。在纽约上西区一幢七八层高的小楼里,楼下有家书店,只卖《圣经》和基督教书籍。我在圣经协会呆的时间不长,没搞清它的全部目的,有专管募捐的部门,有专管财会的部门,我呆的那个部门是发放《圣经》。比如,监狱里的犯人都可以给“圣经协会”写信,要求某种某种版本的《圣经》,“圣经协会”就会给他们寄去,真正做邮寄工作的就是义工。我做了一阵电脑统计方面的事,没事看看那些监狱来信,有时看个没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且终使我明白,基督教有这么本书,对他们的文明发展有多重要。再不读书的人,也有这么本书要读。那些监狱里的人,他们写的信经常让我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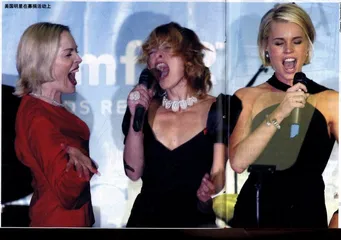
美国明星在募捐活动上
我在“圣经协会”工作时间不长。至于义工,在美国也有好多形式。“9·11”之后,我就到红十字会当了一次义工。红十字会有一些基本工作人员,但也有一个义工网。像我的那次当义工,就是因为申请救援群众中有各种族裔,所以红十字会临时需要翻译。我去一看,不管是普通话还是粤语都有几个人在那里了。我帮忙翻译的两位唐人街同胞,都是福建籍人士,好在尚能用普通话交流。唐人街离世贸中心不远,“9·11”后经济大受影响,所以红十字会给该地区失业或受创人士发放救济。这些人要填一些表格,携带一些证明。结果,我帮助其翻译的那位红十字会的先生也是义工,不时要跑到后面总管那里询问条文规定的意思。总之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临时抱佛脚,但你要承认这是红十字会这种救援组织最有效的运作方式。灾难不是天天发生,所以你不能用捐来的钱养很多闲人在那里等出事,而是有一个基本的人员基础,然后需要时义工来帮忙,当然是义务的。像我当了一次义工之后,信息就留在了红十字会,以后他们有这方面需要,可以打电话给我。
还曾经到布鲁克林的学校去刷墙,这是公司组织的义务活动。很多公司有这样的活动,也算让员工来个“加强团队情感”什么的。我把那看成去玩,忘了什么义工不义工。
中国学生组织的一个读书基金会,捐钱给中国失学儿童,也都是义务服务,网站维护,数据输入等等,都是义务性,而且很多人是通过网络联系,根本不认识。
一个人愿意捐钱给一件什么事,或者为一件事当义工,都是跟自己的一种想法或情感有关系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做这事,这种志愿的事,绝对要视乎你内心的需要,而不应被人强迫。对我而言,捐钱给失学儿童,这不需要任何解释。我还愿意捐钱的地方是美国癌症协会,原因是母亲患癌症去世,希望癌症研究有发展。所以,在美国每个人捐钱都有自己的一个什么想法,是一种个人选择。提到非赢利、义工、慈善、捐款,我想不要提“雷锋”这种概念。我们过去那种完全去除私心的教育方式我想是很失败的,所以,“爱心”可以提,“奉献”最好别提,把整个事情又弄糟了。

义工是“奉献爱心”的表达方式之一
我介绍过纽约的富翁市长彭伯。此公自传《财富、智慧和工作》的最后一章专讲慈善,像是给富翁们的自我帮助手册。按其说法,有钱人捐钱,不是关于负疚感,不是道德义务,或者甚至认同他人的痛苦,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实现。当你赚了很多钱后,他说:“第一,不要为交税担心,第二,不要娇惯你的家人……第三,自私自利,为自己买巨大的乐趣,把你大多数的财产捐给慈善机构!”是不是所有富人都能像此公那样想得开是另一回事,彭伯自己倒是从自己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到纽约的近600个组织都没事就捐钱,还给哈佛捐钱设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捐钱的奖学金。
美国人这种捐钱意识与其制度分不开。其实交税本身也是回馈社会,但从个人选择角度,交税与捐款的不同是,捐款跟个人取向有关。所以美国的制度是捐款可以减税,实际上都是回馈所得,但一个是强迫,一个是自愿,这样给个人以选择的空间。美国人的义工意识也是从小培养的,像小孩申请大学,不像中国只看考试成绩,而要看你课外技能,包括体育、音乐之类的技艺,也包括社会活动,里面就有义工一项。
美国的募捐活动也是多彩多样,让你边玩边掏腰包。举个例子,最近,美国肝病协会大纽约分会举行募捐晚会。“肝病协会”是为肝病研究、肝移植手术等募捐。他们想出来的办法是,找了纽约若干名餐馆的主厨,义务制作七道菜的晚宴。这是你有钱也吃不到的晚宴:你很难把这些高级餐馆的名厨师召集到一起。于是,这些名厨出力,你出钱,外加大享口福,于是厨师和你都为肝病协会做贡献了。
晚宴上,讲演人是百老汇制作人Marty Richards,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患肝病去世的,所以以身说法,讲述肝病研究的重要。这些活动都会找些名人发言,还有捐钱多的公司或个人讲话。不仅是通过晚会募到一些钱,而且通过引起媒体关注而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信息。“肝病协会”的一场名厨晚宴请到475位客人,得到的捐款是:45万美元。
也不是必须有名厨才能募到钱。有时,是你又得出钱还得出力。比如“乳癌协会”还有“同性恋协会”都是到中央公园去集体走路。你要加入这个走路队伍,你得捐钱。你得到的乐趣?也许是与名模为伍?也许是加入集体的快乐?这个我没有参加过,我只是被同公司一个同事索去了一张支票,他要我们每人出20块钱,声称要代表我们大家去走路,并帮我们把钱投到现场的募捐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