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里的情感协奏曲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林逸聪)

Ludwig van Beethoven
我喜欢这张明星片上的贝多芬形象:坚硬的脸部线条、怒发冲冠,背景是早春那种纯净的绿色。这是十多年前一位好友刚到德国波恩时给我寄过来的,随明星片寄来的信上说,波恩是“二战”中保存较好的城市,美国飞行员当年在轰炸时把它变成一个盲区,因为那是贝多芬的故乡

海菲茨与波士顿交响乐团、明希合作1955年录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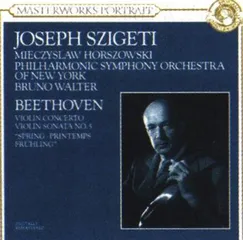
西盖蒂与纽约爱乐乐团、布鲁诺·瓦尔特1947年录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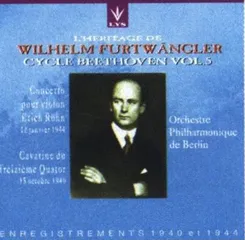
罗汉与柏林爱乐乐团、富特文格勒1944年录音
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被称为这种音乐形式中最伟大的一首,原因是其中凝聚了最丰厚的情感。这首作品作于1806年,这是贝多芬的个人命运中特别值得回味的一年。这一年是普鲁士与法兰西决战的前夜,贝多芬刚刚从耳聋、“海利根斯特遗言”中走出来。这一年秋天,他前往奥匈边境的马尔屯法扎尔,这首协奏曲的音乐动机就来自秋天的马尔屯法扎尔,在那里他继约瑟芬与朱里叶之后,与布隆斯维克家的第三位伯爵小姐——姐姐泰丽丝产生情感纠葛,再次受挫后终其一生与爱情无缘。这一年,在他生命中生长出了最具抒情气息的作品——除这首协奏曲外的《第四交响曲》与《拉兹莫夫斯基四重奏》中的慢乐章,几乎都浸透了一种美得令人伤感的沉思默想。
这首协奏曲为当时维也纳剧院最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克莱门特(Franz Clement)而作,充分考虑了克莱门特对技巧表现的要求,所以乐队尽管仍然是进行曲式激情洋溢的节奏,却自始至终是小提琴的和谐陪衬。根据音乐史学家的分析,此曲主题来自马尔屯法扎尔,也就是说在1806年冬天贝多芬把他秋天的情感淤积转换成了克莱门特的华彩表达。这是贝多芬惟一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我在其中听到的是一个36岁已进入秋天的生命对女性与爱情的描述。这种描述包裹在作为意志力与情感的刚柔之间,而这意志力中柔肠寸断恰恰是贝多芬留给我们最动人的精神财富。
刚开始我听到这首协奏曲是比利时有贵族气质的格吕米欧与柏林爱乐乐团前首席施奈德汉及海菲兹演奏的版本,这三个版本曾使我把这首作品单纯解读为贝多芬与泰丽丝甜蜜情感对话的记录,称第二乐章为“阳光下的情意绵绵”。因为这三个版本中的小提琴都太亮丽了,它美得耀目,且有些娇嗔。它与乐队的关系,几乎没有冲突——乐队就像贝多芬来到马尔屯法扎尔,她在秋天明净的阳光下一出现,就成为美丽圣洁的化身。他与她的每一次相遇,都构成美的渗透。到慢乐章,完全是一种美丽的倾诉,尤其是海菲茨那种华丽表现,简直勾勒了一个美得要将人融化的意境。第三乐章的回旋曲就像是情感意味悠长的舞蹈。
而这一切在听到被称为“小提琴思想家”的匈牙利籍的西盖蒂1947年演奏的版本后被彻底改变。之前,我曾听北京大学的爱乐前辈严宝瑜先生叙述过“文革”前关于这张珍贵唱片的记忆。他说,录音太早了,放在唱机上噪音劈劈啪啪,就像是打炮,但味道是最好的。等我听到被翻制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CD时,噪音已经不再像“打炮”,但我确实听到了出乎意料的小提琴的“哽咽”——在本来是阳光下极端甜美的第二乐章,变成了小提琴略似嘶哑的叙述,它与海菲茨的清亮相成了那样强烈的对比。再仔细听,其实第一乐章的发展部,小提琴表述就有了那种苍凉。这种苍凉的弥漫是那样伤感,到第二乐章完全成了一种凄婉。我开始被这种一个人意志力之后的脆弱情感所震撼。
再之后,我听到了富特文格勒1944年与当时柏林爱乐乐团首席罗汉(Erich Rohn)的录音,这个在纳粹时代被认为是最深刻解读的录音又给我提供了另一种体会。富特文格勒以他惯用的放慢速度使整首作品陷入一种迷人的沉思默想,没有人像他那样,把乐队处理得那么弱,在弱中又涌动着一种柔韧。小提琴在第一乐章出现时是一种清丽,但很快就能感觉一种空间的阻隔——乐队与小提琴好像都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关系所左右,使小提琴只能拔高了歌唱。第二乐章,富特文格勒没有让罗汉的小提琴极端地“哽咽”,但乐队与小提琴的对话是那种伤感的无奈,在这种伤感的无奈中既有感伤的婉转,也有在这婉转中蕴涵的力。第三乐章则好像是要对这种感伤的挣脱,或者是对这种感伤与挣脱的双重哀叹。
有音乐评论家认为,1806年贝多芬彻底埋葬了他对女人从情感上的追求,他的情感内敛在音乐之中,构成了他的音乐中的情感丰富性。按这位评论家的观点,我们太多的情感都变成平庸的爱情宣泄掉了,而贝多芬的情感凝聚而成他音乐中最打动我们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