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92)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布丁 张小尹 愚妹 晓玮)
检查制度
布丁 图 谢峰
池莉女士新出了本小说叫《水与火的缠绵》,我已经好久没看小说了,所以忘记了坏小说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本小说让我想起所有坏小说的要素。对于一个庸俗的小说作家,我本没有太多的要求,只是想一个人有勇气把一个作品完成,总该在创造的过程中停下来审视一下这东西到底值得不值得。创作者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审美尺度,当他对作品不满意的时候,应该果敢停下来,去干点儿别的。
这个要求对小说作者来说并不过分,但对电影导演来说却显得太残酷。好多电影,看到半截就感到导演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拍下去了,他的创造力枯竭,悬在半空中下不来,可为了对得起投资还要硬着头皮把故事讲完,把片子剪出来给大家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蓝宇》。如果导演是个不负责任的混蛋,成心要拿他的烂片子出来恶心观众,也就是说他抛弃自己的审美尺度或者尺度太低,怎么办?咱们这里有电影审查制度,就像食品卫生法一样严把质量关。比如高晓松的电影《那时花开》,被认为是没有达到电影作品的基本技术要求,不能公映。检查机构还像是老师,可以让创作者回去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这不仅是对观众负责,说是也要对艺术负责。修改之后的《那时花开》现在公映,就像一盘菜没炒好要被端回厨房再炒一道。
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应该不错,可还过不了检查制度这一关,为什么?检查制度说是要拿更高的艺术标准要求他,他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是那么棒,第二部怎么能退步呢。没看张艺谋的电影越来越臭吗,所以姜文大师要严要求。
我在大街上第一次看到盗版的姜文主演的《鬼子来了》就买回家,打开一看是《红高粱》,可片头三个大字已经被认真地改为“鬼子来”。后来在网上居然能下载这个电影来看。检查制度造就了新的电影发行渠道,并且提供了新的看电影方式。比如贾樟柯的一个电影,有两种方法可以看到,一是恰逢民间电影节,你作为艺术青年去看;—是法国使馆搞文化活动,你拿着请柬去看。这样,检查制度还间接造就了艺术沙龙性质的文化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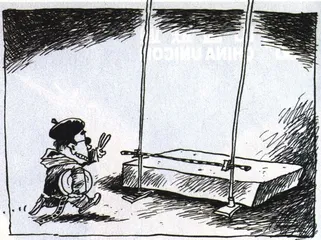
5月7日
张小尹
如果柴可夫斯基和泰戈尔还健在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愿意悲剧发生在自己生日的。当埃航的波音737和中国北航的麦道82相继在突尼斯和大连坠毁的时候,我正在庆祝一个同为柴可夫斯基迷和泰戈尔迷的生日。过生日的家伙平常最可恶的事情就是向我这种压根不识音律和不黯文学的人炫耀“阿柴”如何和“阿泰”如何。“狗日的,”他看到手机上收到的短信后,气急败坏地骂道,并迅速冲向正在长长延伸出无穷无尽悲伤的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的终乐章。
“飞机又出事了,”他坐下告诉我。然后,我无语。因为他也无语。
打开电视,打开电脑,像寻找猎物一样寻找最新的信息。“果然是真的,”泰戈尔的疑问回绕在脑间,“没有一个人不惧怕灾祸,但灾祸发生的时候又能以何种能力施以逃避呢?”
一直到第二天、第三天,记录飞行信息的黑匣子还是没有找到。“阿柴”的传记、《悲怆》和“阿泰”的《难以避免的灾祸》却相继被我找到。第一次翻开早已经发黄的传记和《难以避免的灾祸》,第一次打开唱机,悲怆的人生和悲怆的音乐开始第一次浸淫我。当《悲怆》终乐章呐喊而出的时候,我记起了大学老师原文念叨过的话:“西伯利亚的大雪中飘着一团墨绿色的温暖旋律,一望无际的寒冷和洁白浮动着淡泊和迷人的哀伤,一行长长的足印在白雾腾腾中向着古老的森林延伸,无始无终,——凄绝美艳,虽然难免与人以窠臼的感觉,但是却带着一抹悲伤的感情,就好像寡妇夜半的哀哀啼泣。”
“每一个柴可夫斯基迷都有一台哭泣的机器,”我记起了我那个最可恶的朋友的话,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哭泣带来的感动。大学老师也曾介绍说;很多时候,很多场合,灾难过后悲痛、默哀,继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轻轻传出早已是超度亡灵的程序。“人禁不住啜泣,眼泪流了下来,眼泪流到心里去。”也成为慰藉灾难的怨语。
柴曾经说过:“你很难想象知道自己的时代尚未过去是一件多么值得宽慰的事情。”但是我想,5月7日,没有一个人可以宽慰自己的日子。同样还有泰戈尔,这个印度老人一生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篇,偏偏会有一篇叫做《难以避免的灾祸》,并且偏偏破坏了他老人家的一个原本很美好的生日。
《悲怆》在哀愁中结束,但人们的悲伤却依然写在某报纸称的撒满阳光的脸上。一位在加拿大留学的学生在网上对中国说:“我是一名在加拿大留学的学生,本来不想发言的,真的很难受。5月7日是我的生日,身在异国,感受是不同的。我对这次事件表示沉痛的哀悼。但好像每一年我的生日,都会有关于中国不好的事发生。记得1999年5月7日至8日,我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身在异国,看到自己的同胞遭遇如此不幸,真的很难过,很难受,留给我的又是一个难忘的生日,为什么总是在这一天——我无言了。”
女人百炼成钢
愚妹
和很多人一样,我这辈子看的第一本外国小说就是《简爱》,还清楚记得当年看的是译林出版社的孙致礼版本。除了抄下那段经典台词以作谈资,十几年后仍觉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结尾。
简爱因为得知罗切斯特已有妻子而感到丧失了“在坟墓和上帝面前”的尊严,继而从婚礼上出走。这点没有问题,这次出走几乎和上世纪初娜拉的那一次齐名。可是好像很少有人注意简爱是怎么回来的。最后她下定决心回到罗切斯特身边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已成鳏夫并身患重疾。是什么叫这个倔强固执的女子改变主意愿意忽略和容忍这一点呢?你当然可以说是因为爱情的魔力和召唤,可简是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否则她不会出走。除非这一点大有保障,否则她也不会回来。你看,惟一发生变化的情况就是——简得到了一笔遗产,她有钱了。这让她有底气回到那座庄园,而不至于有危险成为某个人的附庸。
承认并尊重金钱的意义,尤其是对女性独立的意义,这才是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一点也不假惺惺。五四时期,人们热衷探讨娜拉的出走,可我奇怪为什么人们一提到简爱就开始背台词,却从没人说起简爱的回归。在我看来,这个回归所昭示的意义和思考,丝毫不在娜拉和简自己的出走之下,即便到今天也还是这样——还是有大批人在叫嚣要“嫁个有钱人”,光叫不过瘾,还整个电影出来寒碜人。
今年“三八”那天,我难得空闲,重看了一遍《乱世佳人》,上一回看还是青春期呢。这一回兴趣从巴特勒转到了斯佳丽身上。这个女人真是有意思,她比简爱又要有魅力多了,性感,倔强,并且野心勃勃,拥有毫不掩饰的占有欲望。她身上有我们熟悉的很多影子,比如邓文迪、章子怡。她要活到现在,一准是个麦当娜。说到娜姐,那就又厉害些,她显然不会在暗恋一个人达十年之久后,才发现自己原来爱的是另一个人。她太知道自己要什么,最后一点遮羞布也不用。她也因此变得更加强硬和难以驾驭。她的导演老公盖里奇说:要想给她导戏,惟一的办法是向前一步走,然后抓住她的胸部。我看除此之外,她在本质上和一个男人也没什么区别。
从简爱到斯佳丽再到麦当娜,女人总也离不开男人、金钱和权力。不过,显然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像简爱那样好运,凭空冒出一个有钱亲戚,还很快死掉把钱留给你。她们大多死的死、老的老、伤的伤,总也难以得到幸福。所以,与其羞羞答答等待,不如大张旗鼓自己下手。女人早已百炼成钢,任你金枪不倒,我自刀枪不入。
售票员情结
晓玮 图 谢峰
一直以来,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叫做“售票员情结”的东西。我喜欢售票员同志古意盎然的票夹板,喜欢她们使的那种单孔的打洞钳,我还喜欢用来开门的那个黑色活塞状按钮,就这么轻巧地一拉,“嗤……”一声,门轰然地开了,人上人下。
小时候,我沉醉于站在售票员座位下那个突出的平台上的时光,当然只有在车很挤的情形下才有此幸。如果车不是很挤,女售票员同志是断然不允许我贴着她站的。我把在车上的无穷无聊时光都花在观看售票员同志整理钱上了。结论是,这算是一门熟能生巧的手艺活:她们先把每张票子的角都用尖指甲刮平,每十张成一叠,然后蘸一点票夹板内置的小海绵,飞快地复点一遍。攒到十叠后用橡皮筋一箍,然后在小帆布包里找到那叠票面所属的铁夹子,撑开,夹紧,最后随意地把那一铁夹子的钱往包里一扔。我每每在心里帮着她数钱,发现自己在连续数数上存在致命弱点,我还惋惜,整理了半天的钱,最终只是为了上交车队时的形式美。
在拿捏时间方面,售票员同志也很有火候,往往在理完钱或者票的时候,车就到站了,可能其中也有和司机的默契。于是,她们操起那面写着“慢”字的油腻小红旗,推开窗门,用旗柄笃笃地敲着外车厢壁,并铿锵有力地吆喝,传达着如果车不“慢”下来大家就得闪的意思。然后开门,大半个身子倾到窗外一阵乱捅胡戳,骂山门,使劲地推上门,按电铃,头还这么佝一下,然后重新振作着开始本职卖票工作。
记得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曾在一次春游回校的路上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当时老师坐在那辆包车的售票员座位上,我紧贴着她站着,心里盘算着如何等车停稳后,迅速取得机会难得的开门权。我当即回答道“做售票员”。原来以为她会有点失望,没想到她当时只是淡淡地,以一种过来人的腔调哼唧道:“没啥意思的,这种活计做起来很吃力的。”
弗洛伊德的那些情结通常会用一个我总也记不全的神话人物来命名,我决定把我的这个情结搞得纯朴一些,于是管它叫做“CONDUCTOR COMPLEX”,也就是“售票员情结”。据我的经验,有这个情结的人,多半现在正心不甘情不愿地从事着某种机械的脑力工作。而这份脑力工作也牵扯到简单算术、稍许腕力、戳人捅人、吆喝骂街、拿捏时间和搭档的默契配合等等。最重要的是,兢兢业业地为人敛完了钱数好了码齐了,还得立即把它们扔到一个无形的白口袋里。但是比起车厢里广大辛苦地站着还看不到窗外的乘客,有这个情结的人好歹还能坐着,好歹还能在数钱的间隙瞅一眼窗外又出什么事了。所以,有“CONDUCTOR COMPLEX”的人还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