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与排行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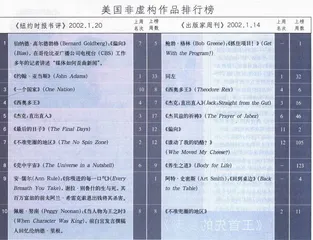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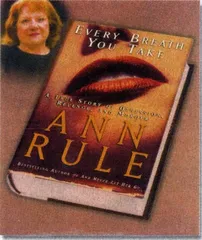
本期上榜新书不多,我们要介绍的则是罗伯特·斯凯德尔斯基(RobertSkidelsky)撰写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一书。
提起凯恩斯这位本世纪西方杰出的经济学家,人们自然就想到了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凯恩斯主义”,其主张的深远影响固然是众所周知,但其产生及对英国战时经济的重大作用,则是该书叙述的中心。
温斯顿·丘吉尔作为英国狮的最后代表和战时首相,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如何得到财政支持注意不足,对于战后的经济安排更欠考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那是凯恩斯的职能范围,用不到他多虑。事实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自从亚当·斯密以来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也是二战中丘吉尔内阁的金库。一战之后他曾撰文,言词激烈地反对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他警告说,如果战胜国坚持使战败国贫困化的政策,“我敢说,复仇绝不会姗姗来迟的”。在他不幸而言中之后,他的“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便是使同盟国“比上一次要做得出色”。而由于凯恩斯折服人的辩才,同盟国一方也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遗憾的是,丘吉尔在他那长达六卷的回忆录中只有两三处简单地提及了凯恩斯。多亏罗伯特·斯凯德尔斯基的这部三卷本的凯恩斯传记,才为我们提供了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故事和贡献。我们这里要介绍的是其最后一卷,副标题是《为自由而战,1937~1946》(FightingforFreedom,1937~1946)。
凯恩斯和丘吉尔一样能言善辩。一位着迷的听众说道:“他属于我们的物种吗?在他身上有一种神奇惊人的东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巨大和神秘,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怪斯芬克斯,……”应该说,斯凯德尔斯基的这部权威传记围绕着历史记载,深挖传主的生活和性格,远远胜于此前一些传记只写凯恩斯理财和外交上的成就,从而拨开凯恩斯身上的谜团,使他以活生生的普通人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在描述凯恩斯从1936年发表他的极富创见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至1946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四个月之后他去世的十年的第三卷传记中,作者表明了这位一度是希鲁姆斯别里(伦敦的一个美术中心)的唯美主义者、剑桥大学的教师、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艺术赞助人和股票投机商的凯恩斯,如何将他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英国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如作者所写:“这是一个故事,其超出一切之处讲的是凯恩斯的爱国主义。”
在这部引人入胜的有关无畏的思考能力的作品的开篇,作者讲述了时年55岁的凯恩斯(他生于1883年)正患有不治的心脏病,似乎已在他位于蒂尔顿的乡居中早早地过着退休生活,由他的妻子、俄国芭蕾舞演员出身的丽迪亚·洛波科娃照顾着,她貌似公主,具备娴熟的护理素质。他过着一种乡间地主似的生活:看着别人剪羊毛,为他的牧羊犬犯愁,躺在床上一连几小时浏览善本书的目录,接二连三地给报社编辑写信并给他的股票经纪人发指示。奇怪的是,德国一种有奇效的药物和丘吉尔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讲话在两年后使他一跃而起。凯恩斯虽然也和他的同代人一样对战争备感恐惧,并曾被人一度称作“绥靖的‘精神之父'”,但他实际上从未幻想过那些“强盗政权”会被安抚。“他厌恶纳粹统治,在1933年以后从未访问过德国,而且对希特勒经济政策的成功从不理睬。”不久之后,刚刚恢复活力的凯恩斯便在财政部的一个房间里既无职务又无工资地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了,并且在丽迪亚的陪同下作为英国的主要谈判人对美国华盛顿进行穿梭外交活动。
凯恩斯接受的第一项挑战是策划如何不伤英国市场经济元气而从财政上支持战争。他的那部名著《通论》本是在大萧条的局面下激发出来的有关经济衰退中削减税收和公共工程的,但随着英国投入战争,政府赤字高扬和失业迅速缩减,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是过少而是更多了。他开出的处方便是紧缩国库。当他的一名美国门徒对此表示惊讶时,他回斥道:“你比我本人更像个凯恩斯主义者。”
一些人认为凯恩斯是支持政府集权的圣者,实际上,他的《如何支付战争》一书恰恰是专门保护个人自由和防止英国变成中央计划“奴隶”国家的蓝图。他手持一张定量配给计划嘲讽说:“限定物价的政策加上店铺中无物可买——这是俄国当局多年来烦恼的权宜之计——无疑是防止通货膨胀的最佳途径之一!”
他接受的第二项挑战是与华盛顿谈判英国的战时债务问题。“丘吉尔为保持大英帝国而与纳粹德国交战。凯恩斯则为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与美国交锋。对德战争获胜了,但为此,英国却既失去了其帝国也失去了大国地位。”具有保守党观点和身为沃维克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作者在这里同意了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英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美国并接受美国借贷条件是犯了错误。
凯恩斯后来把目光转向战后的财政和贸易安排。他主张,如果美国想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和英国殖民地的解放,就要为遭到战争蹂躏的国家输入大量的现金。这一建议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立,他虽在马歇尔计划实行之前去世,但他在经济问题上的创见却影响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