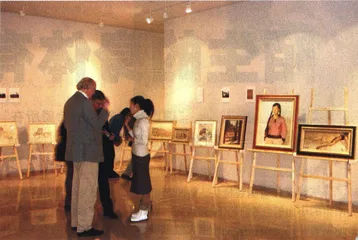蔡国强的焰火与艺术展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蔡国强展览作品
蔡国强就像上海的熟客,2月1日在上海美术馆开幕的“蔡国强艺术展”好像势在必然、理所当然。美术馆邀请来参加开幕式的客人都入住在展馆对面的金门大饭店,这里的服务生似乎都知道蔡国强住在这里,并且明显地为之骄傲。因为2001年10月上海Apec会议开幕烟火是蔡国强设计的,他给上海带来了新的风光和骄傲。
对蔡国强,不知算是荣归故里,还是算答谢旧缘。蔡国强是福建人,1981到1985年间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上学。那是一段运动、风潮此起彼伏的时期,很多艺术主张都同时烘托出一些艺术家的名字。而按蔡国强自己的话说,那时候他做不成什么事,“净想”——胡思乱想。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先在日本后在美国工作,他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个艺术大展上。现在重回上海开个人展览,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受瞩目的艺术家之一了。
真正在上海出名还是因为去年的焰火,尽管在这之前他也参加了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去年上海美术馆开始筹备蔡国强的艺术展,其中的一个作品是烟火,他提出的一个爆炸方案是炸出一个天梯。美术馆在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时,主管部门刚好在筹备Apec的开幕焰火晚会,就通过美术馆邀请蔡国强来做晚会的焰火总设计。
蔡国强在为此次展览准备的一本小册子里说,他当年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曾用鼓风机吹画面上的颜料,鼓风机一吹颜料在画布上到处跑。后来用火烧油画。很多尝试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自我破坏的过程。后来用火药炸也是在同一个逻辑之下。因为他自觉是个本性保守的人,迷恋中国古典文化,这种文化的支撑让他感到自己不寂寞。
可能因为这是蔡国强在国内,尤其是在上海的第一次个展,他在选择作品时一定是感情多于主张。当然他的作品里似乎一向都主张与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由此带给他的联想对应。比如他为威尼斯带去了马可·波罗遗忘了的东西,因为那是威尼斯的展览。比如《龙来了》这件作品产生于美国舆论大讲中国威胁论的时候等等。而上海这个地方可能更多的是与他在国内生活情感记忆的多层次联系。
一楼展厅是两件新作品,一件叫《梦》,一件是《网》,都是与他现在对此地的印象有关。一进门就能看到一个尺寸不小、以上海龙华塔为造型的鸟笼,鸟笼里的100只金丝鸟啾啾着跳跃着,与鸟笼相连的一根绳子另一端连着一根倒扣着的“草船借箭”下的桅杆。渔船的木头骨架是他从他的家乡泉州海边找来的,因为久已弃用,木头已经满是裂缝,好似久远的乡亲。船上扎满的3000支箭金灿灿地格外耀眼,倒扣的船身下躲着一台可随时上网的电脑。1998年他在美国参加《新中国艺术展》做“草船借箭”时是为了对应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各种指责,这些指责对于被指责的一方是个借力的机会。而现在这艘浑身披满金箭的船有可能变成一种障人眼界的无形大网,与鸟笼有类似的意思。但因为鸟笼的绳子拉着渔船的桅杆,船好像一个巨大的捕鸟器。到底什么是网、谁在网中的是是非非有点乱了。展厅的另一边,一块长20米宽10米的红绸占满了展厅地面,红绸在5台鼓风机的鼓动下波浪般地涌动,天花板上垂吊下来的红纸灯高低错落着与下面的红色波浪静静地呼应,定是梦之所想。这些纸灯又是出自泉州的传统工艺。所想之物正是充斥世界各个角落的大小器物,从火箭、飞机到钢琴、沙发、洗衣机、摄像机无所不包。蔡国强指点说,其实不管我们想象了什么,还都是红的,本色不变。
在开幕式之后被议论最多的是三楼的作品。在这里,有他的标志性的作品——《炸痕》,这些新作品是按照去年Apec时的烟火设计主题做的,在被裱得很厚的宣纸上炸出的火药痕迹与发光打眼的烟火比起来显得更有凝聚的力量和焕发联想的张力,而且更沉着,虽然是静态无声的。蔡国强还把当时的设计方案都展示出来,其中有大约30%与当时的实地实施不同。他设计的天体本来是作为烟火晚会的开场,从浦东到浦西同时点燃的导火线让火光在江面上奔跑,空中有一飞艇带着一架装有焰火的梯子,江面上的焰火会顺着这个梯子直上天空。但因为“9·11”的影响,会议期间的上海绝对净空,任何飞行物都要打下来,这个计划就放弃了。蔡国强的作品由于涉及的主题和他的作品样式规模巨大,常常要和展览所在地的管理部门打交道,他一向能很有分寸地处理各种要求,包括他自己的要求。焰火晚会是他和中国政府部门的第一次交道,除了必要的改动设计和各方的协调,他说,惟一的不同就是,在国外即使是克林顿要在23层楼上放焰火也要一家一家敲门去征求大家的同意。
比较起这些不久前的记忆,这些已经安静下来的炸痕,另一部分是更远一些的记忆,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的记忆。叫做“蔡国强收藏马克西莫夫作品展”。蔡国强说马克西莫夫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巨匠,但也许不是学美术的人大约不会太熟悉这个名字。1955年马克西莫夫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油画训练班的指导教师从苏联来到北京。当时给他做翻译的佟景韩说,那时候中国没有真正的油画,只有一些不地道的土油画。这个训练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美术院校或机构,他们在这个班里进修两年后,马克西莫夫回国,这些学员就都成了中国油画教学的中坚,其中包括侯一民、靳尚谊、冯法祀。他们的创作和教学无不带着马氏的深刻痕迹。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许江翻着马可西莫夫的画册,好像翻阅小时候的日记,说这幅作品我临摹过……那天,所有人都翻起当年学画时从各种渠道结识的马克西莫夫,新一代的画家刘小东被认为是马氏的孙子辈,也是反马氏的一辈,但依然与他有扯不断的联系。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立即与蔡国强商量把这个展览迎回老家——中央美院。蔡国强的敏感和宽容的文化态度又多一例。
蔡国强说这个所谓的“收藏展”其实也是他的一个作品,延续着他以艺术史、艺术作品、艺术家等为题材的计划,曾经被指责为抄袭的《威尼斯的收租院》就是这计划的一例,《水墨写生表演》也是一例。这被他认为是一个造美术馆的计划,特别是与艺术相连的情感的梳理。他收藏马克西莫夫的作品开始于两年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路边画廊偶然发现一幅令他倍感熟悉的小画,他说虽然没看见过这幅画,但对马氏太熟悉了,所以一下就认出是他的作品。他买下了这第一张画,现在他已经收藏有91幅马氏油画,差不多是能够买到的马氏的大部分作品。
蔡国强自称他是个不坚定的人,容易左右东西摇摆,关键问题是艺术要好玩,要能让大家都跟着一起玩。所以他总能找到一种大家都接受的玩法,又能给出不同的经验。有时候是刺激的,比如在约翰内斯堡炸发电站。开始他只是提出炸废弃的厂房墙面,而市政府提出炸正在运行的发电车间岂不更有意义,他也就不客气地炸了。有时候又是温馨的,比如在磐城的《地平线》实施时,那里的市民提出,在他的作品燃烧的一分钟里,沿岸人家都关灯配合出更宁静悠远的效果。有时候则是能让人记起一段与生命相连的精神往事,比如《收租院》、50年代的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