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客: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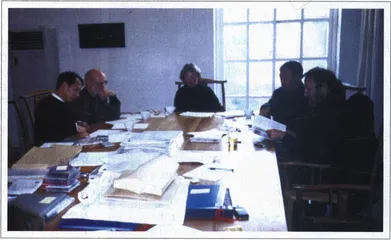
评委会讨论(左二为西客先生)(佚名摄)
瑞士人乌利·西客在某一个范围内被定义为“完整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人”。1979年西客初来中国,是作为瑞士一家企业的副总裁与中国建立一个合资企业,那是全世界第一个与中国合资的企业。对西客来说,这个职位就是个衔接人,联系瑞士和中国两边的工作。这样持续了好几年。1995年初到1998年底的4年时间,西客出任瑞士驻中国大使,让他有更集中的时间了解中国。从初来中国时候起,西客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而真正的收藏是在90年代。90年代初他收藏了第一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那是一位女艺术家的作品。从此后开始大范围有系统地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到现在,他已收藏了上千件。
2002年新年刚过,乌利·西客与他创立的“中国当代艺术奖金协会”的评委又开始评选这一届参加申请的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奖金协会”从1998年始,邀请居住在中国的、未满35岁的中国艺术家来申请这个奖金,由评委作出评选。最后被选出的艺术家会获得3000美元的奖金。评委会由来自中国的批评家、艺术家和来自国际的著名策展人及西客本人组成。2000年他们对有关项目作了一些调整,包括取消了申请艺术家的年龄限制。今年的评选是第三次。
每次的评选他们都收到上百份艺术家的申请,但依然有艺术家对是否参加评选犹豫不决。这不仅是表面讨论的对评选标准的疑问,还有一个因素是西客这位与中国当代艺术有着极深渊源的特殊人物。
1月20日,这次“中国当代艺术奖金”评审工作期间,西客先生接受了本刊专访。
生活周刊:你如何评价中国当代艺术?
西客:从反映中国现状和大家心态这点来说,中国有一个非常生动和活跃的艺术景象。有一个广泛、成熟的艺术基础,艺术家都有很好的技巧训练,虽然这不能保证有好的作品,但的确为出现好作品提供了条件。另外一个尤其引起我兴趣的原因是,从国际角度,中国的艺术并不是主流艺术。
生活周刊:主流艺术是什么样的呢?
西客:现在国际上的主流艺术基本是一种无法知道其原始语言的艺术,所谓原始语言就是用同样的方式解决同样问题。在全球化环境中,由于大家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就很容易被其他人所影响,所以国际上的潮流和时尚不断地更替。但中国当代艺术在一个很长的阶段中不是这个游戏的一个部分,好的艺术家发展了自己的语言。我的意思是说它曾经是很特殊的,现在却越来越明显地进入国际潮流,因为艺术家和策展人的来往交流越来越频繁。在这当中,中国艺术会损失一些品质,同时也会得到一些新的品质。所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好的或坏的作品,而不是中国的或外国的作品。
生活周刊:你收藏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西客:有一个原则,我希望收藏一个总体的规模、全面的看法,而不一定都是好的。在这个观念下,希望我收藏的作品能表现中国当代艺术的总体。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些作品更明确地表现了中国的现状,另一些作品则比较纯粹,它们并不一定表现为“中国的”艺术,而是无论放在何时何地都称得上是很好的作品。
生活周刊:除了收藏,你也在向世界推介这些作品?
西客: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看到“北约艺术”,但所有有名的策展人在他们的展览里都忽略了中国的艺术。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它是“北约艺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在我看来,中国有世界上一流的艺术家,理应得到一流的认可。所以我以各种方式向世界上有权力决定展览的人介绍中国艺术,我一直在说服这些人。
生活周刊:48届威尼斯双年展有那么多中国艺术家参加,占了参展艺术家总数的20%。当时有传说是你在幕后起了很重要作用?
西客:那只是我这种努力的一个结果,我就是要把中国艺术介绍给重要的展览和策展人。当塞曼(48、49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来中国考察后,跟我有同感。一个世界级展览,有世界级野心的活动,就一定得包括中国艺术。我现在认为并不是要有一个“中国艺术展”,而是不管做什么展览,有可能是关于月亮的或关于战争的,都应该有中国艺术家,他们对这些主题也会有他们的说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否则中国艺术就会一直被当作地域性、猎奇的对象。
生活周刊:这种状况得到改变了吗?
西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也需要那些对艺术有重要影响的人的广泛支持。更重要的是中国艺术家要有更好的作品。我只是打开门,最终是要作品自己说话。其实我只是若干人中之一,有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我不希望人们认为只有我在做。
生活周刊:你收藏中国古典艺术作品吗?
西客:我很尊重它,但我了解得很少。当我有机会时候都会去看,因为这也能帮助我了解当代艺术的来源。
生活周刊:你是否也收藏西方艺术作品?
西客:现在我已经停止了对其他艺术的收藏,因为能力有限,当然没有放弃对其他当代艺术的关注,因为这也同样有益于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对我来说,收藏中国当代艺术更重要,这不仅因为我熟悉它,也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系统地做这件事。在中国没有建立当代艺术的收藏系统,别的地方也没有。我没听说过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机构或收藏家来收藏自己的当代艺术,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状况。
生活周刊:你能估计一下你走访过多少中国艺术家吗?
西客:我走访过几百个艺术家的工作室,看他们的作品,和他们交谈,花了很多年时间。1979年以来我作为一个商人、作为一个外交官、作为一个对中国艺术有极大兴趣的人,走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我对中国的了解很广泛,当然不能说我就是个中国人,也不能说我懂得中国的所有事情,我知道有一个限度。但我也没碰到一个能了解中国所有事情的中国人。
生活周刊:你在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中,更感兴趣的是“艺术”,还是“中国”?
西客:很可能是中国。好的作品就像动力一样使我的头脑能够运转起来,更多地认识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当然我无法真正区分艺术和生活,因为艺术作品仅仅是一个产品,是一个表面的状态,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个表面进入现实。能使人深入到表面之后,这是一个好作品的基本素质。除了我作为商人和外交官的渠道,当代艺术给了我另一个渠道使我进入到我要了解的领域。最终我们的话题是中国。
王鲁炎与西客的交易
王鲁炎是星星画会成员,’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后他收藏了一批包括王广义、张培力在内的参展作品。后来其中的大部分转到西客手中。
王鲁炎说:“当时收藏它们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既没有人买,也不方便运回各自的家。十多年时间里,我一直设法推介这些作品,最终都因为出入海关的技术问题无法实现。最后一次努力是在高名潞在美国亚洲协会策划中国当代艺术回顾展的时候,作为回顾展一定要有这些作品,我当然非常想让这些作品有出头机会。于是我就开始怀疑我收藏这些东西的理由。”
“这时候我见到了西客。西客的收藏规模吓了我一跳,他真是一网打尽,而且差不多每个人都收三张以上。和他比较,我没有他的保存条件,那些作品在我那儿都开裂了,油彩也有剥落的。他的身份和影响力也能给这些作品提供更多的展出机会和被评论的机会。这时候我想,从国际化角度看,我过去一定要让这些作品留在中国的想法可能太狭隘了。最后我拿出大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后来不仅参加了高名潞的展览,并巡回了很多国家,展览结束回到西客的手中后他还请了专业人员修缮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