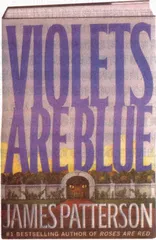畅销书与排行榜:《邂逅》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本期虽有七部新书上榜,但多属以情节取胜的惊险故事,大概是为了让人们在圣诞-新年假期的旅途和休闲中消遣的吧。
我们现在还要介绍的是一部未登榜的小说——纳丁·高迪玛(Nadin Gordimer)的新作:《邂逅》(The Pickup)。我们的译名虽然含有了无人正式介绍的偶然、随意结识的含义,却无法反映原文中那种尤指异性间的相互吸引——但还未必一见钟情的内涵。不难猜想,这是个爱情故事,而其非同一般的背景则是不同的文化传统、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带来的爱与忧、情与惑。
故事发生在南非。一开篇就有个象征性的“起兴”:身为汽车修理工的男主人公正钻在一辆小轿车(车主即是女主人公)下修理出了毛病的汽车:小轿车代表着西方现代文明及生活,而趴在公路上、“压”在汽车下的则是阿拉伯文明的化身。“在她抱歉的话音中,他的两条腿和下半身扭动着,从车下爬出,站了起来。他年纪很轻,身穿油腻的工作服,一双长臂下晃着两只油污的手。”这就是他们邂逅的场面。她是家庭富有、追求自由的南非白人姑娘;他则是来自北非某个穆斯林国家(未指名)的移民青年。她的轿车抛了锚,而他的老板的加油站(兼有修车业务)是最近的一个。她有自己的姓名和门第、社会关系和金钱,还有一帮在名称响亮的“洛杉矶咖啡馆”聚会的高谈阔论的年轻朋友;他却连个名字都没有——只知人们叫他“阿卜杜”,在南非举目无亲,而且没有合法的身分。这一对青年,朱莉和易卜拉欣(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实际是两种文化互相探求的符号,显然是著名观点“文明冲突”的人格化。作者的贡献在于,他并非简单地将两种文明带入一种可以认知的人性宽慰的地步,而是显示了二者间的相互不理解如何也与相互吸引有关。
他们相遇后,逐渐熟识了,成了恋人,然后便是现实的干预。易卜拉欣成为朱莉社交圈中的尴尬,他不声不响地坐在她那伙标榜自由的朋友们中间,听着他们酒后漫长的醉言醉语;朱莉却为易卜拉欣的“另类”着迷。他不能也不肯告诉她的有关自己家世的那些情况,她却以移情的心理和相当可爱的降尊纡贵的方式去填充。“他那修长、紧绷、挺拔的身材从他干活的阴湿的地方走出来,在阳光中勾出了他背影的轮廓,他漫步踱到水边,把一些隔夜的剩饭扔给鸭子——他脱颖而出的背景,她肯定只能错误地加以想象:棕榈树、骆驼、晾着毯子和铜器的街巷;阿拉伯的三角帆船上坐着男人们,她无法把他的面孔置于其中。不,他根本没有照片。
朱莉如同众多痛苦的西方人一样,也尖锐地意识到了她在幻想中也在俯就。这个男人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有着一双脏污的手,来自一个饱浸宗教和传统的地方,比起她自己那个有着令人发窘的政界交往和纳斯达克文件夹的富裕家庭来,他的故土具备了多得多的抽象意义。然而,作者笔锋所指,更在于易卜拉欣看待朱莉和她的背景时所明了的东西。当这一对青年终于连袂去拜访朱莉的家时,紧张的气氛到了极点。“她为她的父母感到惭愧;而他却以为她是为他而难堪。彼此都不知道对方。”
妙笔恰恰在于易卜拉欣崇敬朱莉感到惭愧的人。他对这种富有、逼人的白人国际文化敬畏有加。对那个圈子,朱莉巴不得要出来,他却渴望要进去。他在被介绍给朱莉的家庭时,觉得他们是“有意思的人”,“他们取得了成功”。作者并没有落入俗套,没有影射脱离全球经济的孤立和贫穷是一种文化的成就。易卜拉欣极其聪明,他对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深知自己来自何处,他全部生活的中心动力就是逃离那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去“世界所在的地方”。表象没能欺骗他,他看透了她那群有知识的城市青年是在装腔作势:“唉——皮肤白,年纪轻,并不聪明,却要穿上那身打扮,自认为可以掩饰贫富差别,就像我穿了这身工装就为了掩饰我的非法移民身分一样。”这话说得不够隐忍,却是一针见血。
整部小说记叙的就是这一对并不匹配的青年的故事:他们持续的误解,他们与那个争权夺利、矛盾丛生的外部世界交相作用。内心不断的惴惴和焦虑蚕食着易卜拉欣,他的无家可归,他的勃勃野心,他的同时存在的既是一个人又没有人的身份的状态……而朱莉却没有这一切烦恼,她只是吃腻了山珍海味想换换口味,尝点粗粮而已。她生活在什么都不缺的现实中,却追求非现实的抽象的幻想。
他们的爱情很快就被移民法缠住了。他面临着被递解出境的下场,想方设法(朱利还不得已去求了她的家人)也未见成功。她决定随他一起走。他们结了婚,来到北非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于是她充满浪漫,对他则犹如牢狱。他还是想走,这次是想去美国,叔父给他提供的修车场的高薪职位也被他拒绝了。家乡的许多现状,他都觉得丢脸,朱莉反倒迷上了那里的一切。既然他们找不到一块两人都满意的地方生活下去,他们的婚后生活也就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作者为他们找到的出路是性生活上谁也离不开谁。这诚然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