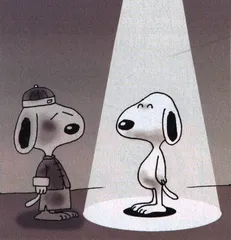生活圆桌(176)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东方月 邓迪 郭东 小昭)
倒计时60岁
东方月 图 谢峰
倒计时54321似乎总比12345来得富有紧迫感。12345后面,是可以加上一长串省略号的,54321则不然,眼看着直直地就往终点撞去。点火箭时,倒数到1便没有了任何退路。数字的无限性给了人们以错觉,以为生命的数字也可以是那样一路数将下去,三十立四十明,长长益善,至于究竟是数到哪一个时戛然而止,那就再说了。现在的说法是,20岁是半成品,30岁是成品,40精品,50极品,越活越辉煌。虽说终于意识到60是“废品”了,废品还有回收呢,随着绿色工程再加工再创造,重来一遍精品极品也不是没可能啊。人为自己的一生创造了无限乐观的前景,又为着那似乎永在未来的光景寸寸熬炼在眼前的光阴里。
居住在安达曼海的梅依群岛上的部族,自古保留着一种风俗:人一生下来就是60岁,以后每过一年就“年轻”一岁。按这个算法,50岁的人称为小孩,而两三岁的则是老人了。能够光荣活到1岁的寿星微乎其微。但如果真把“预定”的60年用完了,活到0岁,那就再添加10年,这回从10岁算起,等于他又出生一次。若这个年限也用完了,那就只好再次追加,期限也是10年,好比第三次出生。
《圣经》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其实谁都晓得日子如一声叹息,在病了的时候,在受伤的时候,或仅仅在安静的时候。只是我们常常以为挣扎了就会将有效期延长。——倒计时60岁,不知梅依人是从哪里来的这般智慧:当享用完两万多顿免费午餐后,任何人平等归零。以后的日子,是额外的,因而一切都是额外的:辛苦与享乐,发放与收回。
神人摩西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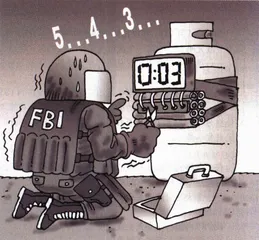
人人都可以当诗人
邓迪
上大学时,我突然有一天诗兴大发,写了首长诗,自己觉得还挺满意,于是跑到诗社社长那里,让他欣赏,以便从他嘴里听到一些鼓励和赞美的话。哪成想他看了几行便扔给我,“你这也叫诗?”我茫然地看着他,他说:“现代诗最重要的一点是,没一句人话。”我明白了,我这首诗人话太多,所以不成其为诗。那时候我还没怎么学会不说人话,所以写不好诗。
写诗的想法后来就忘在了一边,再后来诗人也不吃香了,虽然后来我已经学会了不说人话,但发现已用不上了。
前几天我又萌动了成为诗人的想法,这源于一个翻译软件,叫东方网译。平时看英文网站,觉得麻烦,就想着装了这个软件之后,会让自己方便一些。这个软件很好用,点一个按钮,几秒钟内,让你眼前的英文全部变成中文。但接下来我就傻了,眼前的汉字没有一个你不认识,但没有一句你能看明白。
诗可以创造一种语言,也可以破坏一种语言,但我还从来没见过像翻译软件这样把语言破坏得如此登峰造极。现在互联网普及了,但外语还没普及,对很多上网的人来说,大都面临语言障碍,看外国网站如看天书,于是一些翻译软件应运而生。我粗粗统计一下,目前国内翻译软件不下几十种,但没一个在说人话。于是我灵机一动,何不拿它翻译一首歌词看看。
“独自一个的人/出生石头/愿望邮票时间的尘土/他的手打击他的灵魂的火焰/系住绳到一棵树并且挂宇宙/吹寒冷直到笑的风/在人的耳朵扰乱的害怕/并且饲养它是恐怖的头/畏惧……死亡……在风中……/钢的人祈祷并且下跪/与发烧的燃烧火炬/在面临晚上时插入/拉片如果同情/吻了由无数的国王。”我发誓这段歌词我没有动一个字,这大概就是那个诗社社长说的“没一句人话”,按他的标准,这绝对是首好诗。不过这还不算什么,三年前我用一个翻译软件试着翻译了一下《泰坦尼克》中的那首歌“My Heart Will Go On”的歌名,结果是“我的红心大战将要继续”,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想象力的翻译。于是我又想,既然这些翻译软件都不说人话,那些程序员辛辛苦苦做出来,当翻译软件用实在是浪费。何不用其所长,当成诗歌创作软件,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当诗人了,说不定又能出来一堆李白杜甫。软件叫“东方网译”也不好,叫“东方诗译”更贴切。
记得几年前看报道说联合国某机构正在研发联合国官方语言对译系统,并且要把这个成果在2005年左右推广到互联网上,于是我开始担心,可别到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了诗人。
其实外语这个东西,学起来没有什么捷径,只有踏踏实实地学。而写诗则不然,就是几秒钟的事情,你看,有这么多的软件等着你变成诗人呢。
在火车上
郭东
他上了火车才发现,这趟车并不是他原本想要的那趟。晚上8点多,去上海,他想要的是终点为上海、第二天早上8点多就到的。而他现在坐上来的这趟,是去厦门的,他看了列车时刻表才发现,这趟车到上海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多,比预计的时间晚6个小时,他埋怨自己太粗心,订票的时候没有问清楚。
火车上总有奇怪的味道和相似的人群,那股味道不变,那些人的面貌也不变——老头儿,一个带孩子的妇女,一个喜欢喝酒的中年汉子,一个听随身听的学生,一个军人。他们似乎永远在旅行。
他的女朋友在上海,他们有半年多没见面了,他在北京。他记起老早以前看过的一篇小说叫《彼得·卡门青》,男主人公在乡下,爬到山巅的一处陡壁上,摘下一枝奇异的花,带着花坐火车回城里要献给心爱的女子。故事情节记不清了,大概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情绪,促使他选择坐火车而不是坐飞机去上海。他想,十多个小时并不算长,我们已经半年多没见面了,这十多个小时又算什么。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车窗外漆黑一片,青色的月亮在天上。他打电话告诉女朋友,他订错了车票,要晚几个小时才能到。他嘱咐女友好好睡觉。可他自己却睡不着觉,静静地站在车厢连接处,偷偷抽烟。还有个留着胡子的年轻人站在他对面看书,后来,那年轻人走开了。他女朋友打电话来说她睡不着,两个人就在电话里聊天,电话贴在耳朵上,左边的脸有些热。聊到没什么话好说了,他们就道晚安。
火车上鼾声一片,列车员都睡了,他的电话又响了。还是他的女朋友,还是睡不着,还要接着说,电话还剩下一格电,他等不及了,火车太慢了,他希望立刻飞到她身边。她说到脖子酸了才挂上电话。
后来是女朋友发来的短信息,“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他想,该不会把这首歌的歌词全都发过来吧。第二条很快来了:“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这首歌被简化成“嘀嘀”的声音传送千里,它的旋律在火车的车轮声中若隐若现。“我怕时间太快”,“我怕时间太慢”,他的电话里已经存下了全部歌词。
列车停站,他走下来,深夜的站台上空寂无人,一个大大的时钟呆板地表明现在的时间是凌晨3点,距离上海还要有11小时。他有些等不及了,忽然,他跃下站台,沿着铁路向前奔跑,他想要早一点再早一点。被他甩在后面的火车很快呼啸着从他身边掠过,带动的风吹得他好疼,那辆火车上还有他的行李,一个大大的旅行包,包里有他要送给女朋友的礼物,不知道是什么,但绝不是山上的花。
亚细亚的史诺比
小昭 图 谢峰
早年间看香港电影,周润发们老是去泰国或者越南或者马来西亚菲律宾,搞些非法的事儿。这回看《全职杀手》,反町隆史风头出大了,亚洲城市杀了个遍——有史诺比为证。这个亚洲第一杀手,要攒足一套四十个史诺比,送给林熙蕾,那个给他打扫卫生的年轻女人、替死鬼、情人。
认得了几个香港朋友之后,我就总有VCD可看了。看的都算是香港电影,但是不时地也出些常盘贵子藤原纪香什么的。最近亚洲很热闹,竹野内丰陈慧琳,木村拓哉王家卫,金喜善张艺谋,申贤俊钟丽缇,美人大师,合作的合作,绯闻的绯闻,恍恍惚惚好像一家人,热热闹闹好像世界的中心。
我们这里有个学视觉艺术的家伙,总要拍些短片,是作业。有一个周末,找到我,要我穿了黑衣服在街上走。我就在街上走。我明白他的意思,一遍就拍成了。拍完了一起吃饭,难免就要谈艺术,我就叉开话题说别的。不过又是电影。我说《东京物语》挺好的,他说他没看过。我不敢指望他能理解香港烂片的妙处,只能试着提起一些,据说得了奖得了认同的,伊朗韩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电影,他只看过两部。这个比利时人还算是个亚洲迷,但也无非是这样。我发现我的世界中心远不是世界的中心。我发现原来我很不“西化”,不喜欢也没看过几部他们欧洲美国的电影。搜肠刮肚也只能言不由衷地说说红白蓝双生花罗拉快跑。
我们的片子拍出来我看见了自己。我好像从来没见过自己似的。穿个黑衣服在伦敦的街上走,时缓时急。放松闲逛的步调里,我好几次不自知地深深叹气。一叹气,肩膀都跟着往起提。肩膀上头是一张眉头微皱的脸,一张焦虑的亚洲的脸。
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个人要给我剪头发。是一个韩国人,她抹个深褐色的嘴唇,所以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她还画着莹莹闪光的金色眼皮儿,涂得干干净净一张平坦的脸。她要给我剪头发。免费的!免费的!她说了好几遍。我撩了撩自己的头发觉得剪剪也无妨,反正不会更丑了。我说,那就剪吧,去哪里。可是小姑娘又说要等到两个小时之后,那工作台才归她用。我就走了。
那天我正伤风,回去很早就睡了。睡觉做噩梦就醒了。醒了的时候静悄悄,拉开窗帘院子里正在下雨,水银灯照着满世界的金针。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就想起了今天有人要给我剪头发。拉上窗帘打开灯,见得镜子中一张浮肿呆滞的脸。我操起剪刀喀嚓一声,就没了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