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76)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吴小迪 魏文彪 聂武钢 马廷刚 曹丽娟 杜比 张无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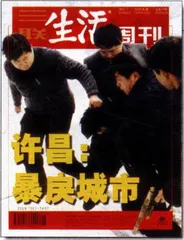
“一群生活在暴力阴影之下的人民是不是会长久的被打败?暴力、权力和经济到底以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运行?没有人愿意看到大大小小的梁三们成长和壮大,问题是,我们用什么去保卫社会?”
北京吴小迪
公益短信且慢登陆手机
北京魏文彪
元月2日上午开始,陆续有北京移动的用户收到一条来自首都精神文明办与北京移动的“公益短信”,短信的内容是:欢迎参与“争做文明北京人”活动,提倡文明乘车、遵守交规、爱护环境、尊老爱幼、杜绝“京骂”。据了解,这是公益信息第一次以短信息的形式大规模地出现在北京人的手机上,北京移动的400万用户在这两天内都陆续收到这条短信。
精神文明办提供“公益短信”内容,移动公司负责将短信发到各用户手机上去,这就等于是移动公司向精神文明办提供了手机用户的个人资料。但未经得用户同意,也不是配合司法调查,移动公司根本无权向他人提供用户的个人资料。
更为重要的是,手机信息通道实际属于用户的私人空间范畴,严格来讲,进入该空间都必须得到它的所有者(或称目前所有者)许可。移动公司如不是出于业务上的必要,未经用户授权也无权占用用户的个人信息资源。移动公司未经许可向用户发送短信就是擅入用户私人信息空间,是不尊重用户权利的表现。移动公司未经许可往用户手机上发“公益短信”是种自我授权、单向“行使权利”行为,说明其骨子里并不承认双方权利的平等性,还未真正把自己放在对等的“纯企业”层面上。
对公众进行公德教育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但公益信息宜通过广告墙、电视、广播等公共信息资源来发布,如要进入私人信息空间,就必须征求私人信息空间所有者的意见。社会必须倾听来自个体的意见,充分尊重个体的自身权利。
不是想禁就能禁的
西安聂武钢
2002年1月3日,西安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华商报》头版头条报道:“为确保‘春运’安全,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出台预防重特大事故的安全管理措施,规定凡定员15座以上的长途客运夜班车辆,晚11时至次日凌晨6时不得载客行使。”
如此规定,怕又是一例“利己主义”的样板,作为一个曾做过一年多警察的法学硕士,我知道每年春节期间恶性事故给各方面带来的灾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类似规定出台的主要原因。比如西安市,在2001年就先后取缔了游戏厅、录像厅,如今,又闹出了这么一场禁运运动,而以后,不知道还会不会取缔私房出租、废品回收等行业,因为这些行业容易导致不安全因素,也是公安管理的难点。
可是,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忽视了,这项规定还涉及到司机和乘客的利益。作为司机,只要他合法办有相关证照,交纳了相关费用,行驶时不违章,那么他就享有营运的权利。而乘客在春运期间,是否也应该被剥夺乘坐夜间大客的权利呢?从法理学角度,法规的制定是为了使社会关系的各方主体之权利在某一特定时期达到尽可能的合理状态,也就是说法规在现代社会是为了让各方面的权利达到平衡,而不是像封建社会那样用来“治民”,纯粹成为一种统治治理。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是公安交警部门用来治理交通的权威性文献,全文93条对深夜行驶没有作任何禁止性规定,第89条也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也就是说,《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只有省级以上的政府才可以对其内容做些补充规定。
“最低消费”该谁买单?
山东马廷刚
福建省的城市居民在新年到来之际收了一份最好的礼物:正式停止收取每户每月5吨自来水基本水费。
取消最低收费是深得民心之举,因为“物价部门当初在定价时就已考虑到水、电、煤气的正常损耗,也就是说水价、电价、煤气价格均包含了损耗部分”,这就从根本上驳斥了垄断行业关于最低消费是补偿损耗的说法。因此,许多人认为最低收费就是重复收费。“这三个垄断行业实行的‘最低消费’由来已久,最长的甚至延续了22年”,从而“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这现象又岂仅仅是在福建?“由来已久”乃至“延续了22年”,它们会侵害了消费者多少利益?这个数字不算则已,一算就会吓人一跳。有关部门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取消”了事,也没见到他们给用户道歉的报道,更别说给用户精神和物质的赔偿了。该不该给用户以精神和物质的赔偿?赔偿时该不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双倍赔偿?
就业何需讲“出身”
成都曹丽娟
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办公室最近发布文件,对2002年进沪就业大学生的所属高校作出严格规定,根据这一规定,被许可进入上海就业的外地毕业的大学生所属院校,除北京、江苏等少数省市外,80%的省区市符合条件的学校数目不超过10所,海南、宁夏分别只有一所高校榜上有名。就业指导办一位官员称,此举是为了适应加入WTO后上进一步构建人才高地的战略需求,把人才从“留”变为“流”。尽管有关官员声明该规定并不是“一刀切”的硬性规定,但就业也需看“出身”,外地大学生不能随便进沪就业的性质,在政策上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
不难看出,就业也需讲“出身”的规定,对于外地大学生在沪求职,以及沪上企业的用人,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一切都得遵照政府定下的框框办事。本来,大学生找工作是个人的事,企业如何用人是企业的事,全然没有政府在旁边说三道四的份。而这回有关方面却公开立规定矩,这不行那不行地要讲“出身”,使就业市场的供需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受干预、遭约束,由此让人看出政府干预就业市场的浓浓色彩。
对于这项就业讲“出身”的规定,有关方面作出的解释是为了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可是WTO自始至终所全力维护的公平、公正地运作市场的原则,在这里究竟能看到多少踪影呢?相反,由政府的行政性决策,武断干预市场,这又与WTO所规定的非歧视性和政府不得过多干预市场的原则相去甚远。
一次吵架
北京杜比
元旦时候,我去北京的东方新天地逛商场,遇到一次吵架事件。那是在宝马专卖店,这个店不是卖宝马车,而是卖宝马牌的衣服和饰品。有个小伙子,十五六岁的样子,要在店外照相,他的背景是玻璃墙内的一辆宝马自行车,给他拍照的大概是他母亲。店员看见这母子俩要照相就出来劝阻,说“这里不能照相”。
母亲说:“哪里有规定说不许照相了?你拿出条文来,要不我就去告你。”这个商场里好多地方可以照相,奥迪汽车的展厅里就有不少人和名车合影。店员嘴笨,喃喃地说:“我们这里就是不让照。”她显然不会说“知识产权”这个名词,名牌商店的陈设也是要保护的“知识产权”。而那位母亲显然不知道法律还真的不一定让你们拍照。那个小伙子火气很冲,说:“不就14万吗?有什么呀。照!”他固执地要站在那辆价值14万的自行车前,店里的另一个店员没出来吵架,她迅速把那辆自行车搬下来,要移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没有看见这次吵架是如何收场的。
断腕
北京张无谋
最讨厌的文艺工作者还不是那些本身智力有问题的,而是那些智力不错、但对受众的智力表示轻蔑的家伙。
电影导演冯小刚可以列入后者行列。他拍的《大腕》被说成是2001年中国最好的电影,原因是人家请了外国人演、合作方之一是哥伦比亚公司,票房成绩好等等。最无聊的一篇吹捧文章说“冯小刚就是泰勒”——泰勒就是电影里那个外国导演,他在片中说,如果没有好的想法,拍出来的东西就是垃圾,他因此陷入了创作的困境。说实话,《大腕》本身就是一堆垃圾。我花了30块钱为它的票房纪录做贡献,在电影院里也哈哈傻笑了几次,但要我说这是中国最好的电影,我决不答应。
冯小刚导演之所以敢牛哄哄的,就在商业的成功。如今谁在商业上成功了,就有一股劲,让人说不得,还不服不行。这样的风气在演艺圈里盛行,那就是好莱坞的名言——“谈艺术请到走廊里”。
(本栏编辑:吴晓东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