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往事的回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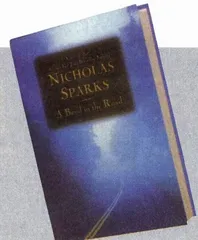
一如既往,感恩节之后,美国的书籍市场又活跃了起来,准备圣诞节前的大销售。本期上榜新书多达10部,几乎挤掉了原有的畅销小说。我们要在这里为大家介绍的却是另一部。
这位作家名叫瑟巴尔德(W.G.Sebald),他于1944年生于德国,近30年来一直旅居英国,在东英吉利任教。他在过去10年中所写的作品,直到近5年才有英译本出现,其中包括《移民们》(The Emigrants,1997)、《土星光环》(The Rings of Saturn,1998)、《晕眩》(Vertigo,2000,原书出版时间更早),及目前这部最新的长篇小说《奥斯塔利茨》(Austerlitz)。他的努力始终是一种麻烦重重却又十分宽广的发现,犹如某种存在,我们感觉到了并且发掘出来了,但还不能对其定性。可以海王星为例,当年天文学家也看不到,只是通过其相邻的天王星绕太阳运转轨道的偏转,才计算出并最终找到了它。
瑟巴尔德笔下的人物都是因其以往的经历而发生了偏转。他们要么屈从于疾病或倒霉,要么摆脱不掉噩梦的纠缠,从而与人群格外疏远。这使我们想到了普鲁斯特,并非把他俩归于一类或列在一级,而是加以对比。瑟巴尔德的作品也有类似的优美细节和微妙漂掠的交织,不过他那勾人回忆往事的“马德琳蛋糕”却是有毒的。他的作品可以冠以《绝非往事的回忆》这样一个总标题。我们还可以将他和普莱摩·利维一比,后者是大屠杀的首席发言人,有了他的揭露,阿多诺才有了那句名言:“大屠杀之后便不可能有艺术了。”利维写的是事情本身,及其人道与非人道的维度,而瑟巴尔德所写的却是逃脱了灾难的人所受到的沾染,通过记忆、搜寻、梦境与创造的天衣无缝的结合,把那场恐怖折射出来,从而使其效果辐射到当今甚至回溯到200年前,并无声无息地滴落到未来。
《移民们》是人们首次遭遇瑟巴尔德那个凄凉又魔幻的世界。书中展示了一些由于种种原因逃脱了大屠杀的犹太人却或迟或早仍发现他们终归是牺牲品。其中一人是英国医生,他的犹太父母在纳粹占领立陶宛之前离开了那里,但随着他长大,他平日的生活离他而去,而历史上错过的东西却返回来拥到了他身边。于是他退隐并最终自杀。另一个人是德国人,祖先虽有犹太血统,但并未阻止他在二战中参军报效祖国。他自幼迷恋铁轨,战后他得知了铁路曾运送犹太死囚,结果便卧轨去追随他们了。在第三个故事中,时间返回到20世纪初。叙述者的叔祖安勃罗斯为一个过着挥霍奢靡生活的花花公子工作,他们一起去游览耶路撒冷,后来一个抑郁,一个狂躁,预示着上个世纪的病症。后来二人双双死于精神病院。
《土星光环》的叙述人病愈后沿东英吉利平坦的海岸步行了数周,看到了种种污染的后果和凋蔽的现象,“空荡的巨大力量”,他还反思了19世纪的战争和殖民征服——尤其是利奥波德二世治下对比(利时)属刚果犯下的残暴罪行——这其实是对非洲黑人的大屠杀。与《移民们》相比,《土星光环》更阴沉、更缓慢,也更开阔,因此而独具异彩,极有震慑力。加之每一两页就有一幅来自被遗忘的相册中的档案式的照片,与文字交相辉映,更令人掩卷难忘。
目前这部新作的同名主人公杰奎斯·奥斯塔利茨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家犹太人的儿子,德寇入侵后4岁的他被送到英国。他在威尔士长大,以为自己的名姓是达菲德·埃利阿斯。他进入牛津大学,后来成为一名建筑史专家。直到他年过50,才知道是大屠杀夺取了他父母的性命。他不得不面对那些可怕的记忆,成了一个备受折磨的人,总想着应该到远隔时间的另一面,去找那些地方和那些与自己有关联的人。
小说主要由主人公和叙述人之间相距20年之遥的两次邂逅组成。在20世纪60年代末,奥斯塔利茨在显然回避一切个人见解的前提下,拿出了一些对欧洲建筑的广泛观察与探讨。在如安特卫普中央车站那样的巨型建筑物中,他看到了力量、傲慢和残忍,那是19世纪传给20世纪的遗产。他如同盲人一般摸索那些建筑物的含义;他勾出了那些建筑物在希特勒劫掠下的顶峰。20年后,他才说:“事实上,资产阶级时期的建筑和文明的全部历史,也就是我研究的课题,指向了大灾难事件发生之前已然投下的暗影。”
在那20年中,那个大灾难的暗影实际上也一直追随着书中这位主人公。他不仅饱尝了人间的沧桑沉浮(这并不是他个人的独特遭遇,也是叙事人的经历,这种“同病相怜”恰恰暗示了世事对个人命运影响的普遍性),而且已经从了解他的过去的那个地狱转向了发掘那段历史的炼狱式的折磨。主人公在谈及自己的成长、成就的同时,无法不涉及他自己精神上的坍塌。
统观瑟巴尔德的作品,虽然以甚嚣尘上(笔者选用这个词是有感于二战中我国3500万同胞的死难由于种种原因而为人淡忘或根本不知)的犹太人遭大屠杀为主线,却揭示了战争及残暴对人性的戕害——连未曾亲历的人都逃脱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