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娃之夫》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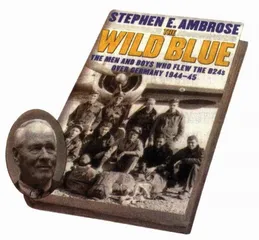
近来美国人似乎喜欢阅读叙述家史的书,这是一种在不太晴朗顺利的环境中带有垂暮心态的选择。我们现在介绍的这部新书作者是瑞克·布莱格,是《纽约时报》的地方记者,曾于1996年因一篇特写而获普利策奖。
真正描写南方劳工阶级生活的作家寥寥无几。詹姆斯·阿吉(James Agee)曾写过一部《咱们现在来歌颂名人们吧》(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但那是从局外人的角度接近他们的生活的。而瑞克此次却是从内部写其文化。他所讲述的是他自己的家庭,书中的人都是自己在说话,那种典型的场景和人物个性化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读者。
瑞克此前曾写过一部回忆作品《除去呼叫全都过去了》(All Over but the Shouting),是献给独立支撑全家的母亲的。布莱格一家属于地道的又穷又脏的劳动者家庭,住在亚拉巴马州东北部阿巴拉契亚山麓的小丘地带。瑞克先是摆脱了艰苦的生活与劳动,后来便投身写作,把他的家人和乡亲当作了书中的人物。此次新作《爱娃之夫》写的就是他从未谋面的外祖父查理·班德拉姆,“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没有留下什么,既没有头衔也没有财产,甚至在阁楼上都没有留下什么信件。他身后留下的只有故事,在家人中凭记忆口口相传。你如果可能,只消把这些故事写到新纸上就成了”。
查理·班德拉姆健谈而善讲故事,他这种天赋显然传给了子孙们:“查理·班德拉姆长着浓密的淡黄色头发、蓝眼睛——蓝得就像有钱女人手镯上的宝石。他的面孔和身体都是瘦骨嶙峋,但他扬着下巴,口气傲慢,如同他有多少钱似的,其实他从来都没钱。”查理的生活中有很多徒手格斗、空手抓松鼠等故事:他身上集合了当地文化的那种情操、独立和恐惧。那里人的们具备深沉、往往难以言传的感情和忠诚,他们自力更生而且自尊自重,但他们对外界的有钱有势的人,尤其是变化,却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这种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特色对读者陌生又新颖。
班德拉姆一家本是胡格诺派教徒(是16、17世纪德国加尔文教派的称谓,如英国称之为清教徒),早在18世纪就来到美洲,并一路辗转漂泊到南方。本书将班德拉姆一家耕耘与伐木、拼搏与爱恋、跳舞与饮酒的整个世界——从一处到另一处,都写得栩栩如生。他们以剧烈的舞蹈、坚强和执拗的性格而著称。瑞克的外曾祖父吉米·吉姆·班德拉姆以“雷霆之怒”而为人称道,曾在一次格斗中咬下一个人的指头。
但班德拉姆家的妇女就不同了。在艰难的岁月里,她们的孩子们不吃完,她们便不肯吃东西。爱娃脾气暴躁、伶牙利齿,但更出色的是干活和护佑子女。在一年数度的迁徙中,她都要背着几件宝贝:一本家用《圣经》、她搜集的一些廉价袖珍书籍和一盏阅读亚特兰大报纸的煤油灯。
查理是这样一个人:找到活儿干的时候,就修房、挖井打短工,没活儿干的时候,就捕鱼狩猎来养家糊口。闲下来则游逛、讲故事、和子孙玩耍。他不识字,要靠妻子为他读报。他们一家主要吃玉米和斑豆,有奶牛时才喝得到牛奶。穷人的晚餐通常是玉米饼和牛奶。
查理年轻时被称作“吹风裤子”,因为他的工装裤上满是窟窿,也许还因为他主要吃豆子。他虽骨瘦如柴,却坚强似铁。书中最生动的细节是对他的手的描绘:“那双手十分动人。垂在瘦臂的终端,如同棒球的垒垫,那双手之大,普通人的手握进去就看不见了。手掌上的老茧形成一道横贯的高棱,全掌粗糙得像是鲨鱼皮。上面的油污像是刺进去的,染黑了皮肤,黝黑的脏东西涂污了指甲下的嫩肉,已经再也洗不掉了。”
查理和家中的其他男人一样也喜欢喝酒,但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喝。喝醉了也不胡闹,只是特别兴奋,光想唱歌。他也酿造少量私酒,供自己喝,有时也卖。查理有他自己严格的道德标准。他和爱娃夫妻俩费尽力气让一个孩子免于夭折,在大萧条时期总共搬了21次家。他们还从河里救出了一个流民,收养了好几年。
该书的一个亮点是烹饪。布莱格详细描写了如何制作玉米饼、斑豆、小鲨鱼、冰茶。作者还描述了他母亲玛格丽特儿时初尝热狗的情景:“用蜡纸包装,面包松软热乎,生洋葱、稍辣的肉和辣椒的气味充满车厢,一路上她肚子撑得饱饱的,颊上沾着芥末。”
爱娃是个虔诚的教徒,而查理却不去教堂。他把妻女们送进教堂后,便坐在外面等候。他一生艰苦,却热爱生活和自由。虽然喜欢饮酒,却也没有改变他善良的本性。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情大变,连阿巴拉契亚山区也不例外。查理感到不适应了。“他更习惯于以往的山川,而不喜欢此时此地。新修的黑亮路面的高速公路,从雾锁的丘陵地通向四面八方的草原和低地,标志着那一地区的未来,查理本人和他的生活方式已成为历史了。”
书中最奇特的故事是查理外出捕鱼时遇到洪水,因衣着破烂、身上无钱而被当作流民拘留了两星期,家人也不知他的下落。这一插曲成了他的时代已经逝去的象征。
本书内容朴实,却令人掩卷深思,回味无穷。 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