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和潘石屹谈共产主义红色与商人道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吴晓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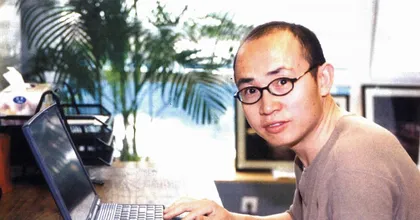
记者:您本人和您的产品经常成为新闻关注的热点,这种关注和认同给了您作出这种行为的基础支持。你曾经把和客户的关系比作婚姻关系,如果“过不下去了,那就离婚吧”。据说有个国外客户有可能退房的理由是不喜欢共产主义的红色,这也能构成离婚的理由吗?
潘石屹:其实,离婚纯粹是个个人感觉问题,有时候你很难讲出什么非常确切的理由。SOHO现代城要开始入住了,我在想,这些房子基本上是一年半以前就销售出去了,从期房到现房,肯定有一个差异。有的客户看到现房可能觉得不满意,那么可不可以退掉呢?1999年我们就提出一个“无理由退房”,就是给客户一个出口。我们二号楼实行无理由退房的时候是退还房款加上活期存款利息。但在现代城房价已经有了一定升值的前提下,整个客户的反应,是发展商占了便宜。所以我们提出今天这样一个带回报的无理由退房,加上年息10%,期限是20天。SOHO10月24日开始入住,我们预计大概有三到四套会退出来。其中一套是因为色彩,是一个芬兰住户,认为红色是共产主义,跟我说了颜色的问题。
我们在公寓部分的无理由退房中发现两个问题:一,给客户考虑的时间太短,他们购买的房子毕竟是价值上百万的商品,应当有充分时间去决策。二,许多客户反映他们购买的房子升值了很多,如果只退房款,升值部分又全部属于开发商了,不够公平。我想,客户买房本身就是一种投资行为,他们给予我们支持的同时也承担了风险。他们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应当把我们房子升值了的一部分利益拿出来回报给当初支持我们的客户,所以我让财务部门进行了测算,把房款连同回报一同返还给客户,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想法。
记:应该说,您的成功和您与公众建立了非常良好的沟通有很大关系。我的印象是,两年前您和邓智仁之间的矛盾和纠纷造成了您与公众交流的第一个巅峰期。现在看来,是不是可以说当时的事件与其说是一场危机,倒不如说是一个机会?
潘: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试图隐瞒事实而不让公众知道是愚蠢的想法。我想是克林顿、莱文斯基事件给我感触很大,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变了。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也好美国也好,都要允许媒体说话。当时全世界媒体都在说克林顿与莱文斯基,恨不得全世界的人能把克林顿的裤子扒了。但他尽管脸上很憔悴,还得出来参加晚会,会晤外国记者,这压力有多大!这说明人还要有专业化的精神,还得强大;说明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公开化的社会,不要再怕面对什么事。媒体公开与社会的公开,实际形成了一个良性监督机制。有人把那一段时间我对媒体的态度称作危机公关,其实我只是对媒体曝光采取了配合的姿态。因为我感觉到,你从事的这个行业和你的工作要给别人带来价值,你所提供的产品与你的经营理念就要经得起别人的检验,否则你这个人与你干的事都不可能长久。
记:有人说过,客户和发展商之间利益的冲突是必然的和无法调和的,做发展商赚钱会不会影响你的道德形象?
潘:只要你做出足够好的产品,情况一定不会这样,比如说我们的带回报无理由退房,客户和我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怎么会无法调和呢?至于说到道德形象,商人不是普通人,股东把钱给他,客户把信任给他,他惟一该做的就是赚钱、创造财富。不让股东、客户失望,也不让跟着他打天下的人失望。如果他连起码的商人准则都做不到,何谈道德!说严重点这就是犯罪。况且,在市场经济下,资本是会说话的,如果你业绩不好,你连做商人的资格都会失去,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作为商人,是要创造财富而不是浪费财富,也就是一定要赚钱,赚了钱才可以交税,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推动世界的发展。至于我们现有的道德观念也要在市场经济下有所改变,传统的道德观念是自给自足,人们羞于谈钱。前些天在云南的一个地方,看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人卖东西,人却站得远远的,不好意思。买东西的人也很有意思,把钱往筐里一扔,拿起东西就走,好像做贼一样。这就是受传统封建观念的影响,耻于谈钱。而现在的道德观念是只要在阳光下的交易就都是道德的,而且还应该建立一个社会机制,把那些不赚钱的商人都淘汰出去,让更优秀的商人在激烈的竞争中赚更多的钱,这才是市场规律。在赚钱过程中,商人会运用一些方法,采取一些手段,人们总是将这些归为“奸商”做法。其实商人做事是要有原则的,法制是第一位的。我个人认为,只要不违法,商人所做的一切就都是道德的,并没有错。人家给了你10平方米的舞台,你不敢往边上走,只在2平方米的舞台上表演,你能表演好吗?当然商人是特定的名词,如果你是教师是公务员,赚钱就不该是第一位的。
记:您说过,房地产这个巨大的行业和家电、手机等行业相比,是向市场化过渡最慢的行业,一直到今天,很多做法也没有遵循市场经济的法则。那么,您的很多做法是不是要为房地产业寻找市场化操作的出口?
潘:我想是这样,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要做你认为是对的和有用的事情。1987年4月我从机关辞职下海。当时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这个局有4万多人,光机关干部就有一千多人。我辞职是因为那是一个开放而令人激动的年代,国家领导人的言行,比如当时胡耀邦穿一身西服都能给人的观念很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我慢慢觉得,我在机关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没用的。可能我们机关只有一个部门,就是输油管理的调度室有用。我感觉到随着发展,各种多余的、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环节,迟早会被淘汰掉的。我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我走回头路,只有一个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我说,计划经济没出息,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这是我下海的惟一支持人。
我说我最感激的一个人是邓小平,一是因为要没有他,我父亲就不会平反,我也不可能离开甘肃,我们现在还可能在受苦受穷。二是要没有他的南巡讲话,海南不可能发展,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
记:出身贫苦的甘肃农村而有今天的成就是很多人一直喜欢探究的话题,您个人似乎也很喜欢路遥小说里表现的来自农村的质朴、坚韧和智慧。房地产行业是最代表城市文明的产品,如何解决这种“文明的冲突”?
潘:如果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思考这种冲突的话,有的时候会发现这种对立并非那么绝对。比如说房子的功能,我们会认为农村的房子显然是落后和不适宜居住的,在农业文明里,一所房子要承担居住、储藏、饲养甚至种植等非常多的功能,到了工业社会,社会分工非常明晰,房子的功能也区分的十分清楚,需要人们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和环境、按照特定的程序组织生产和生活,但是在现在的信息社会,这样的组织结构显然是有问题的。为了更有效的利用资源和空间,我们会反过来思考最原始的居住场所的多功能化是不是对今天的居住设计有实际的意义?我们从农村过来时老看见城市的先进,深入城市后我们也了解到城市里也有落后和先进之分。我们把最前卫的、最先进的东西带到城市里来,例如SOHO这样的概念,例如为中国建筑带来“极少主义”,带来色彩,等等这样的一个个新的人文观念的变化,成为这个城市,这个行业的领导者。至于我个人最本质的东西,很难被改变。就像出炉一个毛坯,经过了机床、洗床、钻床加工过,可毛坯的最基本的形式还是不能改变的。只是城市和工业文明的熏陶,在某一部分把它做得更精致一些。 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