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教育权追求最大限度的平等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雷静)

严志刚 摄/《新周刊》供图
“社会对这一事件的超强度关注,已使得呼唤教育平等的声音传扬出去。”3名学生的代理律师李强对“无果而终”这样解释:据说教育部已有所触动,起诉的目的实际已经达到。
尽管这一事件在外界看来“更像是一个策划”,但它直接传递了一个让教育部不得不正视的信息:高考分数线的地区差异带来的教育不公,已经引起了公众最密集的关注。从关注到最终的起诉,无疑是一种接近极端的表现。
从1994年开始,就有外地考生通过在北京“买户口”来获取高考资格的报道。出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上的便利,他们花钱买来了平等。相比之下,在90年代末引起不小反响的《中国高考报告》一书中披露的相关细节更耐人寻味:曾有一些外地落榜生,专门在高校云集的中关村一带对北京籍市民或京籍大学生实施犯罪活动。他们被抓获后的反应令警察惊讶:“你们北京人让我们上不了大学”,“我恨你们北京人”。
“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分布上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计划经济的产物”,“国家在北京等中心城市和地区实行优先发展教育并用教育保障就业政策的结果”,这是教育部和学者们在分析北京与外地分数线差异时的惯常表述。
虽然现在看来这些说法都很牵强,但这一明显的差异仍然明明白白地存在着。
60多年前的《联合国人权宣言》这样界定教育权利平等:“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它同时很明确地指出,“高等教育的入学,应该根据才能对所有人完全平等地开放”。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学者韩民在谈到中国的教育不公时,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基础教育上,比如存在城乡差异、教学质量差异等等。但就社会舆论来看,公众的兴奋点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不公平上——因为它更直接地决定着一个人的前途。

取得这一权利,必须支付相应的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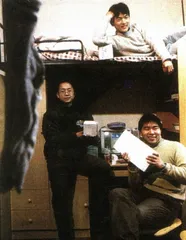
同学就是同等?
人口基数使中国每年有三四百万高中生想挤进大学的门槛,这决定着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像美国一样“宽进严出”,但在既定条件下追求相对的平等,理应成为政府的目标。
在原国家教委学生司官员赵宏亮看来,整个90年代,1994年至1997年进行的高校招生并轨制度改革,就是追求这一目标的一个典范。
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国家任务和调节性(如委托培养和自费生)招生的双轨制,使一些分数相对较低的考生自费上了大学,一些分数相对较高的考生却因经济原因上不了大学,两条分数线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同一班级中新生高考成绩相差200分,这在90年代初期并构不成新闻。
“这显然违背了教育公平性原则。”赵宏亮认为,国家将“双轨合一”,均收取一定费用,正好可解决这一问题。
但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这次改革的核心在于“上大学要收费了”。在此之前,公费生上大学是免费的,有些专业(如师范)每月还能拿到助学金,往往能够一个月的吃喝。
青年经济学者董志强因此对收费作了这样一个更学术化的表述:“高等教育是一种产品。”招生并轨后,国家保证公民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实际上只是保证公民有通过竞争(主要是考试)购买高等教育的权利,“而真正取得消费这一产品的权利,必须以支付相应的价格为前提”。缘于经济基础上的差异,“特困生”成为这次改革的附产品。紧跟其后的,是高校收费的直线上涨。这种趋势在1999年几乎达到了一个极点。
在这一年,高校招生从上一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6万人,增幅45%。毫无疑问,对扩招的48万名学生来说,国家给了他们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但要为这个机会“买单”,他们支付的价格也不菲——在这一年,个别专业的年学费高达1万元。
“这股热潮中,许多地方高校特设收高学费的二级学院,搞所谓‘一校两制’。”让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李宝元更加惊讶的是,他所知道的浙江十多所高校,用降分数线的办法扩招高收费生,学费高达每年15000元。
到2001年,教育部不得不出面以“统一定价”来制止高校收费飙升的势头:医学类每个学生每年4000元,文史类3400元,外语类4800元,艺术类8000元。各高校最多可上浮10%。
即便执行这一收费标准,专家们也认为这可能高估了教育成本。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学生现阶段负担的成本只能是教育成本的1/4或1/3。
“如果想收5000元,就说自己的成本是20000元。”上海市教科院的蒋鸣和认为,“现在出现了一种普遍高估成本的风气。”而据江苏省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苏金康掌握的资料,权威机构对大学教育成本的测算为每个学生每年7000到8000元。从学费占人均GDP的比例来看,武汉理工大学张道中教授认为,当前高校学费明显偏高。在加拿大,大学学费是1700美元左右,占人均GDP的7.2%。我国目前人均GDP约6500元人民币,学费按3000元算即占人均GDP的46.15%。
张道中对高校收费研究的结果是,高校每年学费3000元即有20%左右的学生及家庭承受不了而举债上学;如果学费提高到5000元,无力承担学费的家庭将大幅度增加。如果按每年1万元收费,将会使80%以上的学生无法承受。
“如果在制定高校收费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居民的承受能力,将产生新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新说,政府最大的责任是保证社会相对公正,“如果政府减少对高校的投入,增加学费,从起点上就没有做到公平。”
事实上,曾经有一份报告指出:1997年高校学费标准上提10%后,近11%的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学者韩民将中国教育不公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的财力非常有限”。他列举了一对可供比较的数据:在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以上,而我国的教育经费始终在2%左右徘徊。
如果说招生并轨、扩招所孕育的起点不公平可以通过政府的财力来解决的话,教育腐败所产生的不公却很难靠投入来解决。而这更让人觉得可怕。
“‘条子生’、‘缴费生’、‘学校利益集团’等等就是这种腐败的集中体现。”在北京理工大高教所杨东平研究员看来,最近几年,教育腐败开始加剧了教育不公,“这种通过权力和金钱来攫取短缺的教育资源,破坏了整个教育体制的公平。”
这种可能“破坏体制的不公”,在今年8月17日第一次完全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尽管上海交大一再否认在招生过程中有舞弊“动作”,但数十名“个个有来头”的人“打招呼”却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教育腐败如同瘟疫一样躲藏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角落,它的每一次发作对公众而言都是一种新的不公平。杨东平分析教育腐败产生的原因是,教育部门在引入市场机制后有了较多的自主权,而相关的制度和规范没有跟上。
实际上,即使从西方教育的发展来看,教育公平也只能是个相对的概念,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只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公平。在美国曾有这样一个规定:公立大学录取一个黑人学生,国家给予2个人头的经费,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利。
在中国,这种做法在目前情况下显然不太可能。但如果有这种气魄来改变公民不平等的受教育权,也应该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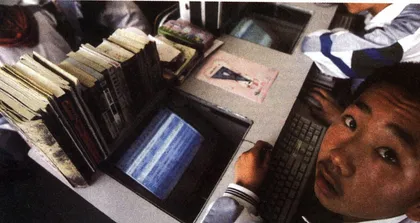
享受教育并非天生平等 大学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