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红色》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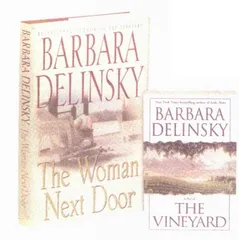
本期书榜有两个特点:一是原来榜上有名的书多数已经悄然退出,二是由此显得新书蜂拥而至,在仅列出的10名中倒有8部新作。然而我们要介绍的却是一部翻译作品。
这部书名叫《我的名字是红色》(My Name Is Red),作者是土耳其人奥尔汉·帕姆克(Orhan Pamuk),译者是埃尔达格·M·郭克诺尔(Erdag M.Goknor)。
帕姆克现年40多岁,是一位西方化的土耳其作家。他曾如饥似渴地学习欧美文学,后在爱荷华作家进修班攻读,吸取了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相结合的一种当代技巧。他所写的是土耳其80年的现代化进程不但未能根除甚至很少触及的那种停滞和落后。他不是思想家、政治家或记者。他就是一位小说家,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他的写作不是谴责现实,而是紧紧深入现实之中。当然,不谴责不等于赞扬,而深入现实则要像媒体那样用两种声音介绍两方面的情况。对于帕姆克来说,这是一种痛苦: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激奋。此前他的三部用不一致的声音所写的小说出版后都受到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好评,可惜没有广泛介绍给人阅读。
目前帕姆克的这部新作在他描写内部的东西方冲突为主题的小说中,当是远远地更为宏大更为惊人的。故事的背景是在16世纪末穆拉特三世苏丹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1290~1622)已有三百年历史。从波斯传入的微型画像也有了数百年之久,而这位苏丹正是微型画像师的恩主——在前商品社会,艺术家往往要仰赖恩主对其艺术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供俸才能维持生活,这种关系自然有“遵命艺术”的一面,对艺术的发展和艺术家个人才能的发挥同时又是一种阻滞力量。当时,恰值列潘托战败数年之后,奥斯曼帝国那种不可遏止的自信已经受到西方势力的痛挫,其文化的活力和诱惑力也已开始渗入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
小说在层层剥皮中展开。穆拉特的宫廷画家中出现了两起谋杀案:对象一位是微型画像大师埃利根特(英文意为雅致),另一位叫埃尼施特,他是个狡猾多端的人物,受苏丹之命要编纂一部包括埃利根特在内的四位最优秀的宫廷画师的书。该书是个秘密,那些画师们只是模糊地怀疑有这么一本书正在编写,而且他们只是对自己承认埃尼施特的使命有极其非传统的本质。
他们的内心暗藏恐惧与耻辱。恐惧的是被强有力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贴上异端邪说的标签和受到内怀隐藏不露的危险意旨的苏丹的惩罚。耻辱是因为他们既深受传统的浸润,可实际上又在破坏那一传统,这种破坏甚至是他们既渴望又畏惧的。
传统微型画的艺术——书中隐含着广泛得多的一种秩序——描绘人体时,有着伟大的美和多姿多彩中的仪典般的、纯客观的、无个性的表现手法。这样的绘画作品其实还是严格的插图。但在艺术技巧上,他们受密令要采取的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创新。人物都是单独的,肖像更是有对象的,即使树和狗也是具体的。这样的绘画不是插图,自身有充分理由算作艺术品。
这样的艺术品怎么会成为异端邪说呢?其一,伊斯兰禁忌定形,微型画之所以获准存在,是因为其笼统,不过是从属于文本的装饰。但如果描绘个人或物体只是出于绘画而没有文本掩盖,便具肖像身份了。其二也是更糟糕的,是透视的运用。一座远处的清真寺会比近处的人甚或他的狗还小。反对者会说:“这是按照安拉旨意的重要性还是肉眼看到的样子画的呢?”
矛盾的旧传统和新技法都是来自苏丹的旨意,这就给画师们出了难题。为首的那位画师本人就是个顽固的神秘的传统主义者,他在绘制一对传说中的恋人时用心良苦,把他俩处理成稍稍相对,却主要面对观者,这样便不同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见到的样子,而表明他们是“出自安拉的记忆”。
在书中涉及的众多情节中有一个最为动人,那就是被谋杀的埃尼施特的助手布莱克(英文意为“黑”)对埃尼施特之女的热烈追求。她以波斯微型画像出现,半侧着身;经过布莱克曲折、有时荒诞的争取,她终于成了血肉之躯,二人缔结良缘。
全书由12个人物分别叙述构成,不时还插进一条狗、一棵树、一枝金币和好几个口吐怨言的尸体和那个绯红的颜色的自白——这最后一点便成了书名:《我的名字是红色》。这些人与物自然是各说各理,有时揭示了故事的线索,有时则表达一种观点,如“红”的观点就有极大的迷惑力和能量。
当然,书中对靠秘密、谎言、阴谋和混乱维系其统治的奥斯曼帝国的具体事例全不见经传,纯属作者杜撰。而书中一切努力的失败,恰是作者的成功。读者会受到一阵阵失落感的刺激和由于故意制造的不可靠而感到痛苦,正是从这种感受中折射出全书的主题:我们的世界是被一团迷雾所左右的。 文学艺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