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收购文学青年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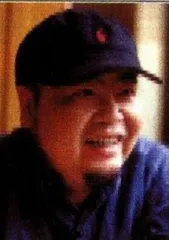
每一次目睹3岁女儿在我面前连续数个小时Non-stop地摸爬滚打,惊讶和无奈之余,也会产生一种功利主义的念头:应该有这样一种装置,让全世界体力过剩的儿童把他们释放出来的能量用来发电,既不致浪费资源,又可以为终将全面爆发的能源危机提供一个备用的解决方案。
这一次,当我在报上读到“榕树下”正在与贝塔斯曼公司洽谈的那宗交易,则令我不得不相信,上面的那一个怪念头至少在理论上是大致可行的。
我估计,全中国有多少体力过剩的儿童,就会有多少灵感爆棚的文学青年。尽管灵感再充沛也不能用来发电,但是,在“榕树下”遇到了贝塔斯曼之后,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相信:文学青年是有价值的。如果一定要在这个价值上加一个数额的话,我想会是1000万。
1000万美元不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即使有捏造的嫌疑,至少也不是凭空的。据报道,贝塔斯曼正在与“榕树下”就以1000万美元收购对方70%~80%股权一事进行洽商。尽管贝塔斯曼近一年来已经在德国商界成为“中国神话”,然而大部分中国业内业外人士对这宗交易依然看不太懂。分析来分析去,结论只有一个:1000万美元购买的不是“榕树下”的品牌,更不是存储在其服务器里的那一大堆字节,而是榕树下“拥有”的160万注册文学青年。一旦完成了对“榕树下”的收购,贝塔斯曼就等于在150万名书友会会员的基数之上翻番,为公司再添160万大有潜力可挖的优质客户。
对于贝塔斯曼来说,1000万美元绝对只是小菜一碟。不过,无论最终谈成了没有,这宗交易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使文学青年获得了数学上可以计算的价值,即平均每个人头价值6.25万美元,约折合人民币50多万元,基本上是一个中国普通白领的全副身家。当然,我更加佩服的还是“榕树下”的CEO朱威廉,我甚至觉得朱威廉卖“树”在精彩程度上几乎超越了李嘉诚的卖“橙”,尽管在此之前我曾经在一篇报道里读到,朱威廉“真的”在“榕树下”办公的地方手植了一棵人造的大榕树,让所有的编辑每天坐在这棵大树下面审阅来稿及更新网页。
俱往矣。文学青年为什么这样值钱?或日,朱威廉凭什么把底限设定在1000万美元?青年创造文学,青年也消费文学,网聚人的力量,网也吸收文学青年的能量。就像朱威廉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有千千万万个文学青年,血液里骨子里都有对文学的崇拜。”怪不得,就连给王朔留下了“阳光男孩”印象的朱威廉本人也常常以“文学青年”自称,当然,这是一个开着红色梅赛德斯跑车的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这个似乎只有中国才有的名词,应该是白话文运动之后开始大量投入使用的,它和白话文一样,代表着当时的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在白话文运动的那个特定的时代,一个酷爱文学的青年(即使只有十五六岁)却坚持以文言文写作,那么该青年仍旧还是一个“旧式文人”,非但不能获得“文学青年”的光荣称号,反而有可能被攻击为“遗老”甚至“余孽”。不管是家庭环境还是潮流风气使然,一日为“文青”,终生都是“文青”,脸上的青春痘可以人间蒸发,胸中的块垒也可以变成豆腐渣工程,唯有对文学的“那份”热爱,永远高烧不退,因而文学青年是作为商业资源极具可持续发展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像我,从15岁开始就是一个文学青年,当然做文学青年主要是想结识若干的文学女青年(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学女青年,则文学青年的总体客流量将大为下降)。我坦白,甚至当我成为老爸级文学中年之后,还是忍不住于某月黑风高之夜偷偷地“上”过“榕树下”一次,爬树的目的是为了查看有没有文学女青年的玉照。
鲁迅的一生爱憎分明,唯独对于青年、尤其对文学青年却是爱恨纠缠,不过到了晚年,鲁迅还是比较偏向于恨文学青年的,最为痛心疾首的,乃是这一生屡屡惨遭文学青年的利用:“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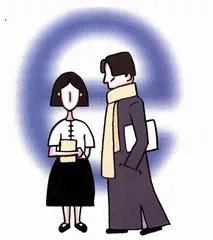
俱俱往矣。在网络时代的表达方式、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念以及新一代的电子化文学青年的共同努力之下,资本、品牌、文学、青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停留在低道德水准上的纯粹的、单向的利用,突出的正是一个“互”字,不是早已经把Internet译成“互联网”了吗? 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