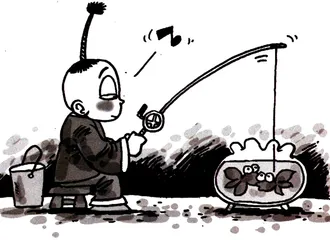生活圆桌(160)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劳乐 艾艾 寒流 惨淡少年)
死人多点的
劳乐 图 谢峰
小时候看《尼罗河上的惨案》,除了那个自认“比利时小人”的波罗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写黄色小说的老太太。我还记得她在饭店里第一次遇见波罗时的那段对话。她让波罗讲一个他经手过的案子,而且要“死人多点的”。以我后来看侦探小说的经验,这个老太太是找对人了。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堪称是手下最不留情的侦探小说家之一,她总是让波罗目睹了三具以上尸体之后才说:“不能死更多的人了。”
忘了在哪儿看到过一种说法:侦探小说里最好不要出现两具以上的尸体,否则就是屠杀了。不过,迄今为止,无论现在的侦探小说中又出现了诸如“黑幕派”、“间谍派”、“硬汉派”多少种门类,凶杀案、尤其是连环杀人案仍然是读者最多的题材。侦探小说中有一个侦探曾经断言:如果说一名凶手在犯下第一宗罪行时手法缜密、不容易被发现线索,那么他在犯第二宗罪行时手法必然出现重复,因而被发现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如果他还敢于第三次或更多次地犯罪,他被发现的概率将呈级数增长。据说现实中的侦探往往不屑于小说中的侦探的手法,认为后者过于自以为是。这种看法到底有多准确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实生活中的连环杀人案的水平远远超过了那个小说中的侦探的估计。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十宗未侦破的凶杀案里有四宗是连环杀人案。1888年的“肢解者杰克”单在伦敦就至少杀掉了五名妓女;美国新奥尔良的“带斧子的人”在1918年至1919年间至少杀掉了八个意大利杂货商;1946年上半年,被《谋杀百科全书》称为“月光下的谋杀者”的罪犯在美国阿肯色的一些小镇里杀掉了三个男人与两个女人;1933年至1937年,美国克里夫兰的一个家伙则以每次砍下两个人的脑袋的速度考验着警方的能力。
在现实生活中,处理一具自然死亡的尸体都需要繁琐的手续,更不用说一具非自然死亡的尸体。但在侦探小说里,一具尸体不过是主人公出场的引子,或者是像在各种RPG游戏中那样,是一种可以使鼠标箭头变成一只小手、然后被“抚摸”一番的道具。我在侦探小说中见过的最接近现实情况的尸体是在一本不出名的《罗莎安娜》中。书中的描述是:死者三围标准,身上有穿过比基尼晒日光浴的痕迹,虽然脸部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已经浮肿,但可以想象生前是个美女;然而,即便是这么一个容易引人注目的人物,警方花了三个多月才找到一点有关她身份的线索。小说的作者之一是一个据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瑞典女诗人。尽管这部小说后来还是俗套,但它已经让我想起了过去认识的一个从不看侦探小说的女孩。这个女孩的全家人在一个晚上被闯入者用石块砸死,只有她一人因为外出幸免。这很像一个刺激的侦探小说的开头,但事实是这个凶手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线索可寻。

准备活动
艾艾
日本人生活的内容之一是为下一次地震做准备,这是我在《樱桃小丸子》和《蜡笔小新》里看来的。老师经常带着一群头上套着棉罩子的小学生从教室逃到操场上,如果来不及逃的话就钻到桌子下面。美国DISCOVERY频道作过一系列“愤怒的星球”节目,其中就包括地震。日本人的脸频繁出现在节目里,这固然是因为日本确实是个地震大国,也因为日本人过于精细的防范措施。厨房里,几个主妇在辅导员带领下仔细关上水电气阀门,然后冲出门。美国人显然不太欣赏日本人过于僵化的训练方法——下一个镜头是一间毁于地震的厨房,美国人的配音是:他们就没有想想如果厨房都毁了的话该怎么办(大意)。
其实准备总是有必要的,只要适时修改,关键问题在于修改过程中个人痛苦的大小问题。高考结束,开始报志愿。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觉得自己喜欢看书,就选了一个跟图书馆有关的系。录取通知书下来之前,我的心理准备方向就是图书馆了,每次经过市里惟一一家图书馆我就觉得亲切。结果人家没有录取我,另外一所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要我。好在我当时是个糊涂的人,没有感觉个人理想的破灭是什么大事(也许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理想)。
进大学后,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将献给光荣的幼儿教育事业,从大三起我就开始准备报考北师大的研究生。大四我们开始进幼儿园实习,彼时我才发现有个巨大的障碍我跨不过去,就是孩子们的午餐问题。每天中午正是饥肠辘辘之时,我们要把一桶桶饭菜馒头从厨房运到教室、餐厅兼卧室,分到一只只小碗里,看着他们吃下去,不够再添。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觉得白菜炖粉条有这么香过。整个过程中我紧紧闭着嘴巴,生怕口水流出来。待到把小孩子们一个个送上床,我伙同几个同学狂奔出幼儿园,冲到最近一个饭铺,什么好吃点什么。大约实习了两个月,同学们平均胖了三四斤。我想还是回去教中学吧,我终于感到改变理想还是很让人难受的,尤其是想想不吃饭时孩子们的样子。
现在我还在不自觉作各种准备,修改各种准备。很快一辈子就过去了吧。
穿过黑发的负离子
寒流
罗大佑的深圳演唱会,本来倒是打定主意不去的,大佑的歌写得好,但是唱得实在不怎么样。越是临近9月1日,媒体攻势越发强大。海报上说:“他的歌,见证过你的青春。”这样的话多看几遍,简直觉得不看罗大佑不是对不起罗大佑,更对不起的是你自己的青春。其实,活到这个年纪,对不起谁都无所谓了,最怕对不起的也就是自己。这么一弄,也就要去看大佑。
9月1日是个周六,还是孩子开学的日子。想到每个周末不是去超市买菜买日用品就是回家给老公孩子做饭,忽地意识到这一个周末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周末。
首先想的是跟谁去看罗大佑的问题,后来还是决定约上去年一同看田震的女友一—她在田震唱《靠近我》的时候把手机打开,电话拨到了一个她暗恋已久的男人那里。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把电话举着举着。
老实说,她的举动比田震的歌还要打动我。
这次约上她,我想的是我要等到罗大佑唱:“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的时候,像她那样,把手机打开,打到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在大学校园里为我唱这首歌的那个人那里去。
票早就买好了,等待着这一天。8月31日,想去做个头发,弄得像个样子去见大佑——好歹总不能像平时一副煮饭婆洗衣婆的样子吧?
发型师建议我弄个负离子直发烫,“这样显得年轻点。”对三十来岁的女人而言,“年轻”二字是她们的“死穴”,一点就中的,我就烫负离子。烫好了,直直的头发贴在头上,没有刘海的中分。等到老公来接,第一句话就是:“怎么弄得跟大寨的郭凤莲似的?”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响起的时候,大雨如注,硕大无朋的伞也挡不住水珠。正要给当年穿过我的黑发的手的人拨电话时,忽然想起烫完负离子时的发型师的千叮咛万嘱咐:“这两天头发不能湿水,否则负离子会失效。”于是心下咯噔一下,让朋友举伞,自己死死抱住我的负离子。
等到“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天上真是一片轰隆隆的雷雨声。大佑说:“有劲的把你们的伞也扔掉吧!”尽管全场群情激奋,万人同歌,但是还没见到真的扔伞的。这样的天气,大佑也许觉得还是有点对不起大家的,他说:“干脆今天干到底,把歌都干掉。”全场叫起来,以为大佑至少会把他的名曲唱遍,但是紧接下来是一首《东方之珠》,演唱会宣告结束。
回到家里,我问老公:“为什么我烫卷发的时候像狮子王,现在烫直了又像郭凤莲?”
老公在沙发上看报纸,他一针见血地说:“老了么,烫什么都不好看。”
渔夫的儿子
惨淡少年 图 谢峰
《大河恋》(A River Runs Through It)是我喜欢的一部电影。蒙大拿的父子三人站在没膝的河水里,用大苍蝇作饵,将渔线甩出优美的弧线,在落日余辉里闪闪发光。然后就是静候鱼儿上钩,满载而归。
从很小时候起我就希望自己是个渔夫的儿子。在我的想象里,我的家应该在海边、湖畔,或是河岸,家里有破船、渔网、钓杆和两三只鸬鹚。每天我会穿着背心、短裤,光着脚跟在父亲屁股后面去打鱼。然而让人沮丧的是,我父亲根本就不是什么渔夫。我家住在拥挤、肮脏的北京城,我的家里没有破船、渔网,甚至连钓杆都没有,更别说什么鸬鹚了。我的父亲是个身上终年散发着医用酒精味道,手里整天拿着冷冰冰手术剪的家伙。我们家惟一和鱼沾边的是父亲在一个瓦罐里养的几条金鱼,是那种极其廉价的,在早市可以用两元钱买上十条的金鱼。小头小尾巴大肚子,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珍珠。这真让人受不了。
其实如果我的父亲像《小镇医生的故事》里唱的是个小镇医生的话,我的心情可能会好很多。《小镇医生的故事》是李宗盛的歌。如果像歌里唱的那样,我父亲是个凡夫俗子,我的家住在一个波澜不惊的小镇上,那该有多好。每天风从小镇的一头吹起,带来远方的消息,不经意间会扬起些许灰尘。《阿宗三件事》里李宗盛这样唱自己的身世:“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之子,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做一个瓦斯行老板的儿子,这也比较符合我关于自己身世的遐想。
记得上大学的第一天,每个人做自我介绍。一个哥们儿的开场白是:“我出身世家!”我们顿时对这个黑不溜秋的小子刮目相看,谁知他的第二句话让我们每个人的下巴都掉到了地上。因为他的第二句话竟然是:“农民世家。”这是迄今为止我听过的最NB的自我介绍了。
今年夏天我去了位于渤海湾的一个小城,终日躺在沙滩上,继续做我年少时的梦。我在小城里目睹过几个男人编织渔网,绿色的线穿过不知名的机器,发出“咕咕”的声音,出来后就变成了好大好大的一张网。织网的男人们赤着膊,抽着烟,身上散发着海水的咸味与鱼的腥味混合而成的迷人味道,而不是什么让人窒息的医用酒精味道,让我艳羡不已!
下辈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