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音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晓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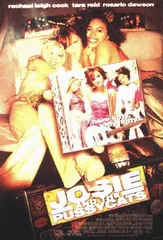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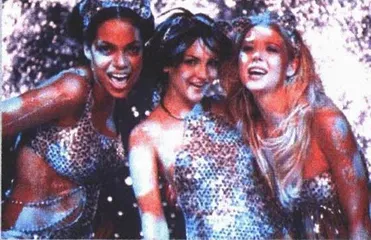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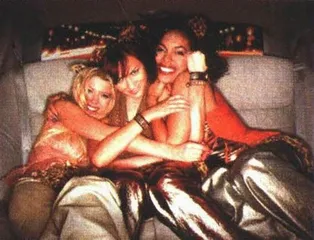
但凡反映当今流行音乐的电影,都有一个固定模式,就是要暴露一下唱片业的黑暗面,比如成员之间的明争暗斗,商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对付听众的欺骗花招……这倒不是导演们没有新意,事实上唱片业的龌龊尽人皆知,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观众吸引住。
最近的一部电影《猫女乐队》又是这种模式的翻版,不过这部电影以更夸张荒诞的手法来讽刺当今的唱片业,甚至,你可以联想到“接招”(Take That)和“辣妹”当年的故事。其实这类影片大都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人们,要重视音乐。
文艺作品里宣扬的往往是现实中没有的,让人们有种慰藉罢了。现在的问题是,人们不重视音乐吗?现在的唱片里没有音乐了吗?在《猫女乐队》里有一句台词:“我觉得他们的唱片里充斥着垃圾。”于是说这个话的人被唱片公司经理人偷偷“干掉”了。
人们确实已经走进了不重视音乐的时代了。
如果有人问你:“最近在看什么音乐?”你会像小学生纠错一样指出他用错了动词,并且认真地说:“音乐怎么可以看呢?”
音乐的确可以看了。前两年,日本开始流行一种叫做“视觉系”的东西。70年代,英美一些摇滚歌星为突出舞台表演效果,演出时浓妆艳抹,比如戴维·鲍伊、“吻”和“纽约妞儿”等,有人管他们叫“华丽摇滚”。但无论怎么打扮,铅饰背后仍然要靠音乐来征服听众。而日本视觉系则完全相反,当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音乐时,只有靠不人不妖的效果来吸引人,并且,这种变态被他们发挥到极致。
MTV的出现,把人们从听觉时代带入了视觉时代。最初,谁也不会想到,MTV只是为那些唱片商做唱片宣传,音乐录像带只是音乐的附属品,但20年过后,唱片商发现,音乐做得好,不如音乐广告做得好。对音乐自身来说,从听觉时代到视觉时代的变迁,音乐逐渐依附在其他东西上,这才是音乐的悲哀。
电视时代的可怕就在于它让人们逐渐失去思维能力,切掉想象的翅膀,使人们对一切判断都基于形象上。一首歌曲只有配上画面才能被接受,这是人对音乐审美的倒退。
最近流行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又是一个明显例证。这首歌写于1995年,当时作者找过几家唱片公司,都被拒之门外。几年后,有人用Flash动画方式,才得以通过网络流行开来,这张唱片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版。雪村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我要感谢互联网。”但他同时对自己作品长期无法得到认同而耿耿于怀。一首歌被形象化,并且通过网络无厘头文化标准验证之后,才会流行。那么,在此之前,人们都干什么去了?
有人会说,音乐这种艺术形式比较抽象,有时通过形象化表现有助于人们对音乐的理解。我曾经看过《第一钢琴协奏曲》配上奔腾的河流和雄伟的高山画面,确实可以更深刻感受到这首作品的恢宏气势,但这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崔健当年不接受记者采访,原因在于他怕文字对摇滚误读。同样,影像也会对音乐误读,日本视觉系音乐简直难听至极,但因为它把观众注意力从听觉转移到视觉上,才大行其道,并且已流窜到中国。所以,问题在于,形象化对音乐的辅助早已喧宾夺主,而人们似乎也认可了让道具作为主角这一事实,音乐怎么样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形象。像莫文蔚这样人,她唱歌的嗓子满大街都是,但是她红了,因为她有一个招男人女人喜爱的形象。有人不喜欢塞琳·狄翁和玛丽亚·凯里,但至少她们还有一个像驴叫一样的嗓子,而莫文蔚之流,连最起码的唱歌条件都不具备。再比如王菲,从北京到了香港这个“远郊区县”后,反倒成了村姑,在试图改变自己村姑形象失败后,她干脆移花接木,把Bjork、Cocteau Twins、The Cranberries符号化的东西移植到自己身上,于是她焕然一新,成了另类、前卫的标志。这时,香港的同类反倒成了村姑。其实王菲的歌不过是裹着一层廉价另类包装纸的垃圾,但这种垃圾恰恰满足了那些对另类一无所知的人心理需求。所以,王菲的“视觉系”成功了。
这就是电视时代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方式,于是就有了读书进入读图时代,读图时代是人思维变得懒惰的最好注脚。同样,音乐也进入读图时代、读像时代,谁还去在乎一个歌手嗓音的表现力,谁还在乎音乐是否动情,人们更在乎这个人本身——他们的花边新闻比他们的职业更重要……
上中学时,一位音乐学院的教授对我说:“音乐是在用时间流逝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是美。”如今的音乐,在它流逝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什么? 视觉系艺术音乐唱片视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