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住在郊外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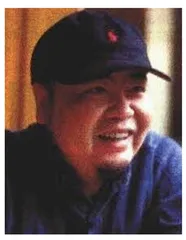

一个人究竟是住在城里好还是住在郊外好?郊还是不郊,这是一个问题。
据说在国外的发达国家、最起码在美国,有钱有追求以及有品味的人都是住在郊外的,再不济的,也得找个城乡结合部呆着,只有穷光蛋才赖在城里。因此,我国的地产商也开始在郊外大搞房事,很多人随之也从城里搬到了郊区,用脚投了票。在他们绝尘而去的身影后面,仿佛响起了约翰·丹佛或“贝六”的第二乐章。
战后在美国兴起的“郊区化”运动(suburbanization)使这个国家的日常生活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例如汽车和快餐的普及。尽管中国1.0版的郊区化运动除了使仍然像穷人一样“赖”在城里的那些人比较郁闷之外,暂时还看不出更多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正是社会富裕的表现,尤其是在祖祖辈辈都住在郊外甚至乡下的农民拼着老命想挤进城里的背景之下。套用《围城》的金句,这大概可以称做“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最低限度上,也有助于消灭城乡差别。
从陶渊明开始,住在城里的人就有“悠然见南山”或“而无车马喧”,也就是搬到郊外的理想和冲动。这种行为不尽表达了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也体现出对“中心”的舍弃以及对“边缘”的向往。即使是在上世纪中叶我国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中,对郊区的浪漫想象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觉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从50年代一直发烧到今天的苏联流行歌曲起到了深刻的作用:深夜、花园、静悄悄的四处,轻轻唱的风儿……浪漫得紧要,正在销售郊外住宅的房地产商完全可以照搬来做广告。冷战结束以后,我们才通过不同的途径逐渐了解到,在“晚上的莫斯科郊外”,其实本国的恋人不多,外国的间谍倒有不少。俪影双双原是假的,谍影憧憧倒是真的。
就我所知,北京、上海、广州或者香港、台北的郊外,也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美好,事实上,所谓的“郊外”只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边缘化的城市社区,根本就是全封闭的住宅社区,与我们对“郊外”的想象基本无关。这些小区里的居民在日常工作和消费娱乐等方面,仍是以中心城市为依附的。换言之,不是我方撤往郊区,而是郊区在向我方靠拢。报上有一则报道的题目是这样的:《广州郊区住宅逼近城市人群》,很显然,我们的战略思想依然停留在“农村包围城市”阶段。罗大佑曾经跟我说过他的一件糗事:曾经和几个研究民歌的北京同志深入内地的穷乡采风,连日来苦无所获。忽一日,就听得从远处的山坡上随风飘来一阵阵若有若无的美妙绝伦的山歌,这伙人强压住心头的狂喜,为了不惊扰唱山歌的人,他们悄悄地从背后接近,正要打开录音机,却发现事情有点不大对头,再仔细一听,原来唱的是邓丽君。
市区和郊区、中心或边缘也都是相对而言的。郊区只是城市拓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区域,这一点,玩过“帝国时代”或“文明”的人比谁都清楚。在哥白尼之前,我们一直坚信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之后,我们才接受了地球只是银河的郊区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但是,比这件事更残酷更可怕的,是那种一出生就带有先天性城市基因的郊外社区比城市更容易被不断地快速复制出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移居到郊区,原有的郊区也在不知不觉地变成另一个新的市区。世界本来是有郊区的,住的人多了,也就没有了郊区。不管是住宅的郊区化还是郊区的城市化,在不久的将来,郊区会变得比城市加倍地“楚德”——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恢复你的班机……但是你将会抵达另一个楚德,完全一样,每个细节都不差。整个世界都被独一无二的楚德所覆盖,无始无终。只有机场的名字不一样。”
在选择居所这件事情上,听谁的都好,就是不能听房地产商的。当市区的地皮日见其少,甚至连被推崇为时尚潮流的Soho也卖得七七八八之后,地产商就不得不打起郊区的主意来,这一次,他们又哄我们说住在郊区的不是中产就是白领,非富则贵,事关品味。其实,在他们的客户自我感觉良好地搬进郊外住宅之前,这些地方本来就是有许多人住着的,就我国的国情而言,他们共同的名字既非中产亦非小资,而是农民。
不管是崇尚品味也好,贪图便宜也罢,一个在城里上班的人最后舍近求远地选择了住在郊区,毕竟是一种逃避的结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在住在郊区这件房事上,小资一惯的盲动尤须注意克服。办好了,叫Townhouse,叫“回归自然”,“远离尘嚣”或者“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办不好,就叫“汤耗子”,“流放充军”,“上山下乡”或者“自绝于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