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都是月饼惹的祸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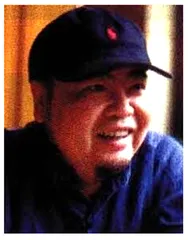

许多年以后,当我们得知“奔”上月球的原来是一个木讷的美国男人,我们对月亮的态度似乎也慢慢变得多少有一点破罐子破摔了起来。那颗遥不可及而且表面荒凉不毛之“球”已经不再有什么指望,好在对“饼”的控制权还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人手中。
月饼大战不仅一年一度,而且“月战前传”或“中秋前戏”也开始得越来越早,历时越来越久,战争规模更是逐年升级。自香港人在三年前制造出世界最大月饼之后,这个纪录先是马来西亚人以1366.6公斤刷新,今年7月15日,台中县30多位糕饼师又以一枚重达2341公斤、长3米、厚22.4厘米、可供15000人食用的月饼申请破吉尼斯纪录。在上海,今年第一批月饼已经提早在农历大暑那天开炉,据该市糖制食品协会称,目前已接到的月饼准产证申请达30个,生产厂家300家,其中新加入战团的不少于30家。预计今年上海的月饼总产量有1万吨,中秋节平均每人要吃掉750克。多乎哉?不多矣,据《老残游记》里一场因“月饼投毒案”而起的法庭调查显示,当年过中秋,一个大户人家就要定做20斤月饼,其中送礼用了8斤,另外“送了小儿子的丈人家4斤”,其余的8斤“自己家里人吃了”,连家里的两个长工也“每人分了两个”,而且“当天都吃完了”。
市场调查一再显示,卖买及授受月饼的越来越多,吃月饼的、尤其是八月十五晚上发生过“月全食”的人家却越来越少。即使没有市场调查,每个人心里其实也都有数。在这个问题上,产、供、销、消四方似乎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装在礼盒中的月饼不是为了被吃掉,尤如挂在天上的月亮也不是为了让人“登”上去的。
不管有多少月饼被做出来,亦不论有多少月饼最后被当作垃圾扔掉,月饼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食物。尽管在《梦粱录》中就已出现“月饼”一词,但是直到南宋,中秋食品仍以应节瓜果为核心,月饼并不普及。在月饼界已成信史的,倒是《野客丛谈》所记载的一段野史:“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夏天……至中秋佳话,刘伯温于月饼内遍置‘八月十五杀鞑子’字条,相约起事,各地胡人是夕均被戕。中秋夜民间无不夜饮,乘酒兴为之,势如破竹耳!胡人不识汉字,因而覆亡。”
可见月饼一开始就是媒体,后来是媒体,现在也是媒体。是媒体总有地方特色,月饼也有苏式、广式、京式之别(也是当前媒体大战最激烈的三大战区)。与饺子相比,月饼在外观、制作以及馅料上的多样性实在要丰富得多。与其说此系各地口味不一所致,不如视为不同地方的居民借助于月饼这个媒体,在团圆的主旋律下以不同方式各自叙述了对于秋天以及月亮的不同观感。岭南的四季不分明,八月半炎蒸未退,直接造就了广式月饼的富足、滋润,整个的一派花好月圆。业已式微的苏式月饼,以酥皮、色白大异于广式“彩云追月”之金黄而与二十四桥的月色最为接近,总是用一张粉色的薄纸两面衬着,这张纸的用途,还在于承接进食时不断剥落的层层酥皮。静的时候,能听到酥皮落在纸上的声音,最后,纸对折,把一堆碎屑仰天送入口中——我当然不会说它是“月落乌啼霜满天”。不过,有一种苏式的鲜肉月饼,竟是热腾腾的,肉感的,秦淮河的桨声灯影也就若隐若现了。
坚硬是京式月饼的通行证也是墓志铭,有那个流传甚广的“掉在地上砸了个坑”的老笑话为证。其实,就算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月饼而是燕赵的秋月,也会是匡当一声,连带砸碎了一大片琉璃瓦。虽然还不至于苍凉到有“秦时明月”的感觉,不过中秋夜的北京确实己很凉了,参阅郁达夫《故都的秋》:“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正是两种月饼的写照。不过全球气候趋暖的同时,节令的市场化也正在统一人们对于月亮的印像。近十多年来,广式的双黄莲蓉月饼一直是消费者的首选,因此各路月饼都在向广式靠拢,就连北京“硬派老生”的代表作“自来红”(京韵做“滋了红”),现在也软玉温香了起来。千里共蝉娟,月饼作为媒体只要能成功传达或者撩拨起这种感受,就已不辱使命,好不好吃、要不要吃还在其次,否则市场上就会年中无休地“月战”不止,就像上海的年糕。热衷于把饼做大及培育“惯性收视”的食品商,是不会产生“明月几时有”这种浪漫主义的疑问的。相比之下,更年期琼瑶代表作里的尔泰口占有两行歪诗,倒是很能体现月饼的无厘头现状,诗云:“一个月饼圆又圆,中间一切少半边,惹得老鼠乱糟糟,花猫一叫静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