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观察:在衰退之雾中航行?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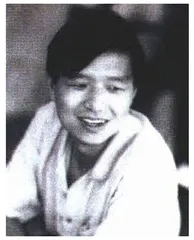
2000年春天,我为《三联生活周刊》撰写过一篇关于思科公司迅速崛起的封面故事,准确预测到思科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思科的夺冠当时曾令许多人瞠目结舌,不过到了今天,令更多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思科从高峰滑落的速度和它攀上高峰的速度几乎同样之快。思科的CEQ约翰·钱伯斯对此的感受是:“对像我们这样规模的公司而言,这也许是其所经历的历史上最快的一次减速。”这种说法在我前些天同思科中国人士交谈时得到了印证——他们说:思科一直顺风顺水,从未被这么大的风浪打晕过。
历史上最快的一次减速?被突如其来地打晕?这种略带夸张的语调展现了一个事实:经历了多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今天有不少企业领袖必须承认,他们从来没有在如此充满变数的环境中操作过公司。他们对经济增长的放慢都谈不上习惯,更不必说面对一场真正的衰退了。可以理解,眼前的艰难时世令他们感到十分不安。每个人嘴里都念叨着一个词:能见度。这意味着,企业的一把手们不再能认清今后的方向。被生意不景气所深度困扰的爱立信首脑柯德川,不久前就说过:“在当下动荡的经济环境中,我们的能见度极为有限。”
雅虎下野的CEO蒂姆·库格,思科的明星领导人约翰·钱伯斯,英特尔的掌门人克雷格·贝瑞特,无一例外地重复过这种论调。惠普的女当家卡莉·菲奥里纳则用了一个比喻:“我们仿佛在雾中航行。”
伴随着股价的暴跌,许多科技公司的市值已经跌去了3/4。一些dotcom公司,例如雅虎,其市值一度是GM、Heinz和Boeing公司的总和还多,现在却在制定如何生存而不是如何增长的战略。
美国上一次遭遇严重衰退的时间是在20年前,欧洲也有10年时间没有体验经济的滑坡了。今天欧美的许多企业领导人对管理经济衰退期的企业没有直接经验,上一次衰退时,他们大多在大公司里苦熬出头之日,而dotcom公司的领军人那时更小,还在读中学甚至小学。
亚洲的情况则很不同。日本在过去10年中始终被衰退缠得脱不了身;其他东亚国家刚刚经历过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危机之后的急剧经济紧缩凸显了为强劲增长所掩盖的管理缺陷:有太多的亚洲公司过于集权化,由创始人或其子孙把持,对股东漠不关心,更没有财务透明度。在市道转坏时,这些因素被证明是非常有害的。

韩国大宇集团的金宇中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7年,就在韩国已经请求IMF援助之时,他还在大肆举债以使泥足巨人大宇能够继续其疯狂扩张。金坚决抵制人们调查公司财务健康的努力,对重组的呼吁也弃之不顾。到1999年银行不得不出面接管大宇的时候,大宇的债务已经攀升到了800亿美元。
欧美公司当然不大可能采取和大宇一样的极端做法,但它们在危机到来之时,很可能像众多亚洲公司一样,用板条到处钉牢破碎的窗户,然后祈祷暴风雨不会对自己造成多大冲击。如果我们考察以前的危机,就会发现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
与在公司内四处大兴削减之风的做法相比,企业领导更应推动企业的全面重组,以为可能到来的回升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这意味着完全砍去不能创造价值的那部分业务,加大对可以带来价值的业务的投入,爱立信外包手机生产的决定就是一个“壮士断腕”的好例子。
许多技术公司,如思科,都曾说过它们不会裁减员工。然而在今天,它们都开始这样做了。“旧经济”公司也加入了裁员大潮。不过,不断公布的裁员人数并不表明,企业在合适的地方施行了外科手术,也不能证明,外科手术的幅度是过大了还是太小。
削减的力度与在增长领域投资的力度一样,是一项管理上的挑战。波音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教训证明,企业有时可能削减过度。当时航空业面临紧缩,波音砍掉了许多供应商,削减了大约6万份工作——工人中每三人就有一人被裁。但到了1997年,订单重新上升,波音用了非常大的努力去跟上市场需求。有一段时间它甚至不得不停止喷气式客机的生产以便供应商和工人能够赶上进度。波音的这一管理失误给了其主要竞争对手空中客车以巨大的可乘之机。